引言:石家河之谜与“羊”的问题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宏大叙事中,一个核心的文化与经济现象是两种不同但相关的物种的引入与扩散:驯养绵羊()以及更晚出现的山羊()。既有的扩散模型清晰地描绘了一条由西向东的传播轨迹:这些源自西亚的动物,首先通过西北的甘青地区进入中国,随后在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500-2000年)逐渐向东扩散至黄河流域中原腹地。然而,位于长江中游、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强大政体——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2500-2000年),却呈现出一个引人深思的例外。在其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形态逼真的绵羊与山羊陶塑,其出现时间与这些动物在中原地区的广泛传播几乎同步,甚至在艺术表现的成熟度上更胜一筹。这种在年代和地理上的不协调,构成了本次研究的核心议题。
本文旨在论证,绵羊和山羊图像在石家河文化中的早期出现,并非其生业经济突然转变的标志,而是该政体高度的社会复杂性、广泛的区域影响力及其积极参与一个初现的、横跨大陆的精英交流网络的有力证明。绵羊和山羊,作为长江中游湿地环境中的“异域之物”,被石家河的统治阶层采纳为彰显其权力、地位和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的强有力符号。这一现象揭示出,石家河并非被动接受北方文化影响的边陲,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其精英阶层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定义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互动圈的形态与格局,甚至属于其作为一个区域性霸权政体接受了来自北方部落的高价值动物朝贡。
为系统阐述此论点,本文将首先梳理绵羊和山羊自西亚至中国的两条不同路径与时间线;其次,深入剖析石家河政体的社会政治图景;再次,批判性地审视来自石家河遗址的具体证据;最后,重构连接南北的远距离交流网络,正是这一网络使得这种卓越的文化转移成为可能。
|
|
|
|
|
|
|
黄河上游(甘肃、青海) |
|
|
|
黄河上游(甘肃、青海) |
|
|
|
黄河中游(河南、山西) |
|
|
|
黄河下游(山东) |
|
|
|
长江中游 |
|
|
|
长江中游 |
|
|
|
长江中游 |
|
|
|
黄土高原北部(陕西) |
| 表1: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关键文化年表 |
|
|
第一章 两条路径:绵羊与山羊的分别之旅
绵羊和山羊虽然一般都起源于西亚,但它们进入古代中国的历程并非完全同步,其传播路径和被不同区域文化接纳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厘清这两种动物各自的旅程,是理解它们为何同时出现在石家河文化中的关键。
1.1 先行者:绵羊与汉水走廊
考古学证据表明,绵羊是两种动物中较早进入中国的 。其驯化最早可追溯至大约11,000年前的新月沃地 。作为“新石器时代一揽子技术”的一部分,驯养绵羊随着农牧人群的迁徙,穿越“内亚山地走廊”,向东扩散。
中国境内最早的可靠绵羊遗存发现于甘肃和青海地区,年代约为公元前3600-3000年(距今5600-5000年) 。这些早期引入的绵羊,不仅是食物来源,其形象很快便出现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开始了其符号化的历程。
图:羊角纹双耳陶尊,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甘肃洮河流域出土,马家窑文化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完整随葬羊骨架。
1.2 后来者:山羊与北方玄武岩帝国
与绵羊相比,山羊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 。虽然山羊同样驯化于西亚,但其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规模化出现,与石峁等北方晚期龙山文化政体的崛起紧密相关。基因组学研究确认,在陕北石峁遗址(约公元前2300-1800年)发现了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羊遗存,其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注:目前经过系统骨骼形态学鉴定的家养山羊即出自龙山晚期的陕西神木石峁和木柱梁遗址。)
此外根据山羊古DNA研究,内蒙古的古山羊与中国现代山羊遗传密切相关,这表明内蒙古的古山羊对中国现代山羊具有遗传贡献,也进一步支持了中国可能是山羊驯化中心之一的假说。
图:中国先秦前出土山羊的遗址地点(蔡大伟等,《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新石器晚期均为龙山时期文化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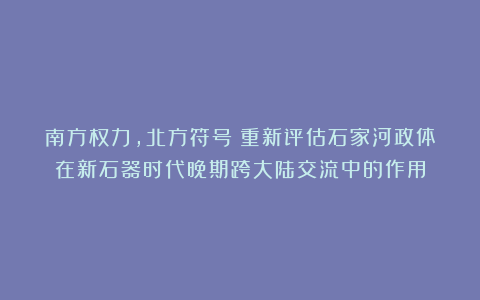
第二章 石家河政体:长江中游的超级都市
2.1 都市、社会与权力
石家河遗址群坐落于湖北省江汉平原,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的巅峰之作。在石家河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500-2000年),该遗址群的总面积超过8平方公里,是当时该区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
2.2 创新中心:手工业专门化与礼仪实践
石家河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更是一个手工业创新的高地。其制陶业尤为发达,生产了大量独具特色的陶器。其中,在三房湾等遗址发现的数以十万计的红陶杯,被认为是用于大规模礼仪活动的标准化产品,这反映了服务于宗教或政治需求的专业化生产模式。
第三章 石家河的绵羊与山羊:证据的批判性审视
3.1 图像记录:高度逼真的再现
石家河文化中存在绵羊和山羊的主要证据,来源于其出色的红陶塑像。这些塑像并非模糊的动物形象,而是展现了高度的自然主义风格和形态学上的准确性。
图:石家河文化陶塑动物,图取自(王劲-《浅议石家河文化陶塑艺术》)
3.2 动物考古学的困境:符号与实体的脱节
尽管拥有数以万计的动物陶塑,但在已发表的石家河文化考古报告中,却显著缺乏系统性的动物考古学分析,来证实遗址中存在大量绵羊或山羊的实体骨骼 。虽然一些报告笼统地提及“动物遗存”或用于祭祀的“烧骨”,但并未提供足以证明当地已形成规模化绵羊、山羊饲养业的定量数据。当然,由于南方土壤的酸性特质,许多骨骸与古DNA难以保存和还原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如何,根据现有信息我们可以确定石家河古人已经非常熟悉绵羊和山羊,尽管可能这些动物并非是他们主要的家养品种。
这与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后者中,羊骨是动物遗存组合中一个常见且可量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图像与实体之间的鸿沟”是解读石家河现象最为关键的证据。它强烈地暗示,石家河社会对绵羊和山羊的接纳,在性质上主要是符号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而非经济性的。是绵羊和山羊的“观念”被引入并受到珍视,而这些动物本身并未(至少在当时)成为当地稻作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陶塑,更可能是一种象征着远距离联系和精英阶层特殊知识的权力符号。
3.3 时间与传播的问题
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2500-2000年)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在时间上大致重合。绵羊符号的出现,可以由一个历时更长的、通过汉水走廊的文化传播过程来解释。然而,山羊符号的出现,几乎与山羊本身在北方石峁等地的出现(约公元前2300年之后)同步。考虑到地理上的巨大距离,这种近乎同步的现象极不寻常。它挑战了一个简单的、缓慢的、波浪式扩散模型,而指向一个更具活力的、目标明确的远距离交流体系。这表明,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中游的文化/符号包裹的传递速度异常之快,特别是对于与北方权力中心直接相关的新兴符号(如山羊)。
图:陶羊(绵羊),襄阳凤凰咀遗址古河道出土,凤凰咀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以北,南阳盆地以南的关键位置是当时的区域性中心古城,其涵盖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煤山文化时期,此地出土陶羊表明其和石家河古城文化上的一致性,亦表明“羊”可能通过汉水,南阳盆地到达石家河古城中心的路径。
第四章 铸造南北轴线:石家河的影响力网络
4.1 交流的走廊:汉水-南阳盆地的门户作用
传统上,秦岭被视为分隔黄河流域(粟作农业区)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的天然屏障。然而,一些关键的地理走廊为南北互动提供了可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汉水-南阳盆地通道。它发源于陕西,流经南阳盆地,最终汇入江汉平原,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天然过渡带和交通要道。考古学证据显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是文化交融之地。这条走廊不仅是北方龙山文化影响向南传播至石家河的最合乎逻辑的路线,也为更早期的绵羊符号沿河南下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4.2 石峁-石家河的联系:一条精英的“山羊与玉器之路”
证明石家河与北方存在高层级、远距离交流网络的最有力证据,来自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在这一时期,石家河与远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强大政体——石峁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联系 。这种联系通过一系列高度相似的、作为精英阶层权力与地位象征的玉器得以体现 。这些关键的共享器物类型包括:
-
玉牙璋:作为石峁文化的标志性礼器,其影响远达长江流域,在石家河文化圈内也发现了风格相似的牙璋 。
-
玉鹰笄与玉虎头:这些是后石家河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然而,在遥远的石峁遗址中也出土了形态几乎完全相同的器物 。
图:玉兽面(山羊) 后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400-2000年),无出土记录,沐文堂珍藏
这种在最高价值物品上的共享物质文化语汇,是这两个相距甚远的超级政体精英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交流网络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条以玉器为载体的交流路线,可被视为一条史前的“玉器之路”,其出现比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早了近两千年 。鉴于山羊在中国最早出现于石峁,这条精英通道也极有可能是将山羊这一北方新符号迅速传递到南方的“山羊与玉器之路”。
4.3 交流机制与羊符号的转移
基于上述证据,可以构建一个解释石家河羊、山羊陶塑来源的完整逻辑链条。首先,绵羊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物种,其知识和图像沿着汉水等通道,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文化渗透过程,逐渐为长江中游的居民所知。其次,山羊作为较晚进入中国,且与北方强大的石峁政体直接相关的动物,其符号意义更为特殊和新颖。关于山羊的知识与图像,正是沿着后石家河与石峁之间以玉器为代表的精英物品交换网络,作为一个“声望物品组合”(prestige goods package)的一部分被迅速传播到了南方。
结论:石家河——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核心推动者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石家河文化中早期出现的、制作精良的绵羊和山羊陶塑,并非一个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而是该政体作为长江中游超级大国地位的必然产物。
通过对绵羊和山羊不同传播历史的梳理,以及对“图像与实体脱节”现象的深入剖析,可以明确这些动物在石家河社会主要是作为一种声望符号而被接纳的。它们的图像通过至少两条不同的路径和机制抵达长江中游:绵羊符号可能通过汉水走廊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文化渗透;而山羊符号则通过一条连接石家河与北方石峁政体的精英交流网络被迅速传递。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峁文化之间共享的高规格玉器组合,为这条北方通道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物证。
石家河政体绝非一个被动接受北方文化辐射的边缘区域,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广域互动圈中一个积极且极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其高度分化的社会、以礼仪为驱动的经济模式,以及对异域声望物品的巨大需求,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文化引力中心。石家河的精英们主动寻求并重新诠释外来符号,以巩固自身权力,并在此过程中,为编织那些最终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基础的、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扮演了至关重要的、领先性的角色。因此,石家河那些小小的陶羊,并非仅仅是史前艺术的珍品,它们更是一个被遗忘的南方王朝在全球史黎明时期,与外部世界建立广泛联系的辉煌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