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乾道年间的蜀道上正蹲在船头,用竹笔在纸卷上记录着沿途见闻。他叫范成大,刚从成都顺岷江而下,但当他抬头望向岸边的茶棚,听见茶客们用浓重的乡音争论”京洛音”该叫”虏语”还是”鲁语”时,突然意识到:这片被他称为”蜀地”的土地,藏着比地理景观更惊人的秘密——它不仅是”华人”的重要祖地,更可能是华夏神话中”盘古”“中国”传说的发源地之一。
“
四人:
四川人的多元身份图谱
范成大的《吴船录》(来自网络)
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录了一段看似普通的观察:
“虽不与蕃部杂居,旧亦夷,俗号为’四人’。四人者,谓华人、巴人及廪君与盘瓠之种也”。
这里四川地界上的“四人”,是南宋初年四川居民对自身族群的概括性称谓。拆开来看:
华 人
是对“遵循华夏礼义之民”的泛称;
巴 人
川东土著,商周时期便以勇猛善战著称;
廪 君
巴人传说中的祖先,《华阳国志》载“巴人出自廪君”;
盘瓠之种
西南少数民族(如苗、瑶)的图腾后裔,《山海经》载其祖先为高辛氏帝喾的神犬盘瓠,因战功娶帝女而繁衍。
在范成大的记录里,它们被并列称为“四人”,共同构成了蜀地居民的身份标签。“四人”的本质是蜀地居民对自身族群的概括性称谓——无论出身巴人、廪君还是盘瓠之后,只要共享农耕伦理、祭祀传统、语言习俗,便被共同视为”华人”。这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恰恰是“华人”最本真的模样。
“四人”——蜀地居民的身份标签(来自AI)
《石湖诗集》里的“中国”
如果说《吴船录》揭示了四川居民的多元身份,那么范成大在《石湖诗集》卷十七《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中的另一段记录,则暴露了蜀地与中原文化的深层互动:
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
范成大的《石湖诗集》(来自网络)
这里的“虏”“鲁语”之争,表面是方言称呼的变化,实则是蜀地文化认同的缩影。
所谓“京洛音”,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官话,代表着赵宋王朝的正统声音。可在蜀地人听来,这声音却成了”虏语”——“虏”字虽贬,却暗含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我们蜀地有自己的语言规矩,你们中原的“官话”,在我们这儿不过是“外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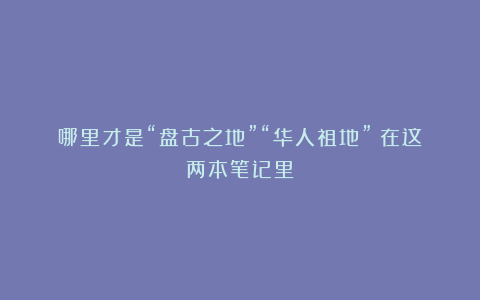
这种态度并非空穴来风。蜀地自古有“天府之国”的富庶,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屏障,历史上多次成为割据政权的舞台(所谓“僭伪”),这里,范成大提到蜀地曾被蜀人自称“中国”,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与我们之前的推理轮完全吻合,四川自古以来上古就自称中国,这里只是范成大用后世帝王角度,将它视为僭越,是站在了后世帝王角度,但它确实陈述了一个“蜀本中国”的事实。当蜀地人将中原官话称为“虏语”,本质上是在说:“我们的声音,才是这片土地的正音”。
蜀国地图(来自网络)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斥”并非针对华夏文明本身。范成大在《吴船录》里写过,蜀地人虽嫌中原话难懂,却对《论语》《孟子》里的道理熟稔于心;他们说着难懂的乡音,却在清明祭祖时行华夏古礼,在中秋赏月时吟诵着和江南一样的诗词。所谓“虏语”的称呼,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傲娇”——我们认可你代表的华夏文明,但我们更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盘瓠与盘古:
四川作为”华人祖地”的神话密码
如果说“四人”的称谓和“虏语”“鲁语”的转变,揭示了四川居民的文化认同逻辑,那么《吴船录》中提到的”盘瓠之种”,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古老的神话——它或许能解释为何四川被称为”盘古之地”。
盘瓠是中国南方民族(如苗、瑶、畲)的共同祖先神话。《山海经》载:
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蓠,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这只名叫盘瓠的神犬,因战功娶高辛氏之女,最终繁衍出南方多个少数民族。
盘瓠画像(来自网络)
但鲜为人知的是,盘瓠神话与华夏创世神话“盘古”存在微妙关联。学者考证,“盘瓠”与“盘古”在古音中极为接近(均属“帮母东部”),可能是同一神话原型在不同地区的演变。更关键的是,四川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自古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从成都出发的商队经云南、贵州进入东南亚,带去了青铜器、丝绸,也带回了各地的神话传说。盘瓠作为“跨民族神话符号”,很可能通过这条路线传入四川,并与本地信仰融合。
南方丝绸之路(来自网络)
范成大笔下的“盘瓠之种”,本质上是四川先民对自身文化源头的追溯:他们既承认与中原华夏文明的联系(通过神话母题的共享),又保留了地域特色(通过图腾符号的差异)。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恰恰是“华人”最本质的定义——认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礼义、伦理、经典),同时包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当我们今天谈论“四川人是华人”时,范成大的“四人”记录正是最生动的注脚——那些在南宋初年自称“华人”的巴人后裔、廪君子孙、盘瓠传人,那些说着难懂乡音却坚守礼义的蜀地百姓,早已用行动证明:四川不仅是”华人”的重要祖地,更是华夏神话中“盘古”精神的活态传承地。
结语:
范成大的笔记,解码
四川的“华人基因”
从《吴船录》的“四人”到《石湖诗集》的“虏语”,范成大的笔记里藏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四川居民的身份认同,从来不是单一的血缘或地域标签,而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多元融合体。他们既保留着巴人、廪君、盘瓠后裔的地域特色,又通过农耕伦理、祭祀传统、经典传承,与中原华夏文明深度绑定;他们用“华人”自称,用”虏语””鲁语”调侃中原口音,本质上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我们认同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但我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或许就是范成大留给后世的最大秘密:四川不仅是地理上的“天府之国”,更是文化上的“华人重要祖地”。它用多元的基因、包容的胸怀、独特的方言,诠释了“华人”最本真的模样:不是血脉的纯粹,而是文化的认同;不是地域的割裂,而是精神的共鸣。
四川在中国地形图的位置(来自网络)
当我们今天站在成都的街头,听见茶客们用川音争论“鲁语”与“虏语”的区别,或是在博物馆里看见三星堆青铜神树与中原礼器的相似纹路,或许会突然明白:范成大笔下的”四人”从未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每一个认同华夏文明的四川人心里。
(感谢网友 @一域无疆 提供线索)
【版权声明】
排版| 德之佑文化
图片| 翔子史前推理师
文字| 翔子史前推理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