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矿区的觉醒者
1906年,孔原生于江西萍乡,一个贫寒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去世后,他便跟随姑父一同生活。1925年,孔原在萍乡中学教书之时,加入了党组织。他白天给学生讲国文课,晚上在矿区创办夜校,教工人识字。
莫斯科的求学者
1928年春天,孔原收到通知,让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带着三块银元,经过半个月时间,他终于到达莫斯科。
白区里的破冰人
1931年叛徒叛变,致使上海党组织几乎遭遇覆灭之灾。孔原临危受命,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在法租界租下石库门的房子,让妻子许明扮作待产的孕妇,把油印机巧妙藏在婴儿床当中。有次巡捕突然上门检查,许明捂着肚子躺在床上,发出呻吟之声,孔原在厨房,搅动锅中的中药,药香与油墨味相互混杂的味道,让巡捕捏着鼻子退了出去。
1933年,在天津孔原以陈掌柜这一身份,经营着一家文具店,其实他在重建北方的党组织。
有一次他在茶馆发现交通员被特务跟踪,他假装不慎失足撞翻了茶桌,用碎瓷片在桌下刻了个箭头,从而帮同志摆脱了盯梢。
在察哈尔,他在深夜悄然潜入抗 日同盟军营地之中,紧紧握住吉鸿昌的手,说:我们的枪,应该精准地对准小日子,绝不应朝自己人射击。两人谈至天亮,敲定了联合抗 日的计划。
重庆的潜伏者
1939年的重庆,孔原承担组织方面的工作,时常前往七星岗的陶园茶馆,进行碰头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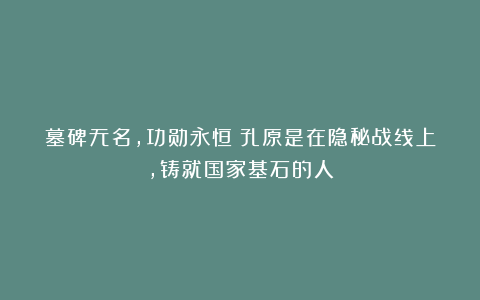
他习惯要一碗沱茶,借助茶盖轻轻点一下桌面,再稍作停顿点两下,接下来快速点三下,以此表示安全;倘若把茶碗,朝左边推动大约两寸的距离,便成为速撤信号。有次交通员老王没来赴约。在他常坐的座位上,那把竹椅,它的藤条断了三根。这便是约定的危险信号。
他果断地绕道三条街,用鞋底轻轻在巷口的电线杆上蹭了蹭,那是通知下线暂停联络的暗号。
1940年,地下党遭遇重创之后,孔原在油灯前撰写总结。他以简洁明快的方式梳理成总结:隐蔽并非躲藏,而是将根深深扎进群众之中;埋伏并非等待,而是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
周 总 理看到这些字时,用红笔圈了一圈又一圈: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要让每一个交通员都牢记于心。
新海关的改革者
1949年10月,孔原走马上任新中 国第 一任海 关 总 署 署 长。他带着工作组跑遍所有海关,在大连港发现旧海关账本里,竟有鸦 片进口税一栏,气得把账本摔在桌上:帝 国 主 义用鸦 片毒害我们,咱们要把海关变成铁闸门。制定《暂行海关法》时,有人提议直接搬苏联模式。孔原始终坚持调研:苏联属于大陆国家,我们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必须防备帝 国 主 义的走 私行为。
他对农民急需的化肥,予以免税;对洋香水,却课以重税。1953年负责对朝援助时,美 国封锁了海面。他用渔船装载着粮食,在夜里跟随运煤船前行,那煤烟遮挡住了星光,居然让物资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情 报战线的守护者
1962年,在人 民 大 会 堂举行庆典时,他留意到一个摄影师,总在贵宾席附近踱步,那皮鞋铮亮铮亮的,却在裤脚沾染了些许水泥。真正的摄影师,早该选景拍摄了。他通知了警卫,从那人的相机里,搜出了微型窃 听 器,在那人鞋底发现了一封用密蜡封好口的信。
1990年9月,孔原病逝前,用微弱的声音对守护在旁的家人说:别搞追悼会,别写回忆录,咱们做的事,让后人知道个大概就行。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墓碑上只刻着孔原同志之墓,没有生平没有功绩,每年清明,会有几个戴深色帽子的老人,在墓前放上一束野菊,鞠几个躬默默离去。
这些在隐蔽战线走了一辈子的人,就像深巷之中的老酒,闻着没什么香气,打开才知道有多醇厚。他们的名字或许永远不会,出现在头版头条上,但那些在暗夜里传递的情 报,在枪口下守住的秘密,早已成为国家大厦里,非常坚实的基石。当我们在阳光之下漫步时,别忘了曾有一群人,用一生的沉默,换来了这份现世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