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搜了一个柏垭赶场视频,依稀可见童年赶场模样
那时候日子穷,鸡公石下的永乐村人都掰着指头数赶场天。三条山路像三根麻绳,系着双龙场、田公场和柏垭场。一四七吃麻糖,二五八喝醪糟,但只有三六九的柏垭场,能勾得我整宿睡不着觉。婆婆总戳着我的脑门笑:”你个油茶馓子喂大的馋猫,莫不是王大爷家灶王爷托生来讨债的?”可她自己不也偷偷把帕子角洗得发白,就为多装几个钢镚儿?
踩着露水翻过山头,老远就能望见柏垭场的青瓦屋顶。老街的石板路被几代人的脚板磨得发亮,石板缝里还嵌着牛车轮子碾出的凹槽。最馋人的是那棵歪脖子黄桷树,树荫底下支着油布棚,王大爷的油茶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把整条街都熏得香迷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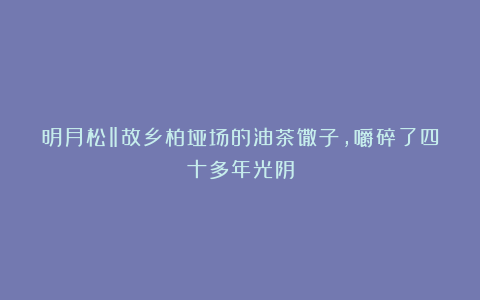
“王大哥,照旧两碗!”婆婆把帕包往裤腰上一塞,铜纽扣撞出清脆的声响。王大爷叼着长烟杆应着,皲裂的手抓起铜勺在米浆锅里划圈。那米浆是头天晚上就泡好的,籼米掺糯米,熬得跟猪油似的浓稠。现炸的馓子堆得小山高,他抄起一把”咔嚓”捏碎,撒上腌得脆生生的大头菜丁,再淋勺红亮的辣油——那油是拿菜籽油和着八角桂皮熬的,香得人直吞口水。
我蹲在石阶上捧着粗瓷碗,烫得直吹气。婆婆总笑我”猴急”,却悄悄把自己碗里的馓子往我这儿拨。咬一口馓子,”咔崩”一声脆响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再混着米糊一嚼,辣得鼻尖冒汗,又舍不得停下。有回下大雨,雨水顺着油布棚往下淌,王大爷往我们碗里多抓了把馓子:”吃热乎点,山路滑哩!”末了还往我兜里塞块灶糖,说是”小馋猫的添头”。
后来才晓得,这碗油茶里藏着老辈人的讲究。王大爷的馓子为啥特别脆?原来面团要揉到三光,发面得看老天爷脸色,炸的时候还得守着油锅里的泡泡数时辰。可那时候哪懂这些?只记得婆婆用蓝布帕子给我擦汗,自己却抿着碗边的米糊,说”我就好这口米汤”;记得王大爷缺了门牙的笑,和他总也洗不干净的蓝布围裙。
如今柏垭场的老街翻新了,黄桷树还在,只是树下没了油茶摊子。偶尔闻到油茶香,总想起鸡公石下婆婆竹烟杆敲门槛的声音,想起她就着煤油灯装烟丝的模样。那碗冒着热气的油茶,哪里只是吃食?分明是裹着粗布衣裳的温暖,是走十里山路才够得着的甜,是鸡公石下穷日子里最亮堂的光。
互动话题:
你小时候最馋的吃食是啥?有没有哪个味道,让你一想起来就红了眼眶?来评论区唠唠,说不定咱们还是老街坊呢!要是你也有压箱底的老故事,欢迎私信分享,说不定下一篇文章,就藏着你的回忆!
袁天文‖百年烟火里阆中油茶馓子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