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定远县。
张县令刚来上任,师爷便捧着一叠卷宗,面色凝重地呈了上来。
“大人,此乃一桩已决之案,只待秋后问斩。前任县令已审定,还请大人过目。”
张县令微微颔首,展开卷宗,目光扫过,眉头却越皱越紧。
案犯杨净云,年方二十,是个寡妇。指控其长期虐待婆婆田氏,致田氏不堪忍受,自缢而亡。邻里作证,杨净云本人亦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画押在手。
然而,卷宗上的描述,与张县令此刻在堂下看到的人,截然不同。
那杨净云虽身着囚服,却难掩其清丽姿容。她身形纤细,脸色苍白,但脊背挺得笔直,一双美眸中并无凶戾之气,只有一片死水般的沉寂与绝望。面对堂上问询,她既不喊冤,也不求饶,只重复着一句话:
“民妇不孝,虐待婆婆,致其身亡,罪该万死。”
这太不寻常了!一个如此年轻貌美的女子,何以对性命毫无留恋?那冷静的神情下,分明压抑着巨大的痛苦。张县令心中疑窦丛生,此案,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他试图温言引导,甚至厉声恫吓,可杨净云如同吃了秤砣铁了心,咬死是自己所为,再无他言。
无奈,张县令只得挥手:“押回大牢,严加看管!”
看着杨净云的背影消失在公堂门口,张县令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需要一个突破口,让杨净云开口。
退堂之后,张县令并未回后衙休息,而是独自在书房内踱步。烛火摇曳,映照着他沉思的面容。杨净云那绝望而隐忍的眼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必有冤情!”他笃定地自语。
硬审显然不行,需用奇招。他目光扫过堂下侍立的众衙役,最终落在了一个面相憨厚、名叫周无后的衙役身上。他早听闻此人性格耿直,且……颇为惧内。
一个计划在张县令心中迅速成型。
“周无后!”
“小的在!”
“本县命你即刻回家,收拾行装,速去速回!有紧急差事需你前往邻县办理,不得延误!”张县令语气严肃,不容置疑。
“是!大人!”周无后不敢怠慢,小跑着回家去了。
约莫半个时辰后,周无后气喘吁吁地赶回衙门复命。
不料,他刚踏入二堂,迎接他的便是张县令的雷霆之怒!
“啪!”惊堂木重重拍下,吓得周无后膝盖一软。
“混账东西!本县让你速去速回,你竟敢在家拖延如此之久!延误公务,该当何罪?!”张县令声色俱厉,目光如电。
周无后懵了,结结巴巴地解释:“大……大人,小的不敢拖延,只是收拾行装……”
“还敢狡辩!”张县令打断他,“本县早就听闻,你家中有一悍妻,名唤路燕,平日里对你非打即骂,你畏之如虎!定是此次回家,又被那泼妇缠住,误了时辰!是也不是?”
周无后被说中心事,面红耳赤,讷讷不敢言。
“来人!”张县令不再给他机会,厉声下令,“即刻去往周无后家中,将那误事的泼妇路燕拘来衙门!本县倒要看看,是何等妇人,敢误公务!”
“大人!大人开恩啊!此事与内人无关啊!”周无后吓得连连磕头。
然而,衙役们已领命而去。不多时,一个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几分泼辣之气的年轻妇人被带了上来,正是周无后之妻路燕。
她尚未搞清楚状况,张县令便不分青红皂白,以“阻碍公务”之罪,下令:“拖下去,重打十板!”
“冤枉啊!民妇冤枉!”路燕的惊叫声和板子落在皮肉上的闷响回荡在公堂之上。周无后跪在地上,心痛又无奈,浑身发抖。
行刑完毕,张县令冷声道:“将此泼妇押入大牢,严加反省!择日再审!”他特意对押解的衙役使了个眼色,“就关在……死囚杨净云那间牢房旁。”
路燕被粗暴地推进一间牢房,臀部火辣辣地疼痛,心中更是冤屈与愤怒交织。她性格本就强势,平白无故遭此大难,岂能善罢甘休?
“狗官!昏官!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冤枉好人!你不得好死!”她一进牢房,便扒着牢门,对着外面破口大骂。
骂声持续了将近半夜,直到她嗓子嘶哑,几乎发不出声,才颓然地滑坐在地,低声抽泣起来。
“这天底下……哪能没有冤枉的事情呢……”
一个幽幽的,带着几分沙哑和疲惫的女声,从隔壁牢房传来。
路燕一愣,止住哭泣,透过木栅栏的缝隙望去。借着走廊微弱的油灯光芒,她看到隔壁牢房里,一个白衣女子靠墙坐着。
那女子正是杨净云。
杨净云望着虚空,眼神空洞,继续说道:“就说我吧,没几日可活了,却还是一肚子的冤枉,强忍着往肚子里咽……你无非是被他们打了板子,关几日也就出去了……何必……何必再骂了呢……”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块巨石,投入了路燕的心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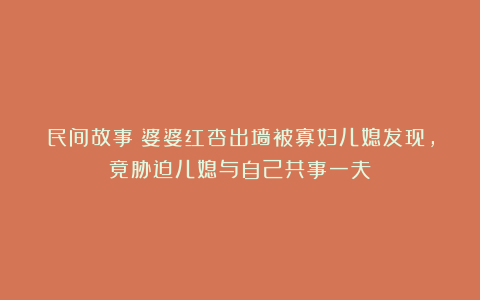
路燕忘了自己的疼痛,瞪大了眼睛。这个被判了死刑的女犯,竟然说自己冤枉?
而此刻,牢房阴影角落里,一个奉命潜伏在此的衙役,将杨净云这“一肚子冤枉”的低语,一字不落地听入了耳中。他眼中精光一闪,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牢,疾步向张县令的书房奔去。
“大人!大人!那杨氏在牢中,亲口对路燕说她有一肚子冤枉!”
张县令正在书房假寐,闻听此言,猛地睁开双眼,精光四射!
“升堂!”
三更时分,县衙大堂再次灯火通明。
杨净云和路燕被带到了堂上。
张县令目光如炬,直视杨净云:“杨净云!本县已知你有冤情!如今公堂之上,本官为你做主,你将那日未曾言明之事,从实招来!不得再有隐瞒!”
杨净云浑身一颤,抬头看向张县令,看到他眼中不容置疑的坚决,再看到一旁路燕好奇而关切的眼神,她心中那道用绝望筑起的高墙,轰然倒塌。
积蓄已久的委屈、恐惧和痛苦,化作滚烫的泪水,汹涌而出。
“大人——!民妇……民妇冤枉啊——!”
她伏倒在地,泣不成声,终于将那段不堪回首的隐痛,和盘托出。
她嫁入夫家,原本夫妻和睦。可不到一年,丈夫急病身亡,紧接着公公也悲伤过度,随子而去。家中只剩她与婆婆田氏相依为命。
婆婆田氏将丧子丧夫之痛全部归咎于她,骂她是“扫把星”、“克夫命”。从此,杨净云便陷入了无尽的折磨之中。动辄打骂,言语羞辱如同家常便饭。所有的家务重担,田氏都推到她一人身上。
“民妇念及与亡夫情深,又觉婆婆年老丧子,心中悲苦……故而……故而从未有一句怨言,只盼着她能慢慢好起来……”杨净云的声音哽咽,闻者动容。
然而,她的忍让换来的不是怜惜,而是变本加厉的欺凌,以及……更可怕的……
那一夜,她起夜时,无意中听到婆婆房内竟有男人的声音!她心中惊疑,悄悄靠近,竟透过窗缝,看到婆婆田氏与隔壁那五十多岁的流浪汉王老汉,正在行那苟且之事!画面不堪入目!
她心中大惊,脚下发软,不慎弄出了声响。
田氏与王老汉破门而出,见丑事败露,两人脸上竟无半分羞愧!王老汉立刻上前,用他那肮脏的手死死捂住她的口鼻,田氏则利落地拿来麻绳,将她捆了个结结实实,拖回屋内。
田氏撕下了所有伪装,面目狰狞地对她说:“既然你都看见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和老王早就情投意合!现在给你两条路选:一是死,二是乖乖做老王的小妾,以后我们三人一起过!”
杨净云拼命挣扎摇头。
田氏冷笑道:“我忘了,你现在没得选!你放心,我不杀你,我让老王用强的!等生米煮成熟饭,成了老王的人,我看你还有没有脸说出去!还有,想想你那住在城外的爹娘!你若敢将今日之事透露半句,老王立刻就去杀了他们!”
杨净云瞬间停止挣扎,只见老王淫笑着扑向自己,极度的惊恐与屈辱之下,她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待她再次醒来,天已微亮。而她看到的,是悬在房梁上,早已气绝身亡的婆婆田氏!
王老汉站在一旁,阴恻恻地对她笑道:“你婆婆是自觉无颜面对世人,畏罪自杀!你若是想让她死后名声扫地,被千人指万人骂,你就尽管去报官!别忘了,你爹娘……”
杨净云心如死灰。她深爱亡夫,不忍其母死后蒙羞,更害怕连累爹娘丧命。自己已然受辱,清白已毁,活着还有何意义?不如将这所有的罪孽都扛下,保全那最后一点体面,换取父母的平安。
于是,她选择了认罪,一心求死。
杨净云的供述,让整个公堂之上一片哗然!衙役们面面相觑,脸上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
他们原以为审的是虐婆悍妇,没想到背后竟是如此曲折悲愤的冤情!
路燕更是听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手刃了那对狗男女!她此刻完全明白了张县令的苦心。
张县令面色阴沉,强压着怒火。真相已然大白,杨净云虐待致死人命之罪不成立!
“杨净云,你受委屈了。”他沉声道,“此案已然明晰,你婆婆之死与你无关!本县现判你无罪,当堂释放!”
“多谢青天大老爷!多谢青天大老爷!”杨净云泣不成声,连连叩首。
但张县令的眉头并未舒展。
他还有个疑问:田氏当夜还在胁迫儿媳,为何转眼就“畏罪自杀”?这不合常理!
“来人!”他再次下令,声如寒冰,“即刻前往捉拿王老汉到案!本县要亲自审问,田氏究竟是如何’自杀’的!”
衙役们领命,如虎狼般出动。
然而,王老汉住处早已人去屋空。这更坐实了他的嫌疑。张县令下令全城搜捕,终于在两日后,将试图逃往外地的王老汉缉拿归案。
再次升堂,面对铁证和张县令的威严审讯,王老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瘫倒在地,交代了所有罪行。
原来,那夜杨净云昏厥后,王老汉看着年轻貌美的她,再对比人老珠黄的田氏,恶向胆边生。他嫌弃田氏年老色衰,恐其日后成为拖累,一心想独占杨净云,于是竟狠下毒手,趁田氏情迷意乱欲罢不能的时候,用绳索勒死了田氏,随后将其尸体悬挂房梁,伪装成自缢的假象。并以此嫁祸威胁杨净云,逼其就范。
“恶贼!竟如此狠毒!”张县令怒发冲冠,“杀人性命,诬陷贞妇,其心可诛!来人啊!将罪大恶极的王老汉押入死牢,判斩立决,上报刑部,秋后处决!”
冤情彻底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