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枉啊!大人!”
朱惠飞跪在冰冷的县衙青石板上,额头紧贴地面,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他刚刚陈述完父亲留下巨额遗产,恳请大老爷做主分家。
堂上,年轻的沈县令,面沉如水。他刚刚到任三月,以明察秋毫著称。
“朱惠飞,你口口声声说父亲留下满缸金元宝,本县问你,那口缸,现在何处?”
朱惠飞一愣,抬起头,脸上血色褪尽:“回……回大人,小人……不知。”
“不知?”沈县令眉峰一挑,猛地一拍惊堂木,声震屋瓦,“好你个刁民!连遗产在何处都不知道,就敢在公堂之上信口开河,污蔑兄嫂,企图讹诈家产!来人啊!将朱惠飞拖下去,重打十棍,轰出衙门!”
衙役上前,不由分说将惊愕的朱惠飞拖到堂外,紧接着一阵惨叫声传来。站在一旁的兄嫂朱大常和尹觉静,低着头,嘴角却难以抑制地微微上扬。
朱惠飞被扔出县衙大门,挣扎着爬起,一瘸一拐回到家中。妻子赖月菁见他背上血迹斑斑,惊得花容失色,忙上前搀扶。
“夫君,这是怎么了?”
朱惠飞面如死灰,将堂上遭遇诉说一遍,末了,悲愤道:“那狗官!定是收了大哥大嫂的好处!爹娘在天之灵,怎容他们如此欺我!”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只觉得天地不公。
与此同时,朱家大宅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哈哈!真是老天爷都帮我们!”尹觉静一扫之前在公堂上的惴惴不安,容光焕发,亲自给丈夫朱大常斟了一杯酒,“那蠢货县令,三言两语就被糊弄过去!这下好了,再没人敢提分家的事了!”
朱大常接过酒杯,脸上却无多少喜色,反而带着一丝忧虑:“娘子,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二弟他……”
“过分什么?!”尹觉静柳眉倒竖,一把夺过酒杯,“你那好弟弟,整日里贼眉鼠眼地盯着我看,还出言调戏,指不定安了什么龌龊心思!再说,那缸金子,本就是朱家的,你是长子,多占些怎么了?要不是我机灵,差点就被他分走了!”
她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狠厉,压低声音道:“幸好那蠢官没深究……那口缸,埋在树下终究不保险,过几日风头过了,得赶紧想法子转移出去……”
朱大常看着妻子窈窕却刻薄的背影,想起弟弟被打的惨状,心中愧疚,一声无奈的叹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朱家宅院一片宁静。
突然,急促的砸门声和衙役的呵斥声打破了这份平静!
“开门!官府办案!”
朱大常和尹觉静连滚带爬地出来开门,只见沈县令亲率大队衙役,面色冷峻地站在门外。
“朱大常!邻县上月发生一起劫杀官银的重案!现有线报指认,你涉嫌参与其中,赃银就藏于你家!来人,给本县搜!掘地三尺,也要把赃银找出来!”
“大人!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朱大常吓得魂飞魄散,扑通跪地,磕头如捣蒜,“小人是本分商人,从未做过违法之事啊!”
尹觉静也脸色煞白,强作镇定道:“大人,定是有人诬告!我家干干净净,哪有什么赃银?”
“是否诬告,搜过便知!”沈县令不为所动,负手而立,目光如鹰隼般扫过庭院。
衙役们冲进朱家,翻箱倒柜,一时间鸡飞狗跳。朱大常夫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院中那棵老槐树下。
怕什么来什么!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就听一名衙役在老槐树下高声禀报:“大人!树下泥土松软,有挖掘痕迹!”
“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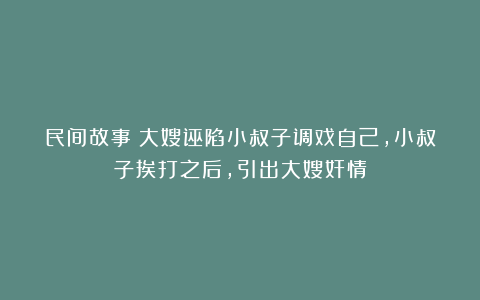
几把铁锹奋力挥下,很快,一口沉重的、密封的大缸被抬了出来。缸口泥封被敲开,里面赫然是满满一缸黄澄澄、耀人眼目的金元宝!
“赃物在此!朱大常,你还有何话说?!”沈县令厉声喝道。
朱大常看着那满缸的金元宝,心中恐惧,他涕泪横流,不顾一切地嘶喊:“大人!这不是赃银!这不是啊!这是……这是家父留下的遗产!是小人父亲行商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千真万确!求大人明察!小人愿签字画押证明!”
他生怕说慢一秒,那“劫杀官银”的罪名就坐实了。
沈县令嘴角几不可察地微微一翘,示意书吏上前记录。“哦?你确定?公堂之上,可容不得反复!”
“确定!万分确定!这就是我朱家的遗产!”朱大常抢过笔,颤抖着在口供上按下手印,仿佛那是救命稻草。
尹觉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想要阻止却为时已晚,一股凉意从脚底直窜头顶。
沈县令收起口供。
“传朱惠飞、赖月菁上堂。”他淡淡吩咐,又看向面如死灰的朱大常夫妇,“也请二位,随本官回衙门一趟吧。”
县衙公堂。
沈县令将口供掷于堂下:“朱大常,你亲口承认,并画押确认,此缸金元宝乃你父遗产。那么,几日前公堂之上,你与你妻子吴氏,为何坚称家无余财,反诬朱惠飞讹诈?”
朱大常瘫软在地,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哭喊道:“大人!是小的糊涂!是小的听了贱内尹觉静的挑唆!她……她总在我耳边说二弟……二弟偷窥调戏于她,行为不端,我……我一时昏头,又贪图家产,才……才做了这昧良心的事啊!”他将责任一股脑推给妻子。
“朱大常!你个没良心的软骨头!”尹觉静又惊又怒,尖声骂道。
“朱尹氏,你为何凭空污你小叔清白?朱惠飞可曾真的调戏于你?”
县令目光如炬,尹觉静浑身一颤,最后的心理防线也土崩瓦解。
她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声音细若蚊蝇,带着哭腔:“没……没有……朱惠飞他没有调戏我……是民妇……是民妇胡编的……”
“为何要胡编乱造,诬陷至亲?”沈县令步步紧逼。
尹觉静羞愤欲死,却不得不招供:“因为……因为民妇与邻街的货郎王八高……有……有私情,有一次……被朱惠飞无意中撞见……民妇怕他将丑事告诉朱大常,便想把他赶出家门……独吞家产,也是……也是顺带的……”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
衙役们面露鄙夷,朱大常更是如遭雷击,难以置信地瞪着与自己同床共枕多年的妻子,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朱惠飞和赖月菁也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嫂子竟如此恶毒。
真相大白。
沈县令沉声宣判:
“本案已明!朱家遗产,确系其父所留,兄弟二人皆有份。原应均分,但念及朱大常将幼弟抚养成人,亦付出良多。本县判定,遗产兄弟均分后,朱惠飞自愿从其所得中,取出二百两银子,赠与兄长朱大常,以报养育之情。朱惠飞,你可愿意?”
朱惠飞此刻早已对县令佩服得五体投地,若非大人妙计,他恐怕永无沉冤得雪之日。他感激涕零,重重叩首:“草民愿意!多谢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
朱大常满面羞惭,无地自容。
沈县令又看向尹觉静,眼神冰冷:“朱尹氏,你品行不端,与人私通,搬弄是非,诬陷亲族,虽律法难究其全罪,然其行可鄙,其心可诛!望你日后洗心革面,恪守妇道!若再兴风作浪,本县定不轻饶!”
尹觉静瘫软在地,面无人色,她知道,自己在这城里,已是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