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溯,一组民国老照片映入眼帘,每一帧都烙印着那个时代独有的人文温度与历史厚重。
20世纪30年代,上海普善山庄的工作人员在贫民区收尸的历史场景。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经历经济大萧条、日军侵华威胁与城市人口爆炸的多重冲击。闸北、南市等贫民区聚集着大量难民、工人与乞丐,居住条件恶劣,疾病与饥荒频发。据史料记载,1930年霍乱爆发期间,普善山庄单日收殓尸体达百具,全年处理3.6万具尸棺。这些尸体多因营养不良、传染病(如天花、霍乱)或战乱死亡,部分甚至被遗弃街头。
普善山庄成立于1913年,最初以施粥、办学为主,但随着社会危机加剧,其职能逐渐转向尸体收殓。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山庄出动全部收尸车处理大世界轰炸后的2000余具遗体,耗时两日完成搬运。
普善山庄组建了由难民、残疾乞丐组成的职业收尸队,配备带铁箱的三轮车与薄皮棺材。他们每日清晨穿梭于棚户区,遵循“三不原则”:不收外伤尸体(避免涉命案)、不碰脐带未断婴尸(避血光)、黄昏后停工(防鬼神)。收尸流程规范:登记尸体特征、用草绳捆缚、旧报纸遮面(遵民间禁忌),每具尸体可换5个铜板。
这张定格邓锡侯(左)、杨森(中)、刘文辉(右)的合影,拍摄于1935年春夏之交的成都。此时正值国民政府“统一川政”后的首次全省军事会议,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旨在整合历经二十年混战的川军各派。
1918年起,川军各派划区而治,形成23个“防区”,邓、杨、刘均曾拥兵自重。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入川,废除防区制,将川军整编成21个师,三人兵权被部分剥离(如邓锡侯45军仅辖3个师),但仍保持对部队的人事控制权。
这张摄于1948年11月中旬的照片,定格在浦口火车站货场。此时距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正式爆发(11月6日)已一周,浦口作为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与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的南端枢纽,正成为国民党军南北调防的“输血通道”。画面中,20余名士兵挤在一节30吨敞篷货运车厢内。
1948年11月,浦口火车站每日开行27列军列,其中19列前往徐州方向,8列南下上海。但因机车不足(半数蒸汽机车因缺煤停驶),调防部队常需在货场等待12-48小时。照片背景中,3列运载第96军的列车因“调度冲突”滞留浦口达3天,士兵不得不卸下车厢木板搭建临时灶台,与前来卖开水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
据战后统计,1948年11月通过浦口调防的75万国军中,约45万人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或俘虏。浦口当地挑夫后来回忆:“这些丘八(士兵)比上半年撤退下来的更惨,有的鞋都没了,拿草绳绑着脚。车上扔下来的美国罐头,都是空的,听说他们在蚌埠就被当官的卖了换金条。”
这张拍摄于1948年10月下旬的照片,取景于浦口火车站北广场。此时距淮海战役爆发仅剩十余天,浦口作为连接华北、华东的铁路枢纽,正承受着国民党军大规模调防的压力。画面中,几名士兵围聚火塘边,用捡来的木箱、枕木生火,火星溅落在他们单薄的军服上。
士兵身着1946年版棉军服者不足三成,多数穿着夏装改制的夹层衣——将两件单衣反缝,内絮稻草(见《国防部后勤总署1948年10月报告》)。按国防部规定,10月15日前应完成全军冬装发放,但据《联勤总部浦口仓库清单》显示,截至10月20日,该仓库仅收到计划量的23%,且半数为潮湿霉变的库存旧货。
更致命的是,第7兵团(黄百韬部)原定于10月10日在浦口换发美式冬装,却因“上海港口运输延误”(实为军服在码头被黑市倒卖),士兵只能穿着单衣北上,20天后在新安镇被华野追上时,许多人因冻僵手指无法扣动扳机。
生火取暖实为无奈之举,浦口火车站的军用候车室因煤炭短缺早已停供暖气,调防部队常需在露天货场等待12-36小时。士兵最初捡拾铁路废弃的枕木(含防腐焦油,燃烧时释放有毒气体),后发展到拆解货棚木板,甚至锯断铁轨旁的护栏。10月25日,浦口宪兵队记载“士兵与车站工务段冲突17起,均因争夺燃料引发”,某连长因阻止士兵拆毁信号箱,被失控的士兵用铁锹打伤。
这张拍摄于1933年8月的合影,记录了沈从文、未婚妻张兆和与九妹沈岳萌在北平西城达子营寓所的庭院中。此时距二人7月25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婚礼刚满两周,尚未正式迁入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达子营28号新居(1934年入住),暂租住在西城一处四合院。
月租12元的四合院(相当于沈从文月薪的1/8),生活虽清简却充满文人雅趣:早餐多为九妹手制的湘西米粉,午餐常配沈从文从家乡带来的腌菜;张兆和将陪嫁的苏绣屏风改作窗帘,沈从文则用稿费买了一台二手西门子打字机,用于抄写稿件。据张兆和晚年回忆,“那时二哥总说’我们三个像从不同星球来的人’——九妹懂他的湘西话,我懂他的文学梦,他懂我们的怕饿与怕冷。”
这张摄于1935年秋的照片,取景于苏州九如巷张家老宅,这是二人婚后第三年重返娘家,也是沈从文首次以“女婿”身份正式踏入苏州豪门。
1929年,27岁的沈从文初任中国公学国文讲师,第一堂课便被台下18岁的张兆和吸引。此后半年,他写下第一封情书:“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但在张兆和眼中,这位操着湘西口音、授课时紧张到冒冷汗的老师,不过是“青蛙大队”中的普通一员。她将追求者按编号分类,沈从文因频繁写信被二姐张允和戏称“癞蛤蟆十三号”(暗讽其湘西出身与门第差距)。
在持续三年的书信攻势中,他既写“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的浪漫,也剖白“我永远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点笨拙气息”的自卑。1933年结婚时,他坚持不用张家一分钱,婚礼费用来自《边城》连载稿酬,连婚戒都是请凤凰银匠打制的苗纹银环。
这张约摄于1925年的摆拍照,取景于上海威海卫路盛宣怀公馆的“愚斋”藏书楼。画面中三位盛家女性呈“品”字形围坐于桌旁:右一为盛宣怀七小姐盛爱颐(19岁),中间为盛宣怀侄孙女盛佩玉(22岁),左一为盛爱颐胞妹盛方颐(17岁),这是盛家“新旧式闺秀”的经典定格,既恪守“琴棋书画”的传统教养,又暗含对西式教育的接纳。
这张照片实为盛家有意识的“家族宣传”:1925年盛宣怀去世十年,盛氏家族因遗产分割、子弟挥霍(如盛恩颐好赌,曾一夜输掉百栋房产)渐露衰败迹象,急需通过女性成员的“才德兼备”维系门楣。照片经《良友》画报登载后,配文“盛氏三美,兼通中西,真名门淑女之范”,成为旧豪门应对时代变迁的文化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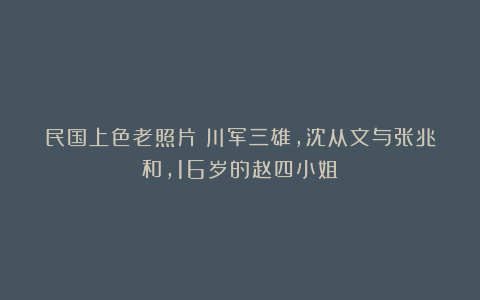
这张摄于1928年深秋的封面照,取景于天津中原照相馆(今和平路百货大楼旧址)。时年16岁的赵一荻(赵四小姐),她身着一袭纯白如雪的西式纱质公主裙,头戴一顶略显俏皮的宽檐遮阳帽,以一种慵懒而不失优雅的姿态斜倚而坐,身姿曼妙,尽显时尚经典之韵,被《北洋画报》编者形容为“东方少女的西化宣言”。
其父赵庆华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次长,急需通过女儿的“名媛形象”维系家族声望。赵一荻就读的天津中西女中(宋美龄母校)推行“新女性教育”,鼓励学生参与社交活动,此次拍摄实为校方与赵家的联合策划。
1927年天津蔡公馆舞会上,张学良对赵一荻一见钟情,但因已婚身份未敢造次。1928年秋,他在《北洋画报》第327期看到封面照,立即致电冯武越:“这女孩,我要认识。”赵庆华默许女儿拍摄封面,却反对其与张学良交往。1929年赵一荻私奔奉天(今沈阳)后,他在《大公报》连登五日启事:“四女绮霞,近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应行削除其名。”
这张摄于1928年秋日的照片,定格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前的银杏道上。北伐后,北平改称“北平特别市”,香山作为前清皇家园林,刚对公众开放十年,成为军政要员、文化名流的“后花园”。左起依次为:六哥赵燕生、挚友吴靖、赵一荻、二姐赵紫霞。这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赵庆华家眷的一次秋日雅集,亦是赵四小姐婚前最珍贵的家族影像之一。
照片原件由吴靖后人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背面有赵一荻1965年题字:“香山银杏黄时,与六哥、二姐、靖姐同游,谁能料到靖姐后来竟成了我的嫂嫂,而我与汉卿的故事,也从这年冬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