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社交媒体上一位网友对小提琴大师宁峰留言:“建议空弦单独练右手。”这番话一出,立即成为段子。令人莞尔的是,宁峰老师并未动怒,而是亲自拍了一段“练空弦”的视频作为回应,幽默而大度。
笑过之后,或许我们应该想起:音乐史上,那些如今被奉为经典的作曲家们,在他们的时代同样饱受误解和恶评。不同的是,他们的回应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怒斥不休,有的自我怀疑,有的选择坚持,有的冷嘲热讽,有的干脆冷眼旁观。但无一例外,他们都让音乐本身成为最终的答案。
愤怒直斥型:贝多芬
贝多芬几乎是被恶评围攻最多的大师之一。1804年,他的《英雄交响曲》首演时,有评论家说这是“一部冗长乏味、毫无章法的作品”;《第二交响曲》更被形容为“一条垂死挣扎却不肯死去的巨龙”。晚期弦乐四重奏,则被斥为“一个聋子的混乱幻想”……
面对这些攻击,贝多芬的反应和他的性格一样:直白、暴躁、不留情面。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痛骂乐评人是“蠢货”“恶棍”,并在一次争论中爆出那句著名的狠话:
“Mein Scheiß ist besser als dein Gedanke!”
“我的屎都比你的思想高明!”
*这句经典毒舌反驳虽广为流传,目前最早载于作家 Austin Kleon 的文章中,他援引的是传说引用,但并未提供原信的具体出处。应作为传说引用处理。
这种回应看似粗鲁,却也展现了贝多芬的核心信念:音乐的价值不由批评者决定,而由时间和人类情感来检验。事实证明,他的交响曲与四重奏早已成为西方音乐的基石,而当年的乐评人几乎无人记得。
自我怀疑型:柴可夫斯基
与贝多芬不同,柴可夫斯基性格敏感,对恶评极度在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在1881年首演后,被奥地利评论家汉斯里克(Eduard Hanslick)痛批为“臭不可闻……它让人想到除了音乐以外的一切,甚至还有难闻的气味”。(《Neue Freie Presse》,原话记录在对汉斯利克的研究与传记中)。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也曾被批评为“酒鬼般的嘈杂,充满幻野疯狂”。
柴可夫斯基在日记里经常写下自己的自卑:“我常常怀疑,我的作品是否真的有价值。”甚至连自己最受欢迎的《1812序曲》,他也嫌弃“庸俗讨好”,认为“不配我的艺术理想”。
但这种自我怀疑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创作。他没有公开争辩,而是让旋律替他发声。《天鹅湖》《胡桃夹子》《第六交响曲》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古典作品。他的“软弱”与“敏感”被音乐转化为真诚的力量,证明了另一种艺术家的回应方式:不与批评纠缠,而是继续把心声交给听众。
沉默坚守型: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的处境特殊。他被同时代人视为“贝多芬的继承人”,这既是荣誉,也成了沉重的枷锁。他用了二十多年才完成《第一交响曲》,被戏称为“贝多芬第十”。首演时,有人认为这部作品“过于沉重”“缺乏创新”,不像瓦格纳那样具有戏剧性的张力。
勃拉姆斯没有像贝多芬那样咆哮,也不像柴可夫斯基那样自我怀疑。他的选择是沉默与坚守。他坚持古典传统,以严谨的结构和厚重的和声为核心,不被潮流左右。在与瓦格纳阵营的“浪漫主义大战”中,他几乎从不公开辩论,而是用作品证明:传统并非落后,理性与深度同样可以创造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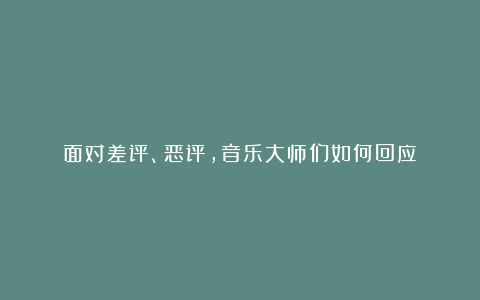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坚持是有价值的。今天,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与瓦格纳的歌剧并列,成为19世纪音乐的“双峰”。他的冷静回应告诉我们:沉默并非软弱,而是另一种深沉的自信。
冷嘲机智型:德彪西
德彪西的音乐在当时颇具争议。批评家给他贴上“印象主义”的标签,本意是贬义,暗示他音乐“虚浮不实”。德彪西对此非常不满,他在1908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
那些傻瓜所谓的’印象主义’,这个词被用得再糟糕不过了。”
更有趣的是,他化名“克罗什先生”,亲自下场写乐评,尖锐地批判法国音乐的陈腐,以及瓦格纳式的“宏伟歇斯底里”。他的文章语言机智、犀利,展示了音乐家如何用思想与笔锋来“降维打击”批评者。
今天,“印象主义”反而成为赞誉之词,德彪西的音乐也因独特的色彩和意境成为20世纪音乐的起点。他的回应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批评不是对标签的反击,而是用思想去重塑话语权。
荒诞幽默型:萨蒂
萨蒂的回应堪称艺术史上的“另类喜剧”。评论家说他的音乐“没有形式”(pas de forme),他就偏偏写出《三首梨形曲》,标题本身就是对“没形式”的嘲讽。
在他的乐谱上,常常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指示:“像一颗空心牙齿一样演奏”“轻如一个鸡蛋”。他甚至把批评者的文章原封不动贴在乐谱里,并冠以标题《惹人嫌的装腔作势者》。
这种荒诞式的幽默,让批评者显得可笑,也让音乐史多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当然,他也并非总是风轻云淡。1917年芭蕾舞剧《游行》遭批评时,他忍不住寄去一张明信片,骂评论家是“一个屁股,而且是一个不懂音乐的屁股”,结果被告上法庭,甚至坐了八天牢。
萨蒂的故事告诉我们:幽默和荒诞,也是最锋利的武器。
冷眼旁观型:斯特拉文斯基
1913年,巴黎香榭丽舍剧院,《春之祭》首演引发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骚乱。观众席上嘘声、拳头、口哨声此起彼伏,支持者和反对者打得不可开交。评论家在次日的报纸上写道:“这不是音乐,而是野蛮人的嚎叫。”(参考Nicolas Slonimsky :《Lexicon of Musical Invective》)
面对这样的场景,斯特拉文斯基没有像贝多芬一样咆哮,也没有像萨蒂那样讽刺。他只是悄悄躲到后台,从幕布缝隙中偷偷观察这场因自己而起的混乱。
讽刺的是,这份冷眼以对却成为最强有力的回应。今天,《春之祭》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与芭蕾作品之一。每一次它在世界各地奏响,都是对当年恶评最响亮的反驳。
从贝多芬的怒斥,到柴可夫斯基的敏感,勃拉姆斯的坚持,德彪西的机智,萨蒂的幽默,斯特拉文斯基的沉默,我们看到音乐巨匠们的多种姿态。他们的选择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结果都一样:作品超越了批评,时间才是最伟大的评论家。
今天,我们笑谈“宁峰练空弦”,或许更该想起这一点:真正的艺术不需要一时的掌声或嘲讽来裁决,它只需要创作者不断拉动那根属于自己的“弦”。最终,回响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