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是关于“苏报案”的重要早期史料,在这封书信的手稿中,有此前未见的关于章太炎、吴稚晖之争的记载。早在1903年7月章太炎、邹容被捕之初,二人便共同认定吴稚晖“卖友脱逃”。从狱中质疑到持续数十年的论辩,章吴之争随着时间、情绪的积累不断升级,争论重心也由“卖友”到“献策”再到“告密”而不断转移。由于章士钊的调解,章太炎在《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中删去了与吴稚晖有关的内容。这封书信刊发于1927年初出版的《甲寅》杂志,在章士钊的删削之中,亦体现出他对章吴之争的调和态度。
关键词
苏报案;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
一
“苏报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苏报》宣扬邹容《革命军》,刊发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一语直斥光绪之名,在当时堪称“大逆不道”。清廷震怒之下,慈禧太后批饬“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由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魏光焘坐镇,派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会同上海道袁树勋负责查办。面对清廷的缉拿,章太炎、邹容等人展现出勇猛无畏的革命气概。中西警探在爱国学社逐一查问,章太炎豪气冲天,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2]其后写信招邹容投案,同担大义。
章太炎像
由于《苏报》馆在租界之内,在司法主权日益沦丧的时代,案件只能在租界中的会审公廨审理,清政府为原告,章、邹等人为被告,双方都聘请了外国律师,成为了中国法律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在会审上,章太炎激烈抗辩,针对“载湉小丑”触犯清帝圣讳的罪名,援引《尔雅》“丑,类也”的训诂强加辩解,“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3],对清廷官员大加戏弄。正如孙中山所言,“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诉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4]与此同时,在苏报案的风起云涌中,亦有革命党人难以排解的是非恩怨。章太炎坚执吴稚晖“卖友”“献策”,吴稚晖矢口否认、反唇相讥,二人之间的争论、讥嘲与骂詈,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章吴之争”成为了苏报案中的一大公案,引发了后人的不断探讨。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是重要的早期史料。吴、张二人皆为章太炎挚友,太炎曾撰《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故总统府秘书张君墓志铭》,可见其交谊之深。章太炎于1903年6月30日被捕,7月2日邹容应招投案,数日后便收到吴君遂手书及墨银二百元,为其聘请律师提供了有力帮助。7月15日,苏报案公开审理,不久之后,章太炎致信吴君遂、张伯纯二人,详细描述当日情形。这封书信始刊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一卷第43号(1927年2月19日),已在苏报案的二十四年之后,其后收入《章太炎全集》。2022年冬,书信手稿(见封三)与一批章士钊书信同时出现在嘉德拍卖,且与章士钊的两份手稿同帧装裱,或出自孤桐后人。笔者有幸得之,与《甲寅》本相较,颇能见其删减改易之迹,对理解“章吴之争”的缘起本末与章太炎的心态变化,以及作为《苏报》主笔的章士钊的调和之意,皆有重要参考价值。
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手稿
手稿原文如下:
君㒸、伯纯鉴:自闰月六日入狱,七日到案,逾数日得君㒸手书,并墨银二(三)百圆,资助讼费,高义薄云,感激无量。吴稚晖以受俞明震嘱托,卖友脱逃,证据明白,已与威丹驰书日本、香港,宣布其罪。君㒸平日亦以稚晖为大人物,悲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自七日到案后,(此案)各领事与工部局坚持此狱,不令陷入内陆,事闻于伪政府,已遣伪员陈情于各国公使,公使允之,领事与工部局仍执不允。俞明震怒,令伪关道袁树勋以兵五百人,解去号袿,潜伏新衙门后,将劫以入城,捕房戒严。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而坐,数英捕驰马(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既往听诉,则闻南洋法律官带同翻译,宣说曰:“中国政府到案。”曰:“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章炳麟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载以为证,贼满人、逆胡、伪清等语,一切宣读不讳。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控告于(在)他国法院,而控告于(在)己所管辖之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诉毕,钱、程二子,自辩本无干涉,仲岐代父入狱,亦已为大众所知,当可开释。弟与威丹,罪状自重,然其所以控我者,自革命逐满而外,复牵引“玄晔弘历”“载湉小丑”等语,以为干犯庙讳,指斥乘舆,不知律师如何申辩,想亦不甚困难也。然此五人罪状虽异,单于见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原告律师已声明不出租界。惟龙积之无事可执,乃云系富有票会匪,犯事在汉口,须解至汉口裁判。而原拏牌票积之名下,只开列“著《革命书》”云云。后以著书无据,忽牵扯富有票案,以相诬陷,此语情节支离,想律师必能明辩也(不值一辩)。最可笑者,新衙门委员孙某,不甚识字,觳觫殊甚,但云公等速说,我与公等无仇无怨而已。事毕,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咽,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麟白
划线部分为《甲寅》本所无,括号部分为《甲寅》本所改,当出自章士钊之手。其中“吴君遂”作“君㒸”,为《说文解字》中的本字,可见章太炎好用古字的行文习惯。吴君遂赠送“墨银二百圆”,《甲寅》整理误作“三百圆”,各本沿用其误。在章士钊删去的内容中,涉及邹容、吴稚晖、俞明震、龙积之四人,前三人皆与章吴之争密切相关。
二
书信开头,章太炎在感谢吴君遂的帮助之后,笔锋一转,谴责吴稚晖出卖朋友。一般认为,“章吴之争”始于章太炎在1907年3月25日的《革命评论》上发表《邹容传》一文。实际上,早在1903年7月被捕之初,章、邹二人便已共同认定吴稚晖“卖友脱逃,证据明白”,在监禁中开展行动,致信吴、张及日本、香港友人“宣布其罪”。对章太炎而言,一开始并不存在所谓的“章吴之争”,这是他与邹容的并肩战斗!章、邹身处监禁之中,消息来源极为有限,何以能够确定此事?核心证据是二人入狱不久,吴稚晖前往探视,言语中漏出极大破绽。章太炎在1908年的《与吴稚晖第一书》中写道:
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须臾引去。此非独仆与足下知之,同系者尚有钱葆仁、程吉甫辈,可覆问也。[5]
俞明震与袁树勋一同负责查办苏报案,在章、邹眼中,他是不折不扣的清廷爪牙。实际上,他对革命党人颇有回护之意,在捉拿之前让儿子俞大纯招来吴稚晖,通告革命党人设法走避。但吴稚晖对章、邹等人全无示警,直到二人被抓之后前来探视,才说自己提前见到了俞明震,不仅“屈膝请安”,还吃了俞家的面条,这势必引起二人的怀疑。邹容更直接质问:“何以有我与章先生?”无论吴稚晖事后如何解释,他得知清廷查拿革命党人的消息,提前却绝口不言,这就是出卖朋友,是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自革命道义而言,章太炎、邹容谴责他“卖友脱逃”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在狱中对吴稚晖的怀疑与厌憎,构成了“章吴之争”的心理基点。
当然,无论是革命大义所在,还是苏报案的形势起伏,都不允许二人与吴稚晖过多纠缠。在革命派、清政府与列强势力的反复博弈之下,1904年5月21日,苏报案最终判决,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在牢狱中,章太炎与邹容饱受折磨,太炎曾以绝食相抗,又与狱卒搏斗而屡遭殴打、酷刑。他在狱中的佛学阅读,也是生死之际的精神挣扎。1905年,邹容不幸庾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次年在《革命评论》发表《邹容传》一文:
会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爱朓,召朓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朓即出《革命军》及《斥康有为》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6]
章太炎为邹容作传,是要“发扬芳烈,酬死友于地下”,并肩战斗也变成了自己一人的“后死之责”。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相比,《邹容传》的记述更为具体生动,寥寥数笔,革命叛徒的嘴脸跃然纸上,吴稚晖的罪名也由“卖友脱逃”变成了“通情献策”。吴稚晖读到此文,极为不满,致信反驳。“君与恒现皆存世,非如慰丹之既没,岂当由君黑白者。”[7]谓邹容死无对证,只能任由章太炎颠倒黑白。对章、邹的生死之交而言,这种说辞无异于极大侮辱,章太炎遂公开复信,怒骂痛诋,开启了数十年的“章吴之争”。
在复信中,章太炎举出了三重证据,除了上文所言吴稚晖见到俞明震“屈膝请安及赐面事”之外,还有章太炎出狱之后,从汪允中处听闻俞明震“自悔”于苏报案事,以及于张鲁望处听闻吴稚晖“献策”之事。汪允中、张鲁望所言未必可信,今人多已辨之[8]。但在章太炎眼中,则是为“证据明白”之罪状,增加了新的辅证。如果说,“屈膝请安及赐面事”来自狱中亲闻,《邹容传》中详述吴稚晖“献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告其徒曰”的沾沾自喜,又得自何处呢?恐怕不无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想象。蔡元培在《读章氏所作<邹容传>》中说:“其后《苏报》案起,章、邹诸君皆入狱,章君又以往日疑吴君之习惯,疑为吴君所陷。既有此疑,则不免时时想象其相陷之状,且不免时时与邹君互相拟议,而诟詈之。大约二年之中,神经口耳间缫返此想象,已不知若干次,故不知不觉而认为实事也。”[9]虽有“解嘲”之口吻,但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他说章太炎“时时与邹君互相拟议,而诟詈之”,更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相合,尤见蔡元培是局中的知情之人。在举证之外,章太炎复以“文体”不同加以解释。“仆作慰丹传,非法庭录供之爰书,有其事则略记其语,宁能适与声气相肖?非独仆然,自来记事者皆然。足下自命为无政府党,与法律相攻,顾于寻常记叙之言,欲以法吏录供为例,岂足下不知文体耶?”[10]史书传记与法庭供状不同,不能句句实录,容有增饰之语。这倒不是章太炎的强词夺理,而是古代史书确有其例。他在十余年后的《国学概论》中,也说《史记》《汉书》中“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11],可见这是其一贯主张。
无论如何,《邹容传》中的增饰想象有“想当然语”的破绽,给吴稚晖留下了质疑口实。二人数番通信,攻讦不已,最终只得不了了之。到了1915年修订《章氏丛书》时,章太炎大幅删减了《邹容传》的相关记述:“会虏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检察革命党事,将逮爱国学社教习吴朓,朓故惎容、炳麟,又幸脱祸,直诣明震,自归,且以《革命军》进。明震缓朓,朓逸。遂名捕容、炳麟。”[12]在这里,吴稚晖“献策”如故,但所献仅为《革命军》而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俞明震等人的对话也被删去。太炎的“史笔”更加慎重缜密,但对“史事”的认定并未改易[13]。1923年,吴稚晖在《章氏丛书》中看到此文,大为光火,遂于次年1月11日在《民国日报》上致信章士钊,针对其《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一文旧怨重提,对章太炎大加抨击,放言要“处置他一下”。数月之后,章太炎与章士钊、李根源、张继、于右任等友人募款修建邹容墓碑,增损《邹容传》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彻底删去了与吴稚晖有关的内容,仅有“会清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来检察革命党,君及炳麟皆就逮,系上海租界狱”[14]一语。
《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见《大公报(天津)》1925年 10月 19日(局部)
三
章太炎的删削倒不是担心吴稚晖的恐吓,更多与章士钊的居中调停密不可分,后者的立场与态度也反映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的文字删改之中。作为《苏报》主笔,章士钊与章吴二人“皆有厚谊”,故“曾以调人自居”。早在1913年,便曾邀请二人聚餐联欢,试图调解,但席间不过客套而已,并未谈及要害。到了1924年,吴稚晖重提旧事,章士钊在1月20日的《新闻报》发表《农治述意续》一文,在文末郑重调解:
盖俞(明震)时总办江南陆师学堂,钊先一年习军旅于是。以英年能文,为彼激赏,后虽离校而言革命,彼此情意未衰。故当时以革命党而与俞道有通疑之嫌者,应先属钊。而吾兄顾疑先生,以为己与威丹被捕,乃由先生出《驳康有为书》及《革命军》上俞告密。微论先生忠亮,不为此事。而是二书时已流布江湖间,并非奇谋阴计,何待有人密陈,俞始晓洽。吾兄身在狱中,张琴饮醪,不无闷损,言偶不检,本可相原。(中略)不谓吾兄曩岁不检之文字,弟子辑录《章氏丛书》,未即削去。[15]
《农治述意续》,见《新闻报》1924年1月12日(局部)。
章士钊为太炎义弟,情谊深厚,其时二人皆在上海,此信很可能征求过太炎本人意见。文中为吴稚晖开解“告密”之事,指出《驳康有为书》及《革命军》广为流传,本无秘密,何告之有?此语深得吴氏之心,是其后来反复置辩的要点所在。章士钊把“卖友”“献策”的问题转移到“告密”之上,对当事人乃至后人对这一公案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影响——蒋维乔在发表于1936年1月的《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亦说“章炳麟矢口断定,稚晖自诣明震处告密”[16]。吴稚晖撰写长文《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其滔滔不绝必欲辩解者,更尤在“告密”二字。在章士钊看来,“告密”是对吴稚晖的误解,与太炎“身在狱中”的愤懑之情不无关系;至于《章氏丛书》不改旧说,则是“弟子辑录”之过。前者转移重心,后者显为托辞,可见其调解矛盾时的用意之深。章太炎对此虽未公开表态,但事实上也接受了他的劝解。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的调解态度不仅关乎吴稚晖,更关系到苏报案的查办人——俞明震。在章太炎眼中,俞明震是革命党人的大敌首恶,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中,吴稚晖卖友是“受俞明震嘱托”,袁树勋在公开审理前带兵劫持,也是俞明震的怒中指使。事实上,这不过是章太炎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的一种误解。[17]在清末人物的政治光谱中,往往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进步与落后之分。俞明震素以思想“开明”著称,对革命志士颇具同情,与章士钊更有师生之谊。其子俞大纯为章士钊好友,实为革命党人,曾参与研制炸药,谋划刺杀铁良等事。于公于私,俞明震对苏报案中的革命党人都有回护之意。因此,他对上“瞒天过海”,在缉拿名单中故意漏掉章士钊、吴稚晖、蔡元培、张继等人之名;对下“通风报信”,让俞大纯招来吴稚晖,让其通告革命党人设法走避。正因如此,俞明震不久便被清廷怀疑。端方致电魏光焘指出俞大纯“剪辫入革命军”,俞明震亦“不可不防”。苏报案尚未结案,清廷便将其调回南京。对于俞明震对革命党人的苦心回护,章士钊十分清楚。他在撰于1955年的《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回忆:“又闻本案初起,查办员未定,先生恐伤士类,曾争取此案入手。到沪之日,即命大纯招吴敬恒参谒。蔡吴之逃,皆先生故意纵之。凡此种种,皆足说明俞先生之不肯名捕及余。”[18]是符合当时情境的。因此,他调解章吴之争,势必要说明俞明震对革命党人的回护,这对章太炎的激愤起到了釜底抽薪之效——吴稚晖知情不语,固有“卖友”之过。俞明震本无严查之意,又何来“献策”“告密”之说?如果说吴稚晖通过“献策”来换取自身安全,章士钊、蔡元培、张继等人皆被俞明震回护,难道都是“献策”的结果吗?至于“告密”,《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又何须吴稚晖相告呢?
明瞭了章士钊的态度,《甲寅》发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时的删削之意,亦不难理解。首先,章士钊在1924年调和章吴,在1927年编辑《甲寅》时删去与吴稚晖、俞明震的相关内容,自在情理之中。但删去这些“攻战的文章”,也未免如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所言,不免有些吃亏上当,“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19]。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手稿(局部),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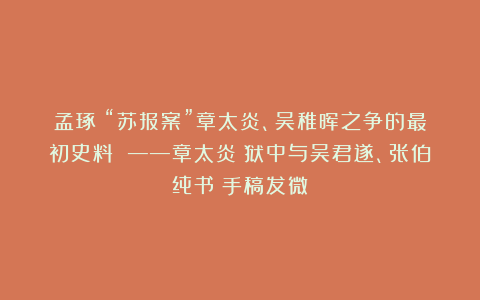
其次,章士钊删减了与龙积之有关的内容,盖其素来认为苏报案的主角只有章、邹二人,其他四人“绝不相类”,甚至有“滥窃时名”之嫌。他在作于1903年的《苏报案纪事》中说:“且此次关涉《苏报》之人物,且有与章、邹绝不相类者,名为’六君子’,若以章、邹同类并称之,辱章、邹多矣。”[20]在《甲寅》文后按语中亦说:“是案本六人,号六君子,实则除章、邹外,惟龙积之略有时望。余三人,一陈仲岐,为苏报馆主陈梦坡之子。一陈吉孚,为馆中账房。一则钱保仁也。审此,革命党滥窃时名以终者,夫岂少哉!”[21]
《又致吴君遂》,见《甲寅》第一卷第43号,第21-22页,19270219
前后观点始终未变。最后,章太炎信稿中说“然此五人罪状虽异,单于见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原告律师已声明不出租界”,此语出自李陵《答苏武书》,以“单于”谓清廷,谓其引渡之谋落空。但李陵最终投降匈奴,岂可以此自况?太炎落笔如风,偶有引喻失义之处,章士钊代为刊去,更可见其认真审慎。
四
以《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为起点,前后推敲,“章吴之争”的始末大抵清晰。从章、邹的狱中质疑到章、吴持续数十年的论争诋詈,这一矛盾随着时间、情绪的积累而不断升级,争论重心也由“卖友”到“献策”再到“告密”而不断转移。最终通过章士钊的调解,章太炎删去旧说,唯余吴稚晖扰扰不休。平心而论,在清廷的查拿之下,吴稚晖知情不告,说他“卖友脱逃”毫无问题;但俞明震回护革命,“献策”“告密”之说不免冤枉。考虑到章、邹二人在狱中的艰难困苦,以及章太炎担当“后死之责”的沉重心态,他的误解与增饰亦无可厚非。学界对于这一公案的评判,在歌颂革命的语境中以“赞章卑吴”为主,接受了章太炎的全部指控;近四十年来则屡见为吴稚晖翻案之文,又不免矫枉过正。首先,学者翻案的基本角度是吴稚晖未曾“告密”,当时亦无告密之必要,这其实延续了章士钊的旧说。但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手稿中,我们看到,章太炎、邹容对吴稚晖的质疑与谴责,首先是“卖友脱逃”——知情不告,是为“卖友”,身在狱外,是为“脱逃”,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开脱的。吴稚晖在苏报案中的污点,不能因其未曾告密而轻易抹除。其次,学者推究史实,认为对吴稚晖的评价不能简单化、绝对化,这是对的。但倘就此走向反面,对革命者缺乏“同情之了解”,仅将其误解归因为“个性”与“情绪”,这更值得深入反思。章太炎在“章吴之争”中的愤怒之情,是生死诀别与酷刑折磨中的产物,这是激情与大义的交织,并不是“偏执多疑”那么简单。一些学者在描写苏报案中的章太炎时,过于强调个性气质的因素,连用“孤傲、倔强、固执、多疑、褊狭、刚愎自用”等词,这与民国报纸中将其诋为“章疯子”的论调,又有什么太大区别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统训诂学与现代阐释学会通研究”(24&ZD231)、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一审:李静宜
二审:黄爱华
三审:姜异新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25年第7期,
原文、注释及相关内容欢迎查阅本刊!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