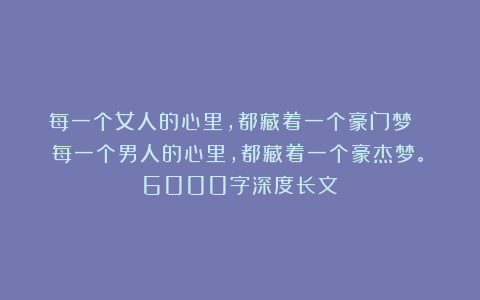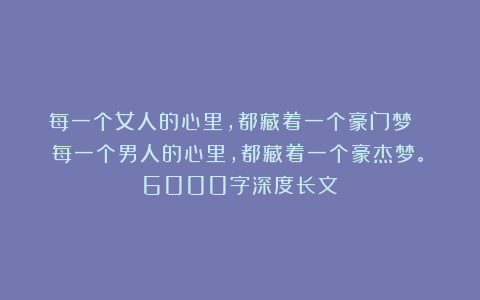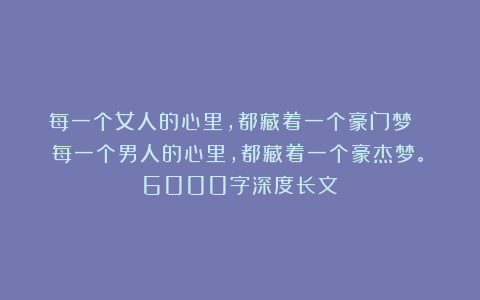俗话说贪财好色,其实应该分开来说,那就是女人贪财,男人好色。
可是,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山川本来异域,风月也难同天,一个文青眼里的月亮,跟一个田间老农看到的终究不同。同样的,男人未必就能理解女人的贪财,而女人也未必能理解男人的好色。
不过,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你不晓得女人有多贪财,你就想想自己有多好色,你有多好色,女人就有多贪财;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你不晓得男人有多好色,你就想想自己有多贪财,你有多贪财,男人就有多好色。
不管是女人的贪财,还是男人的好色,原本就目的不同。而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者达成目的的途径,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女人为实现贪财的目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嫁入豪门,男人为达到好色的目的,最现实的手段,就是成为豪杰。
所以,每一个女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豪门梦, 每一个男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豪杰梦。
也许有人会说了,这句话本身就散发着油腻的爹味,充斥着男权的傲慢。凭任么女人就不能靠自己奋斗达成目的,非得嫁入豪门?凭什么男人就是自己奋斗,吃软饭的也不在少数。
嫁入豪门固然不易,可成为豪杰这条路却更加艰辛,也更加凶险。一个男人,但凡有一丝机会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就能实现好色的目的,是绝对不会去走成为豪杰这条路的。而一个女人,但凡有一丝机会可以通过嫁入豪门,实现贪财的目的,也大可不必以身犯险,去试探其他的途径。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试错过程中,生物总是能找到最便捷的那条途径达成目的,这种策略已经深深的刻进生物的基因里面。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里一开始就说道:人类,乃至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只是基因在亿万年的时间长河里,基于无情的自私性,进化出来的用以保护和复制自己的一个生存机器而已。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存它们、复制它们,或许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所有的个体,以及其他更高级单位的寿命都是短暂的,只有基因生生不息,永垂不朽。
生物在生殖——也就是复制基因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区分为精子和卵子,而是所有的性细胞都一样,都是通过减数分裂产生的同形配子。这些同形配子在相互结合时,碰巧会有一些体积略大的配子,因为一开始就能够为胎儿提供更多的食物,而被优选出来,成为一种进化的趋势。
同时,基于生物的自私性,一些个体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出体积小一些的配子,只要它足够的机动灵活,足够的积极主动,去找到一个体积较大的配子并与之结合,就会从中获得好处,而且相同条件下,制造的配子体积越小,数量就越大,因此也具有了繁殖更多幼儿的潜力。
于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性“策略”开始进化,一种是大量投资的、“诚实”的策略,一种是小量投资的、具有剥削性质的、“狡猾”的策略。前一种性进化的“策略”为后一种“策略”所利用,并为后一种“策略”开辟了道路。
在经过漫长的世代更替之后,狡猾的配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灵活机动。诚实的配子却进化得越来越大,以补偿狡猾的配子日趋缩小的投资额,并变得不灵活起来,反正狡猾的配子总是会积极主动去追逐它们。而介于这两种体积之间的配子就受到了惩罚,因为它们不具有这两种极端策略中的任何一种优势,就从基因池里被淘汰掉了。
最终,诚实的配子变成了卵子,而狡猾的配子则演变成了精子。
虽说每一生物个体都希望存活的子女越多越好,但在生殖的过程中,由于雄性的精子体积小,它的投入就少,能够生育的子女就越多;而雌性的卵子体积大,它的投入就多,能够生育的子女就越少。
如果一方逃避责任,造成幼儿死亡,雌性因为一开始投入的更多,所以比雄性的要蒙受更大的损失。而相较于雌性,雄性因为一开始投入的就少,沉没成本则更低一些。也正因为如此,在交配完成以后,雄性选择脱身而去,同另外的雌性再交配生育子女的意愿就更加强烈。那么作为雌性,它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来减轻配偶的这种剥削造成的损失呢?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界中,每一种生物都是博弈论的大师,它们通过生存策略的调整和选择,维持着自然界里精妙的平衡,雌性也不例外。
在这场博弈中,雌性作为被追求的对象,是当然的买方。不光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的、数量上的优势,还因为它的嫁妆是一个既大又富有营养的卵子,凡是成功地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都可以为其后代获得一份丰富的食物储藏。故此,雌性个体在交配前,拥有更大的议价权,能够据此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从一众追求者中,筛选了那个最中意的雄性配偶来。
比如,雌性可以表现的很矜持,以拉长交配前的求爱期,来考验雄性个体的忠诚度和耐久品质。同时,在这种追求仪式行进过程中,雌性个体可以等雄性个体为其筑完巢后,或者必须喂养雌性个体大量的食物后,再答应与之交配。
总之,雌性个体通过迫使雄性个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先对它们的后代进行昂贵的投资,平衡掉自己在卵子上的投入后,再与之交配。这样一来,雄性个体在交配之后再抛弃对方,就不会有什么好处了。
与此同时,雌性个体可以再次把拒绝交配作为武器,它们慎之又慎,总是挑选那些比其他个体拥有更多的优质基因的雄性个体,使之与自己的基因相结合,以生育出更优秀的后代。基于卵子与精子在数量上的巨大差异,这样的雄性个体不需要很多,它们往往只是金字塔最上层的那几只就够了。
与之相适应,雄性个体要么进化出强健的肌肉,要么进化出能够逃避捕食者的长腿,要么进化出漂亮的羽毛、嘹亮的嗓音等等,让自己在雌性眼里显得更有大丈夫气概一些,以期获得雌性更多的青睐,争取到更多的交配权,让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
有时,它还需要凭借自己强健的肌肉,打败所有的竞争者,在一个族群里爬上金字塔的顶端。或者凭借自己强健的肌肉圈出足够大的领地,并驱逐其他竞争者。有很多例子也表明,一些雌性个休宁愿和在统治集团里地位高的雄性个体交配,而另一些雌性个体也宁愿和拥有地盘的雄性个体交配,却并不在乎这个雄性个体具体是哪一个。
在这种生物层面的、生存策略的主导下,决定了性很多时候是作为对供养者的酬劳形式出现的。同时,在性资源的配置上也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即强者多占或独占性资源,弱者少占性资源或者被排除在性关系之外。
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进行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所有89头公象中,有53头悲催地从未当过父亲,而大多数象崽都只是其中3头公象的后代。通过观察还发现,那些拥有最长的象牙、体形比较弱的对手高出甚至2倍以上的公象,才有资格传宗接代。
除了上节我们说到的——雌性个体通过迫使雄性个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先对它们的后代进行昂贵的投资,以平衡自己在卵子上的先期投入——这个生物层面的因素外,我们再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更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个话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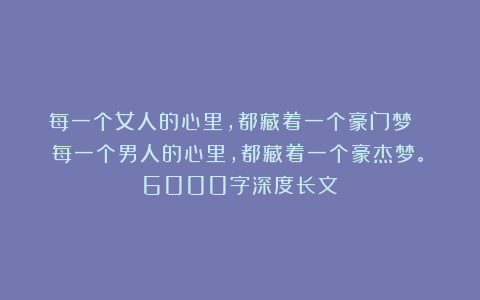 当人类文明进入原始社会以后,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依然极其低下,个体劳作或族群协作一天所获取的食物也非常有限,除了勉强果腹以维系生命外,几乎没有剩余,人类的生存环境相较于今天自然要恶劣很多。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避孕技术。男女之间一但有了性行为,女性就会受孕,便要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和哺乳期,这将耗费女性绝大部分的精力,致使其获取食物的能力大幅降低,甚至于完全丧失。
基于这样的现实,女性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物种繁衍,自然的就会选择那些更快的、更强壮的、更聪明的,并且愿意照顾自己的男性作为配偶。因为他们能获取更多的食物,在保证自己存活下来的同时,也能匀出一部分食物给自己的配偶跟子女,让她们得以生存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子嗣绵延。
倘若几十万年以前,有另一部分女性,是把“帅”作为选择配偶的第一条件,那她们应该在孕育期或哺乳期,就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死掉了,灭绝了。所以,这样的基因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是无法传承下来的。
而那些把食物(物质)占有量的多寡作为选择配偶第一条件的女性,因为在孕育期和哺乳期有了足够的食物,却得以开枝散叶,子嗣绵延。就这样,经过上百万年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种对于食物(物质)的欲望便牢牢地沉淀在了女性的基因里面。
在原始社会,女性的这种出于现实的拷量,去选择那些占有更多资源的男性作为配偶,是生存策略下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既保证了物种的繁衍和自我个体的生存,同时也促进了男性的优胜劣汰,对于人类的进化和物种的改良是一种良性的推动,从而让人类社会进阶到更高的阶段。
但是,即便人类文明进阶到现在,女性择偶的底层逻辑却并没有改变多少,基本上还依然停留在物质层面,只是在表现形式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已。基于这个原因,即便是到了今天,女性择偶的对象,或者说审美(性)取向,依然逃不开力量型、权力型和财富型三种类型。
但不管是力量型、权力型还是财富型,最终都要回归到衣食住行,回归到富足、安稳的生活所带来的安全感、幸福感上来。所以这种崇拜,或者说审美不管以哪一种形式来表现,最终也都要回归到物质,或者说资源占有量的多寡上来。
人类学家对有记录的853种文化进行考察后发现,只有16%的文化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近84%的文化允许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名妻子,即实行一夫多妻制,而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文化仅占总数的0.5%。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男性一生产生的精子能达到万亿之多,但女性的生育潜能却十分有限,她们终其一生能够产生的为生殖服务的卵子不过几百个。如果将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按照一夫一妻制绑定在一起,即使女性已经竭尽全力,男人的生育资源仍然会被浪费。如果将一名女性与几名男性按照一妻多夫制绑定在一起,那资源浪费的情况将更加严重。由此看来,人类的祖先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一夫多妻制,并不单纯是男性压迫女性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层的生物学根源的。
同时,受生存法则与基因传递法则的共同支配,许多女性也会主动选择或取悦能够为其提供生活来源的男性,有时她们宁可跟其他女性共同侍奉一个占有足够多资源的男人,也不愿意独占一个资源匮乏的男人而受穷。
一般认为,一夫一妻制的确立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成果,是妇女解放的标志。但这场本质上由男性领导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男性对女性性资源的一种重新分配。与平均土地、财产等要求一样,平均分配性资源也是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而这种生物学上的动机越是接近社会底层,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就越是明显。因此,一夫一妻制受益最多的不一定是女性,而更可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
另外,女性在择偶时的倾向性选择,又深刻的影响着、乃至于主导着男性进化、或者说努力的方向,是男性奋斗的最原始的驱动力。
于是,两千两百多年前,与人佣耕的陈涉辍耕垄上,怅恨良久之后,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失期当斩的吴广,在大泽乡的暴雨中,也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刘邦和项羽,因为看到始皇帝出游时的阔气与威仪,便立下了“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必可取而代也”的誓言。
不管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还是“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的岳飞,或者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昌龄,他们的梦想,也是一个男人的终极梦想,哪怕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再艰辛、再凶险,也虽九死而不悔。
而当人类社会进阶到更高的文明程度以后,在一个稳定的组织或者体系内,纯粹的依靠暴力来获得更多资源的方式基本上已被摒弃,男性遂把时间和精力、聪明和才智,全都用在了获取更多财富和更大权力上面。
无怪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在镇江金山寺曾问高僧法磐:长江之中大船来来往往,如此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只船啊?法磐回答说只有两只,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唯此二者呀。
几年前,网络上曾经有过一个很火的帖子,大意是根据中国一线城市男女情侣的街拍照片,发现中国的男性无论是从衣服款式还是色彩搭配,乃至于精神面貌,都明显逊于身边的女性伴侣,“要么狗头狗脑,要么缩头缩脑,没一个看的舒服的。”由此得出中国男性配不上中国女性的结论
前面说过,女性的择偶倾向主导着男性的进化方向。倘若中国女性择偶、或者审美(性)的优先标准,一直以来都是诸如衣品、容貌、气质等外在的形象,那中国男性的进化也一定会朝着这方向发力。
正是因为中国女性千百万年来择偶的首要标准还基本停留在物质层面,即资源占有量的多寡上。所以中国男性的进化也就朝着获取权力大小、财富多寡的方向一骑绝尘了。
然而事物总是一体两面的,虽说女性的择偶倾向决定了男性的进化方向,但反过来,男性的择偶倾向,也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进化方向。
近几年一些研究机构、婚恋网站对中国适龄男性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择偶条件里排序比较靠前的几项分别是年龄、外形条件、学历和职业。
不光是现在,从3000多年前《诗经》里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曹植《洛神赋》里的“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再到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些文学作品中男性对于女性体态、容貌的描写,都足以说明,在很早以前,中国男性在选择配偶时,就已经将“窈窕、绰态、倾国倾城”等因素作为优先选项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亚洲四大妖术中,韩国的整容术、日本的化妆术、中国的PS术才应运而生、如火如荼。这些妖术之所以发源于亚洲,而不是欧洲或者美洲等其它地方,至少说明东亚女性在容貌、气质方面的雌竞,比世界其它地方要激烈的多,卷的多。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人生存环境的改善以及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再加上女权主义的推波助澜,女性种群中的精英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勤奋和学识终于挣脱了对男性的依附,使自己首先在经济上独立起来。
而在经济上独立起来的女性种群的精英们,在亲手埋藏了这存续了上百万年的对于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后,思想上也变得更加的自由、独立,相应的审美(性)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上百万年以来,她们第一次不再以功利的眼光去欣赏身边的人和事。
她们不再崇尚那些力量型的明星,转而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纤柔的、妩媚的、有着精致五官的男星身上。这似乎也不难理解,首先,经济上已然独立起来的女性精英们,物质所带来的安全感已经不是她们的第一需求;其次,太有力量了她们可能会觉得hold不住,驾驭不了,反而会带来不安全感。这大约就是类似于养宠物的那种心理吧。
于是,影视剧里的颜狗(为毛要叫颜狗)满天飞了,纤柔的,妩媚的小鲜肉们霸屏了,延续了数几千年的、铁板一块的男权社会终于被撕开了一条罅隙,一抹男色时代的曙光已然若隐若现。
如果有一天,人类社会的善男和信女们,都学会了以纯粹的、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另一方,共赴人生美好,到那时,这世界也许就真的大同了。
当人类文明进入原始社会以后,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依然极其低下,个体劳作或族群协作一天所获取的食物也非常有限,除了勉强果腹以维系生命外,几乎没有剩余,人类的生存环境相较于今天自然要恶劣很多。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避孕技术。男女之间一但有了性行为,女性就会受孕,便要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和哺乳期,这将耗费女性绝大部分的精力,致使其获取食物的能力大幅降低,甚至于完全丧失。
基于这样的现实,女性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物种繁衍,自然的就会选择那些更快的、更强壮的、更聪明的,并且愿意照顾自己的男性作为配偶。因为他们能获取更多的食物,在保证自己存活下来的同时,也能匀出一部分食物给自己的配偶跟子女,让她们得以生存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子嗣绵延。
倘若几十万年以前,有另一部分女性,是把“帅”作为选择配偶的第一条件,那她们应该在孕育期或哺乳期,就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死掉了,灭绝了。所以,这样的基因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是无法传承下来的。
而那些把食物(物质)占有量的多寡作为选择配偶第一条件的女性,因为在孕育期和哺乳期有了足够的食物,却得以开枝散叶,子嗣绵延。就这样,经过上百万年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种对于食物(物质)的欲望便牢牢地沉淀在了女性的基因里面。
在原始社会,女性的这种出于现实的拷量,去选择那些占有更多资源的男性作为配偶,是生存策略下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既保证了物种的繁衍和自我个体的生存,同时也促进了男性的优胜劣汰,对于人类的进化和物种的改良是一种良性的推动,从而让人类社会进阶到更高的阶段。
但是,即便人类文明进阶到现在,女性择偶的底层逻辑却并没有改变多少,基本上还依然停留在物质层面,只是在表现形式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已。基于这个原因,即便是到了今天,女性择偶的对象,或者说审美(性)取向,依然逃不开力量型、权力型和财富型三种类型。
但不管是力量型、权力型还是财富型,最终都要回归到衣食住行,回归到富足、安稳的生活所带来的安全感、幸福感上来。所以这种崇拜,或者说审美不管以哪一种形式来表现,最终也都要回归到物质,或者说资源占有量的多寡上来。
人类学家对有记录的853种文化进行考察后发现,只有16%的文化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近84%的文化允许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名妻子,即实行一夫多妻制,而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文化仅占总数的0.5%。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男性一生产生的精子能达到万亿之多,但女性的生育潜能却十分有限,她们终其一生能够产生的为生殖服务的卵子不过几百个。如果将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按照一夫一妻制绑定在一起,即使女性已经竭尽全力,男人的生育资源仍然会被浪费。如果将一名女性与几名男性按照一妻多夫制绑定在一起,那资源浪费的情况将更加严重。由此看来,人类的祖先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一夫多妻制,并不单纯是男性压迫女性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层的生物学根源的。
同时,受生存法则与基因传递法则的共同支配,许多女性也会主动选择或取悦能够为其提供生活来源的男性,有时她们宁可跟其他女性共同侍奉一个占有足够多资源的男人,也不愿意独占一个资源匮乏的男人而受穷。
一般认为,一夫一妻制的确立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成果,是妇女解放的标志。但这场本质上由男性领导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男性对女性性资源的一种重新分配。与平均土地、财产等要求一样,平均分配性资源也是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而这种生物学上的动机越是接近社会底层,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就越是明显。因此,一夫一妻制受益最多的不一定是女性,而更可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
另外,女性在择偶时的倾向性选择,又深刻的影响着、乃至于主导着男性进化、或者说努力的方向,是男性奋斗的最原始的驱动力。
于是,两千两百多年前,与人佣耕的陈涉辍耕垄上,怅恨良久之后,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失期当斩的吴广,在大泽乡的暴雨中,也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刘邦和项羽,因为看到始皇帝出游时的阔气与威仪,便立下了“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必可取而代也”的誓言。
不管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还是“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的岳飞,或者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昌龄,他们的梦想,也是一个男人的终极梦想,哪怕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再艰辛、再凶险,也虽九死而不悔。
而当人类社会进阶到更高的文明程度以后,在一个稳定的组织或者体系内,纯粹的依靠暴力来获得更多资源的方式基本上已被摒弃,男性遂把时间和精力、聪明和才智,全都用在了获取更多财富和更大权力上面。
无怪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在镇江金山寺曾问高僧法磐:长江之中大船来来往往,如此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只船啊?法磐回答说只有两只,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唯此二者呀。
几年前,网络上曾经有过一个很火的帖子,大意是根据中国一线城市男女情侣的街拍照片,发现中国的男性无论是从衣服款式还是色彩搭配,乃至于精神面貌,都明显逊于身边的女性伴侣,“要么狗头狗脑,要么缩头缩脑,没一个看的舒服的。”由此得出中国男性配不上中国女性的结论
前面说过,女性的择偶倾向主导着男性的进化方向。倘若中国女性择偶、或者审美(性)的优先标准,一直以来都是诸如衣品、容貌、气质等外在的形象,那中国男性的进化也一定会朝着这方向发力。
正是因为中国女性千百万年来择偶的首要标准还基本停留在物质层面,即资源占有量的多寡上。所以中国男性的进化也就朝着获取权力大小、财富多寡的方向一骑绝尘了。
然而事物总是一体两面的,虽说女性的择偶倾向决定了男性的进化方向,但反过来,男性的择偶倾向,也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进化方向。
近几年一些研究机构、婚恋网站对中国适龄男性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择偶条件里排序比较靠前的几项分别是年龄、外形条件、学历和职业。
不光是现在,从3000多年前《诗经》里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曹植《洛神赋》里的“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再到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些文学作品中男性对于女性体态、容貌的描写,都足以说明,在很早以前,中国男性在选择配偶时,就已经将“窈窕、绰态、倾国倾城”等因素作为优先选项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亚洲四大妖术中,韩国的整容术、日本的化妆术、中国的PS术才应运而生、如火如荼。这些妖术之所以发源于亚洲,而不是欧洲或者美洲等其它地方,至少说明东亚女性在容貌、气质方面的雌竞,比世界其它地方要激烈的多,卷的多。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人生存环境的改善以及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再加上女权主义的推波助澜,女性种群中的精英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勤奋和学识终于挣脱了对男性的依附,使自己首先在经济上独立起来。
而在经济上独立起来的女性种群的精英们,在亲手埋藏了这存续了上百万年的对于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后,思想上也变得更加的自由、独立,相应的审美(性)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上百万年以来,她们第一次不再以功利的眼光去欣赏身边的人和事。
她们不再崇尚那些力量型的明星,转而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纤柔的、妩媚的、有着精致五官的男星身上。这似乎也不难理解,首先,经济上已然独立起来的女性精英们,物质所带来的安全感已经不是她们的第一需求;其次,太有力量了她们可能会觉得hold不住,驾驭不了,反而会带来不安全感。这大约就是类似于养宠物的那种心理吧。
于是,影视剧里的颜狗(为毛要叫颜狗)满天飞了,纤柔的,妩媚的小鲜肉们霸屏了,延续了数几千年的、铁板一块的男权社会终于被撕开了一条罅隙,一抹男色时代的曙光已然若隐若现。
如果有一天,人类社会的善男和信女们,都学会了以纯粹的、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另一方,共赴人生美好,到那时,这世界也许就真的大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