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瞒你说,很多看着岁数不小的长辈,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总会感叹那时信息全靠报纸、楼道喇叭,电视还是件稀罕物——可偏偏有一件事,早就在普通百姓心里传开了:每次只要有外国风云人物来咱们中国,电视里总能看到主席身边站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姑娘。谁那会儿不琢磨这俩人是啥来头?她们不是普通的礼仪小姐,也不是秘书,穿着打扮像是复制粘贴出来的,扎着整齐的马尾,戴着黑框眼镜,要说脸蛋也算不差——有的人调侃,活脱脱一对“孪生姐妹花”。大家嘴里都不约而同冒出同一个话题,这俩姑娘到底是谁?
这俩被无数双好奇眼睛盯着的姑娘,其中一个是王海容,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背景多少有点“家学渊源”的味道。可更多人纳闷的是另一个——唐闻生。要说“唐闻生”三个字,许多人一辈子没跟她照过面,但只要翻开那会儿的历史照片,看到站主席身边、表情淡定的英语译员,心里不由得腾起一股敬意。这姑娘,把一口漂亮的英语讲得天衣无缝,后来跟齐宗华、章含之、罗旭几个人一块儿,被称作外交系统里的“五朵金花”。但你要是真以为唐闻生一上来就能挥洒自如,跟伟人们有说有笑,那可大错特错。
其实唐闻生走上这条路,说是巧合,也不全算。她生在美国,自小英语溜得像母语,家里给了她背后的底气。可进了外交部,有多少人适应得了一下子站在领袖身边?那不比考试,一个答案错了再填。22岁那年,她刚踏进外交部翻译室,心里一直觉得自己会的还远远不够。当初老同事还给她打预防针:翻译,不是嘴皮子溜就完事儿,是真金白银的“实战”。谁也没告过她,隔行如隔山,面对主席那湖北口音夹杂俏皮话,翻译想装镇静都难。
1966年那会儿,武汉气温直逼三十多度,唐闻生却一身冷汗,硬是比周围还要凉些。陈毅副总理临时点将,要唐闻生充任主席的英语翻译。她反复推脱,说自己不合适,还央求换人,不但没成,反倒让领导拍了板。七月份的武汉闷得像笼屉,别说女生家家怕热,偏偏她是怕出错、怕出丑,紧张到连肚子都打结。早饭都是强咽下去的,偏偏走廊里忽的眼前一黑,就快站不住了。多亏了旁边的法语译员齐宗华及时把她扶住,不然当场晕倒,估计她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高光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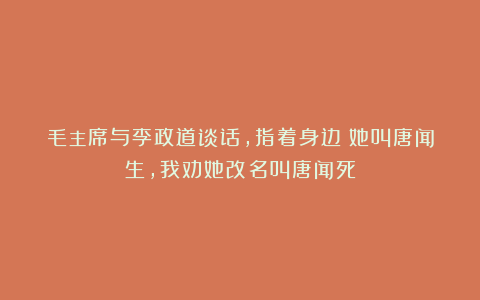
说到这里,其实在场的老外交官都挺心疼姑娘,边安慰,边开玩笑:“唐闻生,你要是晕了,这英语翻译真成绝响喽!”一句话,气氛瞬间轻松不少,边上小伙子姑娘们都笑出了声。可唐闻生能笑得轻松吗?只怕接下来的一场“大考”,还没开始就让她心惊肉跳。
后来到了会见大厅,唐闻生还没完全缓过来,廖承志却忽然通知一句:“今天主席不打算发言啦。”她整个人像被释放了,差点脱口念“阿弥陀佛”。第一次出场居然悬在了半空,连一丝表演的机会都没有,白白虚惊一场。说实话,现在回头看,挺像一场恶作剧,可那时她的腿都还在抖。
其实不只是给毛主席当翻译紧张,只要是重量级的人物面前,哪有不抖的。唐闻生正式走到周总理身边那一年,心里的疙瘩比做主席翻译时可能还要大一些。你要知道,前头一直是冀朝铸先生干的,连续干了17年,堪称一代宗师。突然轮到个毛头小姑娘,心里不打鼓才怪。有一回轮到她值班,周总理看着这个生面孔,问她叫什么名字。估计唐闻生那时脸红得比六月的苹果都艳,低头小声报了名。总理带着笑问她:“两年能不能赶上冀朝铸?”这话要给一般人当场怼懵了——唐闻生紧张得嗓子都快冒烟儿,差点没眨着眼睛大呼“总理您别逗我了”。
可这份紧张和不自信,逼着唐闻生一下子成长得快。从旁观到主力,就靠她每一次上场前的苦练和恶补。有时候,别人吃饭,她在背资料;别人下班回家看电视,她窝在小房间里跟英文原版文件较劲。时间长了,紧张是会被经验一点点打磨掉的,唐闻生站在主席、总理身边,从一个拘谨的“小丫头”,慢慢变得气定神闲,成了别人眼里“气场很大”的外交官。多年以后,她几乎能凭语调猜出领袖下一句要怎么说——翻译不是随口转换,更像贴身保镖,既要帮主人表达意思,也要帮他避免语义上的误解或者尴尬。
其实老百姓想象的“领袖身边”有时候并不神秘。有段时间,唐闻生在毛主席、周总理那儿看到的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温和和体贴。毛主席有时候爱开玩笑,笼络大家的人心。印象很深的是1974年那次,中南海会见,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一左一右伺候着。毛主席用唐闻生做例子,跟李政道“抖机灵”,说她名字叫唐闻生,要改名叫唐闻死,一屋子人都乐得手拍大腿。当时如果唐闻生还是刚到外交部那会儿,估计场面立刻就冷下来了。可几年熏陶,她都能用半玩笑的语气接住话茬——“主席,改名容易听上去可不吉利”。这种互动,已经不只是主仆、上下级的生疏,而是真正融入其中的默契。
写到这儿,顺带说一句,唐闻生和王海容,那不是纯粹的“宫女型”女官。她们是真正跟领袖共担风雨的小辈,甚至在70年代外交工作最吃劲的时候,经常陪总理熬到深夜。周总理那会儿身子骨已经不行了,脸色蜡黄,穿着灰色中山装、别着人民服务的徽章,仔细点会发现衣服都撑不起来。唐闻生有一次看到总理酒杯里的白酒,实在憋不住了,小声嘀咕一句:“总理,还是少喝点吧,对身体不好。”平时台下怎么也没这么大胆,可人一着急,什么规矩都顾不上。这点插曲,往往连中办的人都觉得诧异:这个小姑娘也太较真了吧?可周总理反而拍拍她的肩膀,一句话没怪。
再后来,唐闻生不仅英语“Butter-level”,甚至口音里听不出一点“夹生味儿”,连外宾都惊叹中国翻译团队能如此专业。有人事后讲,这些年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如影随形,没成家也不觉孤单,有的是一份投入到国家大事里的满足感。她们的成长和牺牲,是那一代独有的烙印。
后来,有些细心的年轻人,翻出1976年的旧报纸,发现周总理、毛主席在她们人生轨迹中如两座巍峨的山。周总理去世那天,唐闻生接到电话,坐了半天没动,房间里连钟表的声音都听得见。九个月后,老人们陆续离去,唐闻生却还是每天下班回家,点着一盏小台灯,在翻译文件。每次有人问起老一辈,她并不是一上一下地陪着流泪,只是淡淡地说:“他们对大家虽然严格,但对我们这些晚辈,特别亲厚。那种亲近啊,一辈子难得几回。”
说到这里,我会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惶恐和挣扎,有的人能够化这份慌张,成就一生最难忘的际遇。唐闻生和王海容几十年不结婚?外人拿来八卦,可她们也许自有选择——毕竟,把一生交给爱的人容易,把一生交给时代却是极高的境界。
我只知道,这样的故事,说多少次、听多少遍,都难有厌倦;人生际遇,命运跌宕,走到最后,谁能说她们不是活得最明亮的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