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最早听闻茅盾之名,是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一篇《白杨礼赞》,让这个名字深深记在心底。后来渐知,经典电影《林家铺子》与《子夜》皆改编自他的小说,才真正懂得,他无愧于“一代文学巨匠” 的称号。
更令人意外的是,收藏家张伯驹将毕生珍藏捐赠国家时,那份象征至高荣誉的奖状上,赫然印着“沈雁冰” 三个字 —— 而沈雁冰,正是茅盾的本名。
这位曾执掌新中国文化部的首任部长,在文学与事业的辉煌之外,也有着一段纠结一生的情感往事:一边是相濡以沫的原配妻子孔德沚,一边是异国相伴、给予他无限创作灵感的红颜知己秦德君,最终他的选择,藏着太多时代与人性的复杂。
01乌镇走出的文学巨匠:笔名背后的“矛盾” 人生
1896 年,茅盾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如今的乌镇因世界互联网大会享誉全球,而在早年,茅盾本人便是家乡最耀眼的一张文化名片。他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 只是他 98 个笔名中的一个,却成了最广为人知的标识。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这个带着 “矛盾” 之意的笔名,竟隐隐预示了他此后纠结的情感轨迹 —— 若泉下有知,他是否会后悔选用这个名字?
茅盾的人生起点,藏着一段旧式婚姻的伏笔。四岁那年,祖父沈恩培带他去酒馆,偶遇老友孔繁林与孙女孔德沚。酒馆老板一句“这两个娃娃好般配” 的戏言,竟让两位老人当场敲定了娃娃亲。回家后,母亲陈爱珠曾忧心忡忡:“孩子尚小,长大后自有选择,如今订下婚约,将来若是不合,该如何收场?”
父亲沈永锡却有自己的执念。早年他曾与孔繁林的女儿订亲,后因八字不合作罢,那位孔家姑娘最终抑郁而终,此事成了沈永锡毕生的“情债”。如今儿子的婚约,在他看来既是缘分,也是了却心结的契机,故而坚持非如此不可。
命运对这个家庭格外苛刻。茅盾十岁时,身为清末秀才、饱读诗书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陈爱珠独自带着两个儿子,靠家中纸店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但这位母亲性格要强,深知“读书改变命运”,即便生活困顿,也始终咬牙供两个儿子上学。1913 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陈爱珠终于松了口气 —— 她总算能让九泉之下的丈夫安心了。
毕业后,凭借北大预科的文凭,茅盾本可像亲戚们一样进入银行工作,安稳度日。但母亲坚持让他进入商务印书馆,远离官场与商场的纷扰。一向敬重母亲的茅盾,顺从了这个决定,也由此开启了与文学、出版业相伴的一生。
02旧式婚姻里的温情:从“失望” 到 “刮目相看”
1916 年春节,20 岁的茅盾与孔德沚如期成婚。婚前母亲曾坦诚相告:“孔家姑娘不识字,你若是不同意,也可退亲,但过程恐会麻烦,甚至可能打官司,我实在为难。” 念及母亲多年的养育之恩,茅盾并未计较 “不识字” 这一点,只想着好好经营这段婚姻。
可拜堂时,茅盾却被眼前的景象刺痛了—— 新娘竟是小脚。彼时新思想已在青年中传播,自由恋爱渐成潮流,而自己的妻子仍守着这般旧式习俗,失望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疙瘩。
好在母亲陈爱珠深明大义,她对茅盾说:“夫妻要长久,必须有共同语言。德沚不识字,错不在她,在她的父母。你不妨教她读书,或许能有改变。” 于是,茅盾成了孔德沚的启蒙老师,耐心教她识字写字。令他意外的是,孔德沚极具天赋,短短时日便认识了五百多字,这份聪慧与努力,让茅盾渐渐对她刮目相看。
后来茅盾赴上海工作,母亲接过“教鞭”,继续辅导孔德沚读书。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夫妻二人开始书信往来,字里行间的牵挂与理解,让感情愈发深厚。1920 年,开明的陈爱珠带着孔德沚来到上海,与茅盾团聚。不久后,女儿沈霞、儿子沈霜相继出生,一家三口的日子温馨和睦,满是天伦之乐。
03异国他乡的邂逅:革命知己的情感羁绊
茅盾的人生,始终与时代浪潮紧密相连。1921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资历堪比建党初期的革命先辈,是名副其实的 “老革命”。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遭到南京国民政府通缉,被迫逃回上海,闭门避祸。
好友、浙江老乡陈望道探望时,见他情绪低落、创作受阻,便建议:“不如去日本避一避,换个环境,或许能走出阴霾。”
就在去陈望道家取船票时,茅盾遇见了秦德君—— 一个与孔德沚截然不同的女子,而她,也正要前往日本。
秦德君1905 年出生于四川,是彝族人,骨子里带着川妹子的泼辣与果敢。学生时代,她因剪发、参加游行、创办进步刊物被学校开除,后与恽代英、刘伯坚、李大钊等革命先辈交往密切,1923 年便在邓中夏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履历,在当时的女性中极为耀眼。
更巧的是,秦德君曾在上海平民学校就读,而茅盾正是她的老师,两人本就有师生之谊。1928 年 7 月,茅盾与秦德君一同登上前往日本的商轮。异国旅途漫长,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经历、相似的理想追求,渐渐生出别样的情愫。
秦德君后来回忆,在船上,茅盾常约她到甲板上凭栏望海,聊着聊着,总会说起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幸。虽只是一家之言,但彼时已过而立之年的茅盾,面对眼前这位敢爱敢恨、履历光辉的女子,终究没能守住内心的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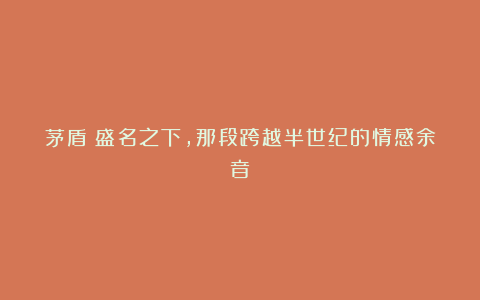
抵达日本神户时,宪兵误以为他们是夫妇,指着秦德君问茅盾:“她是你的夫人吗?” 茅盾几乎脱口而出:“是的,她是我亲爱的妻子。”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秦德君的心湖。她明知茅盾已有家室,却未当场否认 —— 异国他乡的孤独、革命同志的默契,让她渐渐陷入这段不该开始的感情。
到日本后,茅盾每天都会去找秦德君,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同是“天涯沦落人”,情感在朝夕相处中迅速升温,最终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同居生活。秦德君后来强调:“若不是茅盾天天说要和妻子离婚,我绝不会与他同居。”
04现实的拉扯:母亲、发妻与“四年之约”
在日本的日子,茅盾的创作并不顺利,是秦德君为他带来了灵感。她主动讲述自己与女伴的成长经历、四川老家的山水风情、革命路上的挫折困境,这些鲜活的故事,让茅盾重新找回创作热情,着手撰写小说《虹》。
可幸福的表象下,危机早已潜伏。1929 年 8 月,秦德君意外怀孕,因经济拮据、身份尴尬,不得不返回上海做人流。看着已成形的胎体,她既痛心又无助,却仍对茅盾的 “离婚承诺” 抱有期待。
与此同时,两人同居的消息传回上海,母亲陈爱珠与妻子孔德沚得知后,反应截然不同却又目标一致。沈母坚定地站在儿媳这边,她告诉孔德沚:“你以’沈太太’的名义去取茅盾的稿酬,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这段关系自然会瓦解。”
1930 年 4 月,日本当局大肆抓捕中共成员,茅盾带着秦德君被迫返回上海,暂居朋友家。此时的茅盾仍想离婚,甚至带着秦德君去见母亲。面对这位 “不速之客”,孔德沚没有争吵,只是让儿女喊秦德君 “秦先生”,这份体面与克制,反而让秦德君的 “胜利者姿态” 显得格外尴尬。
沈母对秦德君的态度则毫不含糊,她写信严厉斥责茅盾:“你自幼丧父,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教你诗书礼仪,如今你弃妻抛子,毁了这个家,于心何忍?’糟糠之妻不下堂’,你该回心转意,承担起家庭责任,这才是正道!”
母亲的话如重锤,敲醒了茅盾。一边是养育之恩与多年的家庭羁绊,一边是异国相伴的情感依赖,他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孔德沚看出了他的动摇,找到茅盾的好友叶圣陶、郑振铎求助,两人都劝道:“茅盾重情,给些时间,他定会回归家庭。”
另一边的秦德君,承受着“小三” 的骂名,又再次怀孕,压力之下竟出了昏招 —— 她谎称孔德沚与他人有染,试图逼迫茅盾离婚。可这一说法毫无根据,沈母亲自为儿媳作证,揭穿了谣言。此事成了转折点,茅盾的天平彻底偏向了发妻。
为了安抚秦德君,茅盾提出“四年之约”:“四年内,我赚够钱补偿德沚,之后便与她离婚,和你在一起。” 明眼人都知这是托词,好友丁玲特意提醒秦德君:“不要信他。”
可深陷爱情的秦德君,高估了自己在茅盾心中的分量,竟选择相信这个承诺。她再次打掉胎儿,默默等待四年后的“结果”。
四年后,一切如丁玲所料。茅盾彻底断绝了与秦德君的联系,回归家庭,仿佛那段异国情缘从未发生。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了文化部部长,秦德君则担任政协委员,两人偶尔在公开场合相遇,茅盾总是刻意躲闪—— 他终究是愧疚的,却也选择了逃避。
05往事的余音:六十年的“意难平”
1981 年,茅盾与世长辞。在他晚年撰写的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对秦德君只字未提,仿佛那段往事已被时光彻底抹去。就像戴望舒前妻穆丽娟晚年被问及旧情时,只淡然一句 “我已到了这个年纪,不想再回忆了”,茅盾也选择以沉默封存这段过往。
可秦德君却始终无法释怀。1985 年,80 岁的她在香港《广角镜》月刊发表《我与茅盾的一段情》,首次公开这段尘封的往事。1999 年 1 月,秦德君去世;同年年底,她的自传《火凤凰 —— 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出版,引发轰动。
在书中,秦德君写道:“我虽微不足道,可有可无,但茅盾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我反复思量,若是让这段往事湮没,虽保全了他的英名,却对不起后来人,更对不起研究者。”
字里行间,是六十年的不甘与屈辱,她以文字为酒杯,浇着心中久积的块垒。
从1930 年到 1999 年,一个甲子的时光,秦德君终究没能放下这段感情。有人说她 “纠缠不休”,也有人懂她的 “意难平”—— 毕竟,她曾付出真心,也曾两次失去孩子,这份伤痛,不是一句 “放下” 就能化解的。
读名人传记,从来不是为了八卦,而是透过那些光鲜与纠葛,看见真实的人性。茅盾是文学巨匠,也是普通人,他在情感中的犹豫、妥协与逃避,或许不够“完美”,却格外真实。而孔德沚的隐忍与智慧、秦德君的执着与遗憾,也让这段往事超越了个人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最终我们会明白: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却有必须承担的责任。学会珍惜眼前人,不辜负真心,不透支信任,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好的交代—— 毕竟,福报从来都藏在 “珍惜” 二字里。
在书中,秦德君写道:“我虽微不足道,可有可无,但茅盾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我反复思量,若是让这段往事湮没,虽保全了他的英名,却对不起后来人,更对不起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