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她一生获奖无数,曾两次斩获布克奖,代表作《盲刺客》就是其中之一。《盲刺客》是阿特伍德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被誉为“21世纪最值得阅读的小说之一”,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盲刺客》结构精妙复杂,故事层层嵌套,主人公是一对家道中落的豪门姐妹:艾丽丝·蔡斯和劳拉·蔡斯。《盲刺客》的第一层故事,是老年艾丽丝在独居生活中追忆往昔,逐步揭开妹妹劳拉在25岁开车坠桥身亡的事故真相。当时警方判定劳拉坠桥为自杀,艾丽丝却明白另有隐情。蔡斯家族曾是镇上的豪门望族,1870年代,艾丽丝的祖父本杰明创立了纽扣厂,建造了维多利亚风格的阿维隆庄园。但是战争的到来改变了一切,艾丽丝的父亲诺弗尔从战场侥幸归来,失去了一只眼睛一条腿,精神世界变得支离破碎。蔡斯家族逐渐没落。姐妹俩在纽扣厂野餐会上遇到了她们命运中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新兴富豪理查德·格里芬,一个是革命青年亚历克斯·托马斯。格里芬表面上与蔡斯家族结交,背后却策划了纽扣厂失火案,并栽赃给教工人识字的亚历克斯。艾丽丝和劳拉把逃亡的亚历克斯藏在阁楼上,等到风声过去之后又把他送走了。姐妹俩都爱上了他。
纽扣厂火灾后,18岁的艾丽丝被迫嫁给了理查德·格里芬。格里芬是个恋童癖加虐待狂。他不仅全面侵吞蔡斯家财产,导致艾丽丝父亲自杀,还对艾丽丝施以虐待。艾丽丝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富贵生活,把苦水咽了下去。劳拉却一心想要逃离格里芬的掌控。有一天,格里芬忽然声称劳拉得了臆想症,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劳拉想办法逃离了精神病院,偷偷来找艾丽丝,艾丽丝这才发现了难以置信的恐怖真相,并直接引发了后面的悲剧……这一切故事,都出自艾丽丝的回忆记述,充满她的自我辩解与矛盾,同时穿插当时关于蔡斯家族和格里芬家族的新闻事件,构建出本书第一个故事的悬疑基调和惊天反转。
第二层故事是第一层故事的主人公劳拉·蔡斯所写的小说《盲刺客》,在劳拉开车坠桥之后由艾丽丝整理出版。《盲刺客》描写了一位富家淑女与革命危险分子的禁忌恋情。富家淑女——原型疑似劳拉,与革命危险分子——原型疑似亚历克斯,在各种地方秘密会面。最后,革命危险分子离开加拿大,去支援西班牙内战,一对恋人就此分别。这个故事的部分章节也穿插在整本书中,构成嵌套结构的一部分。
第三层故事是劳拉所写的小说中的富家淑女与革命危险分子幽会时,二人共同虚构的一个发生在外星球的科幻故事。主人公是哑女和盲刺客。哑女是代替权贵女儿献祭给神的孤女,盲刺客是因为编织华贵地毯而瞎了眼睛的奴隶孩子,眼盲之后就成了手指灵活的刺客。盲刺客本来是奉命来刺杀哑女,再假扮成哑女在祭祀活动时刺杀国王。但是盲刺客爱上了哑女,想要拯救她,二人开始了前途未知的惊险逃亡……
全书在三个故事的交织叙述中,逐渐揭示出令人震惊的隐情。
劳拉来找艾丽丝,说她当时不是得了精神疾病,而是怀孕了。艾丽丝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劳拉不肯说。但是劳拉关心另一件事,那就是去西班牙参战的亚历克斯要回来了。劳拉的口吻仿佛亚历克斯是她的爱人,艾丽丝立刻误会劳拉孩子的父亲是亚历克斯。艾丽丝被刺伤了,原来她多年来与亚历克斯暗中相恋,她以为亚历克斯和劳拉也是如此。为了报复,艾丽丝当场告诉劳拉,亚历克斯一直是自己的情人,而且已经阵亡了。劳拉一言不发地开走了艾丽丝的车。艾丽丝回到家后不久,就收到了劳拉开车坠桥的消息。
劳拉的死给了艾丽丝重创,当艾丽丝发现劳拉笔记本里记载的真相时,更加痛不欲生。原来劳拉的孩子并不是亚历克斯的,而是理查德·格里芬的。劳拉对亚历克斯只是一种纯真虔诚的单恋与憧憬,格里芬却利用了她的真心,谎称亚历克斯处于危险之中,只要劳拉委身于他,他就会保护亚历克斯。劳拉等于为格里芬的谎言牺牲了一切,又遭到了艾丽丝不计后果地丢出真相,理想破灭的她选择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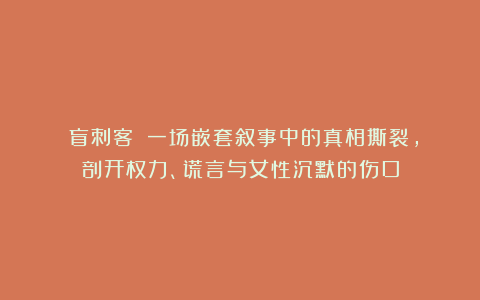
劳拉的死唤醒了艾丽丝,她决心复仇。她用自己与亚历克斯地下恋情的经历写出了《盲刺客》的书,并以劳拉的名义出版。小说一经出版,就因为其中的背德偷情与露骨描写,遭到了保守社会的攻击。人们认为书中女主人公就是劳拉,人们的批判也波及了劳拉的姐夫格里芬,让他丧失了政治前途,身败名裂。这只是艾丽丝报复的表层,更深一层是“诛心”。恋童癖格里芬自认为劳拉是他的“圣女”,当他看到《盲刺客》中露骨的偷情描写,“圣女滤镜”碎了。万念俱灰的格里芬在第一次诱骗劳拉的船上神秘暴毙。艾丽丝独居了漫长时日,在对劳拉的忏悔中回忆往事,并写下这一切,希望把家族女性的记忆传承下去。
《盲刺客》这部小说与阿特伍德的多部作品一样,都是关于女性生存处境的故事,展现了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思想。首先是女性与叙述权力。《盲刺客》赋予边缘化的女性声音以力量,将女性私人书写转化为抵抗话语霸权的工具。艾丽丝的写作不仅找回了自己被压抑的声音,更是重塑了属于女性的叙事空间,让那些被男性话语掩埋的真实得以重见天日,让那些被刻意遗忘的细节重新有了温度和重量,让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被记录并流传下来。
其次是女性的主体重建。蔡斯家族的三代女性,尽管处于上流社会,但都没有自主权,只能靠婚姻获得象征性的社会地位。艾丽斯一直认为自己选择了权衡之后最好的道路,却因此葬送了自己和妹妹。劳拉的死唤醒了艾丽丝,让她走上了自我觉醒与主体重建之路。艾丽丝带着孩子逃离了格里芬家族,并以写作为武器向被剥夺的一切复仇。她的主体重建之路十分艰难,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失去了所有亲人,一个人孤独终老,但她以文字为武器,通过揭露格里芬的罪行,完成对“受害者”身份的超越。
第三是姐妹的复杂性共生。艾丽丝与劳拉命中注定不可分割,但她们的性格、价值观与人生选择又那么不同。艾丽丝就像大地,节制、务实、平衡稳定,为了现世安稳宁愿自我催眠;劳拉就像风,自在、轻灵、变幻莫测,为了独立自由宁愿放弃生命。艾丽丝与劳拉一方面无法相互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彼此的爱和血缘羁绊。
《盲刺客》的叙事策略也可谓精妙绝伦。其中之一就是多文本嵌套叙事。蔡斯和格里芬豪门恩怨的外层故事,套着富家淑女和革命危险分子的地下恋情故事,又套着外星球哑女和盲刺客的科幻故事,这些故事加上老年艾丽丝的现实生活叙述和陈年剪报新闻,被作者错落有致地安排在整体叙事框架中,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叙事智慧、掌控力和探索性。
互文也是本书的叙事策略之一,通过引用、改写、戏仿或对话其他文本,在多重文本交织中构建意义。在《盲刺客》中,阿特伍德直接引用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等古典作品,同时也涉猎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石头天使》等近现代文学作品,为小说构建了丰富的文本参照体系。
除了上面两种叙事手法,《盲刺客》还体现出哥特文学的特征。书中许多人物都是通过讣告的形式出场的,如开车坠桥的劳拉,在帆船上神秘暴毙的理查德·格里芬,在公寓中自杀的艾梅·格里芬,在家中病死的威妮弗蕾德·格里芬。蔡斯家的墓地,大火烧毁的纽扣厂,在战争中变成精神怪物并自杀的父亲,被诬陷为疯女人遭受电击的劳拉,这些段落也是全书哥特叙事的重要构成。作者对哥特文学元素的运用和氛围的营造,深刻探讨了女性如同古堡幽灵般的宿命,揭示女性长久以来在阴森禁锢中所面对的残酷困境。
《盲刺客》是20世纪末文学史上的标志性文本,当艾丽丝一字字凿开记忆的冰层时,那些沉在水下的“哑女”们浮上水面,在日光下唱出自由的歌——这不仅是个体救赎,更是一场用记录和书写完成的审判。正如文学界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评价:“她的作品……丰富着人类对于女性、暴力、文明等议题的认知。她始终关注人类生存的境况,反抗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与观念所形成的压迫。她超越性的目光,强有力的声音,精妙的叙事,让那些被障蔽的显形,被埋葬的破土,被遗忘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