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格遗址 宗同昌拍摄
古格、普兰与噶尔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拉达克、克什米尔及印度保持着紧密的地缘联系,是连接喀喇昆仑古道与亚欧丝绸之路贸易的关键枢纽。
伴随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复兴浪潮,来自中亚、西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多元文化——包括波斯、贵霜及大食帝国的民族、宗教、艺术与思想资源——在克什米尔地区交汇融合,继而通过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进一步传播,最终形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宗教文化复合体,并逐步向西藏西部渗透。
西藏佛教后弘期是藏传佛教史上的核心概念,指佛教在西藏经历毁灭性打击后重新复兴并实现本土化的关键阶段。它与前弘期(7-9世纪,佛教最初传入西藏并鼎盛的时期)相对应,始于1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背景是9世纪中叶赞普朗达玛灭佛导致西藏佛教中断近百年后,佛教从多方向重新传入:一路通过青海丹斗寺的喇钦·贡巴饶赛向卫藏地区传法(下路弘传),另一路由古格王益西沃派遣仁钦桑布等赴克什米尔学法,并迎请阿底峡大师入藏弘法(上路弘传)。
后弘期标志着佛教本土化的最终完成——大量佛经被系统翻译(如仁钦桑布译注显密经典),佛教教义与西藏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等藏传佛教宗派相继形成。此时期也是艺术与思想的大融合阶段:克什米尔、印度帕拉、尼泊尔等艺术风格传入西藏西部,与本土传统结合催生出古格壁画等独特艺术形式,寺院成为学术中心,建立辩经制度和教育体系。在社会层面,政教合一制度开始萌芽,寺院获得经济政治权力,高僧成为文化权威。
这种文化交流在佛教艺术领域尤为显著。
以大译师仁钦桑布和阿底峡尊者为代表的宗教传播者,将克什米尔及帕拉(波罗)艺术风格引入西藏西部,并与本土传统相互交融。其艺术成果集中展现在托林寺、阿基寺、塔波寺、萨波石窟以及古格王国遗址的壁画创作中。
经过9至14世纪长达五百余年的艺术积淀,并在15世纪江孜风格的进一步催化下,西藏西部地区最终于15至16世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壁画体系——古格样式。
这一风格既保留了外来艺术影响的印记,又深刻体现了藏族本土的审美意趣,成为西藏佛教艺术史上的珍贵遗产。
▲古格遗址
古格王国遗址坐落于西藏札达县城以西18公里处的象泉河南岸。
遗址内现存各类遗迹丰富,包括:
445座房屋(含殿堂)、978孔窑洞、58座碋堡遗迹、28座佛塔遗迹、3道由108座小佛塔构成的塔墙、4道玛尼墙、10道防卫墙、1条通往山顶的暗道,以及7孔被称为“冬宫”(国王冬季地下居所)的残存洞窟。
古格城堡北侧山坡的两层台地上,现存四座间距均在二三十米内的佛殿,其旁侧分布着大量僧舍建筑遗迹,共同构成了古格故城规模最为宏大的、以佛寺殿堂为核心的建筑群。
因历史变迁,古格遗址中仅五座佛殿保存相对完好:
拉康嘎波(白殿)、拉康玛波(红殿)、金科拉康(坛城殿)、杰吉拉康(大威德殿)和卓玛拉康(度母殿)。
而红殿与白殿是故城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建筑。
札达古格红殿,是古格王国时期(约10-17世纪)留存的重要佛教殿堂。
作为古格王朝宗教与艺术活动的核心载体,红殿不仅凝结着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的历史记忆,更是西藏西部壁画艺术的典范之作。
其建筑形制与壁画主题鲜明呈现了吐蕃佛教艺术向古格风格的转型过程,具有极高的历史、宗教与艺术价值。
红殿坐落于遗址北坡的第三级台地,因其殿堂外壁通体涂饰红色而得名,为坐西朝东的藏式单层平顶殿堂。殿堂平面呈长方形,面阔(南北向)22.2米,进深(东西向)19.4米,总高9.8米。殿顶屋面采用藏族特有的“阿嘎土”夯打技术处理,形成宽敞的平台。殿顶后部中央升起高大的天窗,以利殿内采光通风。殿顶四周砌筑有2米高的土坯矮墙,墙体下部用石块垒砌基础,墙体上开设了4个方窗孔和13个竖条形或三角形的瞭望射击孔,这些射击孔的形制与城堡中防卫墙和碉堡上的完全一致。在历史上的城堡防御战中,居高临下的红殿屋顶曾发挥过巨型碉堡的作用。
▲ 古格红殿正面示意图
▲ 古格红殿纵剖面示意图
▲ 古格红殿平面示意图
开设在红殿东墙正中的大门保存着完整的木雕门框和门扇。门洞高3.25米,宽3.19米。
▲古格红殿木雕大门
▲古格红殿木雕大门局部特写
门框整体分内外三层,每层上框中间均为一尊弓腿站立的护法金刚高浮雕。
▲古格红殿木雕大门局部特写
里面两层分别雕刻由摩羯鱼和迦陵频伽鸟尾部演化而来的忍冬卷草纹,纹饰繁缛。
外层内容复杂,分成左右不完全对称的18组图案,两侧框图案较小,包含单独的高僧、王子、苦修者形象,以及双象嬉戏、人骑象、人驯象等场景。
▲古格红殿木雕大门局部特写
红殿内原主供的泥塑造像已全部毁坏殆尽。
根据残存的须弥台座、莲座、背光等迹象分析,原主供塑像应为一佛八弟子组合。
塑像的毁灭在很大程度上与藏传佛教造像定规中的“装藏”习俗有关。
按照该定规,造像内部需装入卷紧封口的梵文或藏文经咒(形如爆竹,放置时不可颠倒,否则恐招火灾),以及“五宝”(金、银、珍珠、珊瑚、绿松石)、“五甘”(蜂蜜、石蜜、乳、酪、酥油)、“五谷”(稻、麦、青稞、豆、芝麻)、“五香”(白檀、沉香、肉豆蔻、龙脑香、郁金香)。
这些混合包以黄绢装入佛像内部的圣物,意在使佛像“不散不朽,不生虫虻”,但也因其价值引发了贪婪之徒的破坏。
虽然塑像无存,但像座仍得以保留。
从须弥座的浮雕上可窥见当时的雕塑水平:正中原大佛像座下塑有法轮和一对卧鹿,象征着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次说法;主座两侧饰有蹲狮和力士;八大弟子座下则分别塑有“八吉祥物”与双狮。
佛与弟子像座之上的壁面原有44尊影塑小佛像,现仅存11尊且均残破不堪。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排一佛八弟子须弥座前,另有一个向前突出的大须弥座,明显为后世增建,打破了原有格局,其上的塑像同样无存。
在须弥座北侧,立有两座土坯塔:前方为尊胜塔,后方为菩提塔。
▲古格王国遗址红殿里的佛像和壁画
红殿采用典型的藏式佛殿格局,矩形平面内设主尊佛龛及环形礼拜道。
如同西藏大多数佛殿,只要殿顶不坍塌,壁画通常便能得以保存。红殿殿顶的完好使其内部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壁画基本保持完整。
殿内四壁与顶部(望板)绘满壁画,总面积达数百平方米且保存较为完整。
壁画以矿物颜料绘制,主调红、蓝、绿、金构成沉稳厚重的色域,数百年后仍色泽明艳。
人物造型比例精准,肢体舒展优雅,面部融合南亚的柔美与藏地的庄严——菩萨与度母形象尤以细长眉眼、丰润双唇为特色,繁复精致的衣饰璎珞更展现高超的线描技艺。
▲多数壁画上使用金粉描绘
红殿壁画的构图采用分层设计,共分四层:
底层:描绘常见的兽面衔垂帐流苏二方连续装饰纹样。
主体层(第二层):占据画面总面积约三分之二,核心内容为“七政宝”等主题。
第三层:绘有“佛传故事”、“王统礼佛图”、“如来八宝”、“八吉祥物”等图案。
顶层:为梵文兰查体书写的经咒条带纹。
各层比例依据具体内容和殿堂高度灵活调整。出于视觉舒适性的考量,通常将底层的兽面衔铃铛垂帐流苏纹样设计得较宽,并施以精细绚丽的描绘。这种做法既满足了视觉需求,又以较大的面积有效装饰了建筑结构,衬托了壁画主题,形成了古格壁画独特的形式美感。
古格长卷壁画构图以其包容量大、内涵丰富、形式美观见长。各层表现内容虽异,却统一服务于中心主题。其装饰美不仅体现在多层次的条状构图和丰富多样的图像造型上,还表现为形象布局的疏密对比与大小变化,以及色彩的对比协调与图案纹样的精妙装饰。
古格壁画的形式美遵循着“三界构成法”(天、地、地狱)的理念,并在整体布局中得到了完美呈现。这种构图的形式美,作为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是古格壁画中最具审美价值和形式美感的核心部分。
壁画内容严格遵循藏传佛教仪轨,以密教题材为核心:
东壁:四臂观音-卡萨帕尼观音(绿度母)-三面八臂圣白伞盖佛母-金刚手-马头明王-三面八臂尊胜佛母-白度母-文殊菩萨。
其中以三面八臂圣白伞盖佛母,三面八臂尊胜佛母;绿度母,白度母;四臂观音,文殊菩萨,三组尊像构成护国、长寿、救难、健康、慈悲以及智慧的表意。
▲绿度母
▲殊菩萨
▲白度母
▲尊胜佛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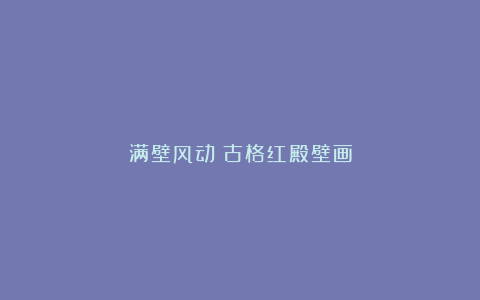
▲面八臂圣白伞盖佛母身
下部以正中大门为界,门北侧绘的是“如来八塔”、“七政宝”、“八吉祥”图案。
▲八塔
八塔——
菩提塔: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于摩竭陀国王舍城印度金刚座成道,降伏四魔而大彻大悟证正大觉,影胜王等在此处建造该佛塔。
天降塔:佛陀到三十三天为其母亲说法,在切利天夏住已毕,午前解制,午后下降南赡部州,返回人间桑伽尸国迦尸城后,人们为纪念其功德而在此处建造了该塔。
大神变塔: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在舍卫城降伏外道六师,勒扎波国王等所造。
息净即和解塔:佛陀在曼迦达和合僧众后建造了此塔。
善逝塔,即叠莲塔:纪念佛陀降生,净饭王在迦毗罗城蓝毗尼花园中所造之塔。
涅塔: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城涅,后人所造。
尊胜塔:佛祖患病接近涅时,众多弟子祈请不要入灭,佛祖告诉大家建此佛塔以代表法身。
吉祥多门塔:释迦牟尼成道四十九天后,在仙人鹿野苑为随侍五比丘及众生初转四谛法论,此后整个婆娑世界响起法鼓之音,为纪念此举建造。
▲七政宝及八吉祥
七政宝 轮宝:象征智慧法轮常转,可使众生开悟成佛。摩尼宝:象征志求解脱的坚定信心。后宝:象征欢喜心。君宝:象征三昧定。象宝:象征远离妄念。马宝:象征精进,勇往直前。臣宝:象征轻安。
八吉祥 吉祥结:象征回贯一切。法轮:象征佛法圆轮。莲花:象征神圣纯洁。胜利幢:象征遮覆烦恼孽根,觉悟得正果。宝伞:象征遮蔽魔杖,守护佛法。宝瓶:象征福智圆满。白海螺:象征佛音激荡无息。金鱼:象征自由豁达。
门南侧的南端绘表现古格国王率领王室家眷和大臣与僧俗群众以及宾客“礼佛”情景的壁画。
▲礼佛图之一 俗民及贵宾
▲礼佛图之二 王室成员及众臣
“礼佛图”是表现古河王室成员、大臣、宾客及僧俗群众礼佛的宏大场面。中间一尊无量寿佛,结跏趺坐于单茎双层仰覆莲座上;右侧主要为僧人礼佛图;左侧为世俗人物礼佛图。
右侧僧人礼佛图,分三层描绘,上层左侧二位高僧,中间三位高僧,均结跏趺坐于华丽宝垫上,双手合十于胸前;后有背光。
上册右侧分四排盘坐二十八位僧人,合掌胸前;中层左侧站立一名僧人,中层中间盘坐十人,其中僧人八名,俗人二名,中层右侧盘坐十人,其中僧人六名,俗人四名;下层左侧盘坐五人,其中僧人两名,俗人三名,下层中间盘坐八人,其中僧人六名,俗人两名,下层右侧盘坐六人,其中僧人二名,俗人四名。
以上所有人均合掌胸前,身稍侧左,面向整幅画面中间的无量寿佛。
门南侧北端绘“庆典乐舞”的场面。
▲庆典图之一 古格宣舞及木材运输过程
▲庆典图之二 狮子舞
“古格庆典乐舞图”全长十米,宽一米,是表现古格城堡落成之后,举行宏大庆典情景的长卷纪实性风格壁画。左上方绘有十名妇女,身着盛装,并肩一字排开,左右手臂隔左右侧临与第三者的手臂相交握,正跳舞蹈“宣”;左下方为表现修建古格城堡运送石块木料的场面,其中描绘驮石块的羊七头,驮木料的牛三头,用筐背石块者一人,横背木料者七人,后还有持木棍监工者二人。
右侧描绘的则是庆典乐舞杂技场面,其中敲击铜鼓者一人,击木鼓者二人,敲击皮腰鼓者九人,敲锣者一人,吹长号者八人,吹短号者二人,表演跑假马者二人,舞蹈者二人(其中一人扮演猴子),说唱者三人,舞狮子者一人,协助舞狮子者三人。从壁画中的人物动态可以看出,这些敲锣击鼓吹号者,又是舞蹈者。从画面看,供五十五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俗人也有僧人。
引人注目的是,壁画并未回避庆典背后的辛劳,坦然地描绘了建寺的背料者、驮运供品的牛群以及建筑寺院的运夫和走卒,他们正作劳役辛苦之状。这种对现实劳作的描绘,与贵族们安闲自得的静态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极富生活情趣。这些精彩的写实手法使人物活灵活现,进一步烘托出庆典整体的热烈欢快气氛。画家通过这幅作品,生动地捕捉并再现了统一庆典活动中千姿百态的世俗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
古格壁画的构图呈现出鲜明的装饰性特征,样式丰富多样,可用一个“满”字高度概括:柱身、墙壁乃至天花板均被绘画铺满,内容繁复、结构多变,却能做到满而不乱、井然有序。主题画被置于易于观赏的重要位置,其他题材则与之呼应,通过对称、均衡、规整统一而又富于变化的审美法则,共同构建出严谨有序、富有节奏感和装饰性的立体艺术结构。
古格壁画在构图上兼具设计性与随意性。设计性构图源于画面装饰功能的需求,或体现了创作者对布局秩序感的追求。与之相对的则是随意性构图,它无需精雕细琢的预先谋划,旨在表达意趣,充满感性特质和主观色彩,画面因打破规律而显得自由、活泼、富有动感。
▲庆典图中跳宣舞的妇女
例如,图中跳宣舞的妇女们,采用程式化的统一造型,其红色披风、黑色衣袖以及红黑条纹相间的长裙,共同构成了类似二方连续的图案组合,展现出严整的形式美感和强烈的装饰性。
▲古格宣舞 宗同昌拍摄
▲庆典图中表演班子 宗同昌拍摄
在庆典图中吹打表演的人群部分排列则自由多变,在整体上打破了过于拘谨的秩序感,为画面注入灵动气息,使整体构图更具节奏韵律。
古格壁画的色彩极其丰富浓烈,展现出强大的视觉张力。这种强烈的色彩风格,既源于宗教艺术感化信众的功能需求,也恰好迎合了信众们的审美心理期待。具体到古格红殿壁画,其用色特点鲜明:整体以暖色调为主,色彩浓艳热烈,营造出富丽华美的效果,同时通过强烈的对比形成别具一格的视觉感受。此外,画师们非常注重运用色彩的轻重(明度)变化来调节画面平衡。
▲礼佛图之局部 群臣及贡品
这一点在上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画面中盘腿而坐的群臣,其服饰色彩看似随意安排,实则极为讲究——巧妙运用白色提亮局部、黑色增加重量感,并让红蓝两色适当地交错点缀。左下角在深暗背景映衬下对比强烈的白色骏马,更是点睛之笔。这些色彩处理手法不仅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有效地平衡了画面结构,赋予其生动的节奏韵律感。
在色彩运用理念上,古格壁画并非简单地模仿客观自然对象的固有色,而是超越了客观限制。画师们根据壁画本身的审美需求和宗教功能,对色彩元素进行主动的提炼、概括、夸张与重构,创造出理想化的艺术色彩。与此同时,古格壁画极为注重二维平面上的色彩构成经营,这体现在对色彩主次关系的把握、冷暖色域面积的精心分割、色彩位置的巧妙安排以及各种色彩对比手段的有效运用上。正是通过这些精心的布局,最终使得画面色彩既呈现出和谐与呼应的整体基调,又能产生富有节奏变化的对比效果。
古格壁画的造型法式与艺术风格,清晰地反映出印度、波斯、克什米尔、西域等多重文化的影响。然而,它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成功融入了古格艺术特有的娟丽、清俊、精细、质朴与写实的本土特征。
▲礼佛图之 古格王与王子
▲礼佛图之 王室眷属
红殿《庆典图》的前半部分,描绘了身着华服的古格王、王妃及大臣眷属的群像。国王与王妃盘坐于垫上,面容安详静穆,气质高贵,头部微向左转。人物面部呈现短圆轮廓,眉形弯长,眼睛较大,嘴角那抹类似希腊古风的微笑,巧妙融合了力量感与柔美感。国王形象年轻俊美,神情自信而沉静;王妃则头部微向前倾,面容端庄中透出妩媚,虔诚恭谨的姿态流露出女性的雍容与柔美,堪称藏族壁画女性形象的典范。同排的大臣眷属们皆结跏趺坐于垫上,姿态各异:有的双手合十,有的辅以手势,表情谦恭,目光汇聚于同一方向。他们的面部特征基于同一基本图式,再施以不同的细节修饰以示区别,体现出鲜明的符号化造型特点。
画面中远道而来兄弟邦国参加典礼的信众嘉宾形象则形成生动对比:有的背负行囊,有的手持木棍,面容刻画得较为憔悴,通过其独特的形象、服饰以及人物肤色的色彩描绘,可以清晰辨识出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乃至中原使者的身份。这种状态与上方贵族们的安闲自得形成强烈反差,平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香客们造型丰富多变、灵活且富有节奏感,其排列方式又与整齐划一、造型近似的贵族群体遥相呼应,在整体构图上形成了极具趣味性的造型对比,更赋予了作品隆重的政治历史意义和浓郁的宗教氛围。
南壁:不空成就佛-阿弥陀佛-宝生佛-毗卢遮那佛(已毁)-不动佛-释迦牟尼佛,六尊像构成五方佛与化身佛的表意。
▲释迦牟尼佛及其二意子即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
▲不动如来及其近佛子
▲大日如来及其近佛子
▲宝生如来佛及其近佛子即除盖障菩萨和地藏菩萨
▲宝生如来佛及其近佛子即除盖障菩萨和地藏菩萨
▲无量光如来佛及其近佛子即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
▲不空成就如来佛及其近佛子即虚空藏菩萨和弥勒菩萨
北壁:释迦牟尼佛-燃灯佛-狮子吼佛-不动佛-释迦说法佛-释迦法轮佛,释迦六佛,六尊像构成三世五方广传佛法的表意。
▲佛二菩萨即释迦法轮佛及其近佛子文殊菩萨和持金刚菩萨
▲燃灯佛及近佛子文殊菩萨和手持金刚菩萨
▲狮子吼佛及近佛子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
▲不动佛及二近佛子
▲迦法轮及普贤菩萨和弥勒菩萨
▲释迦法轮及虚空藏菩萨和弥勒菩萨
南北两壁诸佛胁侍是十二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除盖障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无尽慧菩萨,地藏菩萨,宝手菩萨,虚空库菩萨,除忧暗菩萨,辨积菩萨。
南壁和北壁下部壁画绘“佛传故事”。
▲佛本生传之一 佛祖涅槃
▲佛本生传之二 伏醉象、猴子献蜜
南北两壁诸佛胁侍是十二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除盖障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无尽慧菩萨、地藏菩萨、宝手菩萨、虚空库菩萨、除忧暗菩萨、辨积菩萨。
纵观红殿壁画,人物形象普遍遵循着古格样式的造像法则:头部比例较小,四肢修长,腰部纤细,体态挺拔而姿态婀娜。门廊处的十六金刚舞女形象,正是这一法则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人物身份尊卑或体量大小,即使是现实人物的描绘,都自觉运用这套法度。
这充分表明,古格样式已内化为艺术家们共同的审美准则,标志着古格壁画已从借鉴外来艺术形式,成功发展至自身造型风格的成熟巅峰——实现了内在形式语言与审美品格的和谐统一,达到了一种协调自律的艺术境界。
红殿壁画的价值在于集大成的风格整合与高度成熟的技法:画家通过透视叠压与色彩渐变在有限空间营造三维层次,人物群像的排列兼具宗教仪轨性与韵律感。细节处采用’沥粉堆金’工艺刻画织物纹理与珠宝光泽(原镶嵌宝石多已脱落),折射出古格王室对佛教艺术的倾力投入。
从文化史视角看,这些壁画既是宗教圣像,更是丝路文明交流的实证——印度波罗风格的密教图式、中亚装饰母题与汉地青绿山水在此交融,形成跨越地域的视觉语言。
作为古格艺术遗产的核心标本,红殿壁画以其独特的审美体系与历史信息,为研究西藏佛教艺术演进与文明互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严谨的造像度量、精湛的绘画技艺与深厚的宗教内涵,共同铸就西藏壁画艺术史上的高峰,深刻影响了后世藏传佛教艺术。
如今,这些历经沧桑的壁画仍以恢弘气度与精微细节,向世人昭示古格王国曾经的信仰荣光与艺术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