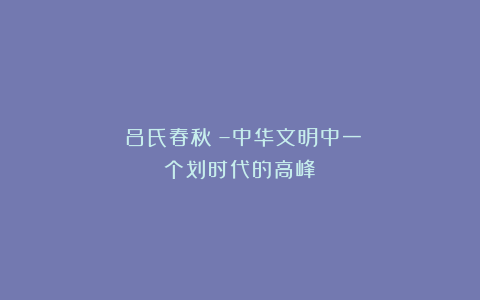|
一、一部帝王教科书
中国历史上号称帝王教科书的很多,但大都失于一技几技的偏颇,也大多不敢自认,是后人恭维的名义。《吕氏春秋》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开宗名义公开声称帝王教科书的著作。它在《序意》即序言中写道:“唯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子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对这段话不管怎样具体解读,但其中吕不韦要效法当年黄帝教导颛顼如何作帝王而主编《吕氏春秋》一书的意图都非常明显。再看其他的著作,《论语》《孟子》《荀子》《墨子》《春秋》等诸子百家,没有一家敢作如此表白,其原因很简单,吕不韦是让秦王政和其父能承袭王位的操作者,“奉先王功大”,在其父未成为王时就被其祖父请为其父的师傅,其父一成为王,就马上“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成为秦国的第一权臣,重臣;“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以上引文见《史记》),全权摄政,成了无冕之王。其他诸子百家都没有这样的身份,当然也不敢放此等大言。
实际上,该著作从内容上看,也的确是一部帝王学的全面教科书。
二、兼收并蓄的集大成者
《吕氏春秋-用众》篇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后来这一说法成了一个成语“集腋成裘”。吕不韦以此来说明要“用众”,《吕氏春秋》也就这样集百家之“腋”,而成就了一家之“裘”,被《汉书》称之“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当时的诸子百家,后来被《汉书》归类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家。这、些家我们在《吕氏春秋》中都可以看到被继承的影子,更可以看到被杂糅综合发展而另出精彩的光芒。
(一)《吕氏春秋》与儒家
《吕氏春秋》尊崇孔子,但没有把孔子奉为唯一的圣人,它极赞成仁,却没有把其放到中心的位置,而是放在道之下。它主张“仁乎其类”,即对自己的同类仁爱,与孔子思想不同。《吕氏春秋》也推崇礼,但不像孔子那样搞繁文缛节,说礼繁琐就不庄重了。《吕氏春秋》很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显然受了孔子影响,但也贯穿道家自然之义,把音乐同其自然观结合,这是孔子和儒家没有的。《吕氏春秋》极赞成孔子重视教育的思想,却不排斥他学。《吕氏春秋》和孔子一样把孝作为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之本,但却将孝又同法家的耕战结合起来。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方面,显然受到孟子的深重影响。它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力量的观点,君臣之间主张对应关系等都与孟子思想息息相通。它重视士人的独立性,强调节操,主张杀身成仁,明显继承于孟子。它敢于对君主采取尖锐的措辞,直抒己见,也具孟子风貌。当然,他们的身份不同,孟子在野,而吕不韦在政,孟子的见解多为建议,张扬迂阔,而《吕氏春秋》的见解则多为从实际出发的结论。他们都主张统一天下,孟子主张去兵,认为“人性善”,只要实行仁政,就可达到目的;甚至认为只要有了仁政,未经训练的民众也能打败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就能战胜野蛮。《吕氏春秋》批评了这个看法,认为无法去兵,主张以义兵统一天下。孟子只赞许王道,《吕氏春秋》对王道之外的“帝者同气”“霸者同力”,都予以不同程度地肯定。孟子还主张恢复古时的井田制,《吕氏春秋》认为时代变了,古代的好办法也行不通,主张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这些差异,既反映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差别,更反映了《吕氏春秋》的技高一筹。
《吕氏春秋》与荀子的思想近似,他们都在为统一的封建帝国设计蓝图,都反对严酷政治;在自然观方面,都反对神秘主义和唯心论;在认识论方面,都主张保持虚、静,去掉主观方面的蔽障,如实认识事物,等等。荀子把礼放在第一位,其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必须用等级制度的礼来约束和改造,使之变成人为的善。荀子虽然也讲民众的力量,但总从消极方面着眼,从性恶方面着眼。《荀子·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告诫君主,应重视礼,否则百姓的“恶”性发作将不可收拾。《吕氏春秋》既不将人的本性说成“善”,也不说成“恶”;既认为人的欲望是合理的,又认为过分超常的欲望是有害的,应该节制。在这些方面,它的观点是公允的。
《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比荀子更卓越。它不是消极地看到民众载舟、覆舟的力量,而是强调积极地因民之力去做事业,去建立功业。它理论中的君民关系,不仅是船和水的关系,而是“君之所以主,出乎众也”,君主是大众立的。它虽然也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谈如何治理民众,但却更强调利民而不自利,“仁义而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而不强调用分别尊卑上下的礼去治理民众。
(二)《吕氏春秋》与法家
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所讲的法治,不同于现代法治,他们只不过把君主的规定予以公布强制推行而已。法家重视赏罚,奖励耕战,不重视德化。法家分为法、术、势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吕氏春秋》主张无为,上德,这与法家相抵,但它不排除赏罚,将这种法家的主要手段作为辅助手段。它重视农业,强调用义兵统一天下,也吸收了法家的耕战思想,但明显地进行了改造。《吕氏春秋》十分重视贤人,内涵与法家不完全相同,其主张循名责实,又吸收了法家的主张。《吕氏春秋》有《慎势》篇,讲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依靠势,“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如何保持君主的势?它主张“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这就把慎到的重势和儒家的重名分杂糅在了一起。《吕氏春秋》还有《任数》一篇讲术,引用了不少申不害的话。不过,它主张的“术”,是顺应自然,君主无为,这与法家的“术”派主要讲耍弄权术,有很大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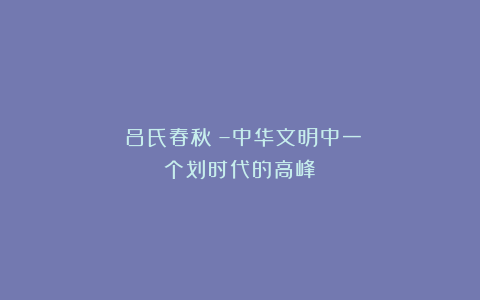 法家韩非综合法、术、势,而又以《老子》作理论基础,中心是巩固专制君主的权力并防止别人篡夺,分析问题全从争夺权势的利害关系出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道出了韩非学说的特点。但韩非继承《老子》理论的仅是一面。《吕氏春秋》同《韩非子》大体上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都采用《老子》思想作理论根据,却引出相反的主张,继承发展了《老子》思想无为贵柔的另一面。
法家韩非综合法、术、势,而又以《老子》作理论基础,中心是巩固专制君主的权力并防止别人篡夺,分析问题全从争夺权势的利害关系出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道出了韩非学说的特点。但韩非继承《老子》理论的仅是一面。《吕氏春秋》同《韩非子》大体上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都采用《老子》思想作理论根据,却引出相反的主张,继承发展了《老子》思想无为贵柔的另一面。
(三)《吕氏春秋》与道家
《吕氏春秋》中,“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对《老子》的道作了改造,即用“精气”来解释,使“道”具有了可捕捉的内容。“无为”,“无为无不为”,是“老子”的核心观点,《吕氏春秋》对此极为推崇,极有见地地将它用于君道,也只把它用于君道,将这一理论内涵作了特别定位,这就将《老子》的这一见解明晰化了,政治纲领化了。《吕氏春秋》认为,无为,只是对君主的要求,是为了不妨碍臣下的有为,使君臣更好地配合;“无不为”则指君主无为之后产生的效果。与此相应,对“虚”“静”“无识”等的解读,《吕氏春秋》都用来囿指君主,与《老子》本身的解读有很大区别。《吕氏春秋》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主、张教育,不赞成《老子》的愚人政策。
《老子》认为,这样才会安居乐业,和平幸福。这是对“春秋无义战”让百姓社会不得安宁的一种厌弃,可却又走向了反动。《老子》认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说,道、德、仁、义、礼等,在社会规范中是逐次递减的层次,越往后越不好,最后出现的就是儒家推崇的“礼”最糟,忠诚信《老子》的理想社会,是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不用兵器,不坐车船,甚至不用文字,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彼此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守都淡薄了,大乱由之产生。这些看法确有哲理,人类社会越发展,离纯朴越远,社会规范越来越多,防不胜防的丑乱现象也越来越多。《老子》深刻地观察和描述了这种现象。但是,《老子》想用退回到上古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前进中产生的问题,既不可能,又不应该。正如江河源头的涓涓细流,极为安静清纯,极少泛滥,不设堤防,极为本分。渐渐流去汇成大江大河,奔腾四泄,让人防不胜防。但却能量非凡,可让百舸争流,万船齐发,龙鱼竞跃。我们不能只看到驯服它的艰难,还应看到它巨大能量的壮美,更不能让它倒流回源头。万千的复古主义者不管思想出发点再神圣,都像要将江河倒流回源头,大智实愚。孩子长大了,难免产生争斗,真的高明是如何化解争斗,将成人过剩的精力引导到兴利除弊上来,而决不能企图让成人返回婴儿,将其缩身缩智再装进襁褓中去。若真有统治者这样做,并将其变成社会规范强制推行,必将扼杀成长、泯灭人性、残害生灵。道德之法“其极惨磯少恩”的原因就在这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与韩非合并作传,其道理也在于此。《吕氏春秋》就反对这样的倒退。它在《恃君》篇中描绘上古社会即《老子》中鼓吹要返回的理想社会还有另外野蛮的一面,“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人们并非都过着《老子》所描绘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这样的分析是历史的真实。
《吕氏春秋》的思想,是创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因此,它很重视贤人,重视民心向背,重视教育,重视音乐,重视农业,重视义民,德化为主,辅以法治,而且主张运用一切社会规范,以建立统一、繁荣、强大而人们又能安居乐业的盛世。所以,除了尊崇道之外,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利以及赏罚,等等,都被吸纳,将先秦诸子共有的和独有的社会理念,融为一体,虽然有的不乏牵强,但却充分表现了其集大成的杂家风格。
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庄周,代表他思想的是《庄子》一书。《庄子》和《老子》一样,以道为本,讲无为,讲虚、静,甚至更彻底地否定俗世的一切,但却追逐精神上的超脱和自由。《庄子》一书,文笔优美,汪洋恣肆,常用轻松谐趣的寓言表达严正深刻的思想,用犀利讽嘲的笔锋揭露社会弊病,有时表现为消极玩世。以积极治理天下为己任的《吕氏春秋》,多次引用《庄子》中的故事,但从中导出的结论,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吕氏春秋》的《求人》篇,记述尧让天下与许由,许由不同意的故事,也见于《庄子》,可在《庄子》中,是赞扬的许由不受天下,保持精神的逍遥,而在《吕氏春秋》中,则用这个故事说明君主应当像尧那样积极求贤。而有些方面,《庄子》的思想却被《吕氏春秋》直接吸收。如《庄子 无道篇》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厖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就和《吕氏春秋》反复强调多方论证的主旨完全一致。
(四)《吕氏春秋》与墨家
《吕氏春秋》有不少地方接受墨子学说的影响,它强调“爱利”,就是接受的墨家思想。儒家讲爱有等差,只讲义不讲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在这些方面,《吕氏春秋》赞成墨子思想。重视贤人,儒、墨两家相同,《吕氏春秋》于此儒、墨并举,不排斥哪一家,但从它尚贤又不强调等级和亲疏看,还是与墨家更相近。
(五)《吕氏春秋》与阴阳家
《吕氏春秋》用阴阳五行说作为桥梁,上接精气说,下接社会。《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春季属木,夏季属火,秋季属金,冬季属水,而把土放在夏季之末,即一年的中心。因为按五行的方位,土在中央,也就应是一年的中心。在每个月中,也是按五行推演和诞生出若干事物和规定。它运用五行说的循环论,阐述王朝的更替由五种气决定,源接精气说,说明历史何以变迁,王朝何以盛衰,贤人为什么有的遇合有的不遇合。这样,就保证了道法自然之义,让其贯串“天地万物古今”,而成为一个有逻辑的体系。五行更替形成的五德终始,是《吕氏春秋》主张变革的理论基础,主张因时的不同而变法。但其所谓的变法,只是君主制范围内的调整,而不是改变或推翻君主制。五德终始这种循环的历史观,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患上了科学的先天不足症,最终还要归宿到“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艺文志》概括阴阳家的特点是:“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吕氏春秋》虽从出发点上不相信上帝鬼神,崇尚自然之天,强调按时令季节行事,但却没有从敬顺昊天中跳出,最后仍然被其所拘。
(六)《吕氏春秋》与名家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出,百家争鸣,穷究根底,自然就引起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形成“名辨思潮”,开始有关名、实问题的讨论,即名称概念和实际事物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如何区分。在这方面特别下功夫而成一家之言的,后人称之为“名家”。著名的名家,有惠施和公孙龙等。名家的讨论涉及的是逻辑问题,可以看作中国古典逻辑学的滥觞,可惜世人不解,如白马非马、离坚白、鸡三足、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目不见、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等等,虽有概念的置换诡辩,却充满辩证逻辑思维。《吕氏春秋》是部实用之作,显然对这些不太感兴趣,虽然也引用了名家的一些观点,记录了一些资料,却没有认真分析。
(七)《吕氏春秋》与兵家
当时,墨子提出“非攻”“救守”,宋钘、尹文提出“偃兵”,《老子》反对战争,儒家不言兵。而秦国从商鞅变法后就是一个嗜血的国家,特别是到秦昭王时任用白起等一些“人屠”,更是“恃兵”。《吕氏春秋》于几者之间,提出了“义兵”说。它论述道:“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为什么?因为当时天下最大的问题是处在“无天子”的“浊世”,不统一,诸侯混战,造成“黔首之苦不可加”,而统一就必须兴兵,“摄敌”,“生民”。兴什么兵,就兴“攻无道而伐不义”的“义兵”,“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义兵至,则临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服若化”。
《吕氏春秋》的“义兵”说明显继承了孟子的“仁义之师”和荀子的“仁义之兵”,但它不轻视其他因素,这是吕不韦作为政治家比孟子单纯的思想家高明之处。孟子认为,施行仁义“不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吕氏春秋.简选》不点名批评了这一说法,认为“此不通乎兵家之论”,具体到战事中间,“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吕氏春秋》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执政“仲父”的“义兵”体系。
(八)《吕氏春秋》与农家
农家据《汉书 . 艺文志》记载,也是战国时期的诸子一家,其著作有《神农》《野老》等,都已失传。其中的观点只能从《吕氏春秋》中找到痕迹。《吕氏春秋》一开始辟出《十二纪》,一个主要意图就是指导春耕、播种、收获等农业生产活动。它更在最后辟出《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全面阐述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在《上农》篇中,它将务农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务耕织者,以为本教”,要求农人“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要求种上等田的农人一人供九人食,种下等田的一人供五人食。在农事大忙时,不兴土木,国家不进行战争,平民一般不得摆酒聚会,农民没有官府同意,不得私自雇人代耕。不是通婚族,成年男女不得到外乡嫁娶,以便农民安居一地。土地未耕好,不得下种,年轻力壮者,不得从事种庄稼以外的果蔬和饲养畜禽活动,力量不足的不得扩大耕作面积。农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与农耕无关的行业。不到适当季节,不得伐木,水泽地区不得割草烧荒,不得捕鸟捕鱼。
在《任地》篇中,它制定的耕作原则是:硬实的土地要将它整得松软些,柔稀的土地要让它硬实些;休耕过的土地要适时种,种乏的土地要休耕;贫瘠的土地要施肥,过肥的土地要让它贫瘠些;过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燥些,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高处的田不能将作物种田垄上,低洼的地不能种在垄沟内。播种之前要耕耙五遍,播种之后要锄五次。耕种的深度必须要见到湿土。翻地的耜柄长六尺,用来计量田垄的宽窄,耜刃宽八寸,用来挖出标准的田垄。同样,锄柄的尺寸用来计算行距,刃宽六寸,用于间苗的间距。施过肥就要浇水,使庄稼苗生长旺盛而有间隙通风。早了就要锄,以防板结而保墒。
在《辨土》篇中,它指出要因地制宜,耕作要分别土地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措施。要先耕种墒情差些的,再耕种墒情好些的,缓种含水过量的。高处的地耕种时要耙平,有积水的要将积水排净。要合理密植,及时清除杂草。农耕必须适于农时,不按农时耕种,即使尽力经营也不会有好收获。有的修治田畦,又高又陡,这样水分就容易散失,畦面还易倾塌。庄稼种到这样的田畦上,遇风就会倒伏,培土过高就会连根拔出,天气冷一点就易凋零,天气热一点就易枯萎。所以,田畦应该又宽又平,垄沟应该又小又深,这样,庄稼下得水分,上得阳光,才能苗全苗壮。庄稼应在细软的土中萌发,而在坚实的土中生长。播种不可过密或过稀,覆土盖种不要使土不足,也不要过厚,盖种的土要细碎且撒得均匀。田畦横要恰当,纵要端直,和风通畅。间苗的时候,要安养先生的壮苗,去掉后生的弱苗。
《审时》篇进一步论述了谷子、黍子、稻子、麻、豆子、小麦种得适时就可高产优质,种得不适时就会减产质差的具体表现,种得适时的作物,它的气味香,味道美,咬劲大,吃上一百天就能耳聪目明,心神清爽,四肢强健,邪气不入,身体就不会得意想不到的疾病。
读着《吕氏春秋》关于重农的这些论述,感觉作者哪像一人叱咤风云的帝王“仲父”,简直就像一个老农在怡然自得、循循善诱地教后生种地。这让我们看到了吕子的又一面,真正接地气、重民生的实实在在的一面。
《吕氏春秋》重视农业生产,从开篇到结尾,都强调农业生产,可谓有始有终。这在当时的诸子中是凤毛麟角的仅见。儒家大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夫子据传思想包容性够好了,他在周游列国期间数次被不同派别的人挖苦痛斥都能“耳顺”,可却听到弟子樊迟向他请教农事时竟勃然失态开骂,可见其不通经济,也不把农作经济当回事。墨子勤劳朴素,却心底清傲,对农事也不屑一谈。其他诸子更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者。只有吕不韦,只有《吕氏春秋》,将农业生产泱而大之,神而圣之,将农业生产知识不厌其细地收入,堂而皇之公之于世,和其他内容一并操弄一字千金。纵览其他诸子的学问,都是吃饱肚子之后的“有闲”学问,是“士”的学问。只有《吕氏春秋》,不但兼容了那些有闲的“士”的学问,还有如何吃饱肚子的“农”的学问。这些农事篇章,《十二纪》中的是给君主看的,后四篇很明显是写给农人看的,让人感到了《吕氏春秋》的以农为本国策的实在。也看到了吕不韦这个人在经济管理上的脚踏实地。这种政治经济学问,将吕不韦的另一面-实干家的形象和他等清谈家区分开来,成就了他卓然独立的一个全才领袖,一个真正的懂经济、会管理、善治国的巨擘形象。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吕氏春秋》在评介其他诸子时,总是以平和的笔融,没有势不两立的箭拔弩张,也没有不同类而相斥的冷嘲热讽。《不仁》篇写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这种对不同见解的包容公正、尊重对手、海纳百川的情怀在那时的思想家中仅有无二。
《吕氏春秋》极了不起的又一贡献就是给出了一个国家统一后的崭新的政体设计-一虚君实臣,一个很像两千年后君主立宪政体的设计。
“爱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很明显,这句话是直接对当时的秦王政讲的。大圜代表天,意思是缔造万物,包容天下;大矩代表地,意思是养育万物,有方有法。“君执面,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圜”,臣子应该效法“地道方”,君臣应按照这样的分工,各处其位,国家才可昌盛。圜,罩住一切,又不是一切,无矩无方,没楞角,不是具体的器物,不能作工具和用具。矩、方有楞角,是器物,作工具和用具。
(二)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吕氏春秋》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据此,《吕氏春秋》引出“圣主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也”,’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要“贵公”“去私”,“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是让“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既然如此,天下就必须共同治理。
这些话讲得太漂亮了!如果不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放在那里,真让人不敢相信,这种公天下的理论竟然出自2240年前的中国古人之口!
(三) 生命健康比权位重要
《吕氏春秋》用《本生》《重己》《贵生》《先己》四篇论述贵生、重己的道理,单从这四篇的标题就可看出作者是如何重视生命健康,“圣人深虑天下,莫若贵一生”。他甚至认为,“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大道真谛,是维护生命健康;在此前提下,再去考虑国家的事,如同用土壤中自然长出的种麻织网织物一样,去治理天下。天子如果不能贵生,放纵情欲,贪恋权势,喜好特殊褊狭,就不能完善自身,不能公正听取意见,就会受物欲引诱,被奸邪所惑,更不会爱惜他者生命,就无法治理好天下。“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就是说,只有不把天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这又是何等杰出的见解!即使拿到今天,拿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卓越而前卫的!
(四) 怎样虚君实臣
1.君主不要亲自做具体事情
“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君主没有具体处理某项事务的职责,而是将这些职责分给主管的臣下。“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以来也。”就是说,君主以不做得当的事为得当,以不做得体的事为得体。因为做事本身不是君主的事,是臣下的事。所以善为君主的人碰到具体事处理,不要卖弄自己的先见,更不要亲自去处理。一遇事就先发表见解,难免有时不完备,去处理具体的事,也难免不周全。这就会引起臣下的不信任,也会给奸邪之徒以可乘之机。“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君主要处在一个不让臣下知道自己什么主张,无任何色彩的地位。“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皆能”;“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千官皆能,从众能为,还有什么事办不好呢?“不为者,所以为也。”
2.君主的职责是用贤
“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径也。”“佚于官事”,就是不去做臣下的事;“劳于论人”,就是努力识别人才,善于用人。“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功名之主,其本在得贤”;“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吕氏春秋》认为,真正的治国大贤是极稀少的,“千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就是说,方圆千里内能有一个这样的大贤,就等于肩靠肩了;几代人中有一个圣人,就是脚跟脚了。正因为如此,贤人特别珍贵。
怎样识别贤才呢?《吕氏春秋》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之法。所谓“八观”,就是从以下八个方面观察人:通达时,看他尊敬什么人;显贵时,看他推荐什么人;富有时,看他赡养接济什么人;对别人的意见,看他采纳什么;闲居时,看他爱好什么;学习新东西,看他的见解是什么;穷困时,看他不接受什么;贫贱时,看他不做什么。所谓“六验”,是指从六个方面检验:使他高兴,以检验其操守;使他欢乐,以检验其邪辟与否;使他生气,以检验其节制的能力;使他恐惧,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原则;使他悲哀,以检验其仁爱之心;使他困苦,以检验其意志。“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四隐”指朋友、故旧、邻居和亲近的人。通过对他这些不同境遇、不同情绪、日常人际环境的观察,全方位了解其真伪好坏,从而找出贤者予以重任,发现不肖者予以贬斥。
3.静因之术
“因者,君术也。”善用凭借,借力发力,集力发力,是君主的统治之法。静因之术,就是君主自身始终处在超然事务的沉静状态,却时时留心观察各种动态,了解各种意见,“静以待时,时至而应”,找准时机,弄准方法,因势利导,借助能借的力量,将大事一举做成。
君主应该让臣下先说先做再表态。“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人,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以执其要矣。”这就是说,君主应先充分听取发言者的意见,再综合各种意见,根据各种情况采纳其真实合理的,责弃其虚妄的,这样才能正确决策让人服气。
《吕氏春秋》认为,人们在认识上常常“多有所扰”,都会有一些局限性和错误,君主也不例外。如果君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总是自以为是地发布施令,臣下必然都不敢发表意见,更不敢报告相左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君主就会成为“重塞之主”,就难以保住地位了。所以,“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因而不为”,指依靠臣下做事而不自己动手去做;“责而不诏”,指督促臣下处理事情而不发具体指示;不代臣子说话,不抢夺该臣子做的事情做,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法宝。“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根本的是“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真正的明君,不体现于什么都会干,而是体现于将百官选拔好,知道他们谁能干成什么,将他们驾驭好,让他们将各自的职责办好,这就是静因术之本。
《吕氏春秋》这种政体设计,在当时既区别于周朝的分封制,又区别于五霸制,更不同于当时秦国自秦惠王以来的君主制。虚君实臣,在中国历史上有为的君王时代好像只有一个商鞅变法时期,其他时期也有,却大都是君权旁落或昏君被惑的几近乱世。而商鞅变法是秦国兴旺的根基,这恐怕是《吕氏春秋》能提出这一政体设计的一个由来。从《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找到秦朝兴盛的经验,而秦朝灭亡的教训,又大多因背离了《吕氏春秋》的设计。把这种政体设计和近代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通之处。
越研读《吕氏春秋》,我越感到它的伟大,它是诸子百家中最全面而少片面的集大成之作。难怪司马迁称其作者为“贤圣”,为“倜傥非常”;更难怪高诱盛赞它“大出诸子之右”。
真的,《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它有许多空谷之音的绝响,它是中华大一统文明中一个划时代的高峰。
张满飚,男,1949年生于河南省濮阳县。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主要职务有郑州大学中文系教师,濮阳市档案局局长,濮阳日报社社长,濮阳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濮阳市政协提案委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