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他讲,我记,留下一些历史细节。
她拿命救了我
1942年,冀中要收麦子还没收的时候,敌人要扫荡了(注:即五一大扫荡)。那会儿仗打得多了,部队带着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比较困难,决定把我们分头坚壁到几个村的老乡家,我们管这样的人家叫堡垒户(注:抗战时期掩护抗日人员、伤病员或机关、物资的农户称为堡垒户)。
我被安排在献县方周村一户老乡家,这家老头叫张扬,是老党员,大娘叫段秀卿,这个名字我一辈子不会忘!他们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几岁,在外面参加了县大队。
教育股长赵一久嘱咐我:你就在这儿等着,不管出什么事,不能暴露自己。坚壁期间不能随便和人搭咕,怕万一说漏嘴被出卖。
他把我的头发用剪子剪吧剪吧,就把我为演戏留的分头给铰了,弄得跟狗啃的似的。
这家老头说我叫罗光明不好,那会儿农村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呀。大家就想改个什么名字好,我说就叫张保胜吧,随老头的姓,名字保胜,就是保证胜利归队!他们说:好!这个名字好!农村里有叫这个宝那个宝的,说你一定要保证胜利归队!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
部队走了,把我撂下了。
这家大娘可疼我了,“我儿呦——我儿呦”地叫,就跟她自个儿生养的似的,给我穿打着对襟儿的土布小白褂,裤子是青色土布,纳底子布鞋,跟村里孩子差不多的打扮。
一天早上,天没大亮呢,敌人来了。
那会儿日本人常常在傍黑或凌晨突然围住一个村,然后掏窝搜人。村里人慌得都奔村外的麦田里躲。日本人就把麦田围起来,然后骑着马往前趟,后边有“白脖儿”(注:指伪军)端着枪从麦田里往外赶人。
大娘吓得浑身发抖,我心想,坏了,跑不了了。
方周村不大,有一条南北向比较宽的街道,宽到能走大马车。结果,人们被赶回村里这条街上。
大娘叮嘱我:“我儿呦!别怕,就叫奶奶、叫爷爷,听见没?”
日本人把村里人小孩归一拨,妇女老人归一拨,一边还抓了好几个年轻的,是不是民兵不知道。我看见敌人把人绑在梯子上吊着头灌水。
一个姑娘吓得拿锅灰往脸上乱抹,看见我,一把拉过去抱着,浑身哆嗦。还好,鬼子没怎么样她,可能嫌她脏了吧唧的。
那个高丽棒子最坏了,中国话日本话都会,比汉奸还坏。老舍《四世同堂》里就说高丽棒子是“高级奴才”。
日本人由高丽棒子带着,审这个审那个,回来审到我们小孩这儿。
二十来个小孩一个挨一个蹲在地上,我个儿小,排在后面。高丽棒子先问前头的小孩:“你是儿童团不是?”
“俺不是!”
乒乓揍一顿;问下一个,还不是,又挨揍;日本人也“三宾的给!”(注:扇耳光)
我一看,不好,就捅捅旁边的小孩:再问,就说是,说是就不挨打了。你想想,这是抗日根据地,小孩能不是儿童团吗?
等那个高丽棒子问到我旁边儿的小孩,他就回答:嗯呐。
嘿,这小子还老实,“啪”打一巴掌就过去了。
轮到我这儿,坏了,我那会儿还满口天津话,他一听,口音不对。刚坚壁时,这家老头就让我学说本地话,可现学来不及呀,我说我会天津话,他说那好,方周村尽有在天津做买卖的。
高丽棒子把我揪出来,问:“你哪的?”我就装作吓得大哭,还用天津话大声嚷嚷。
大娘疯了一样扑过来,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哎呦,我儿呦!是我儿呦!”
我也“奶奶、奶奶”的叫,她紧紧抱着我。
高丽棒子转脸问旁边的人;“他是哪的?”
“就是俺们村的”,村里人都知道我不是这村的人,可都在那喊。我还听见大娘家对门的平安嫂也在喊:“他是从天津来的!”
高丽棒子二乎了。有人站出来证明:我们这有下天津卫做买卖的,他是回来看爷爷奶奶的。高丽棒子再瞅瞅我,觉得也不像个军人,就把我搡回去了。
大娘挨了他两脚,给踢倒地上,满嘴是泥,嘴角还流了血。
后头几个比我还小的,他就扒拉扒拉,没再问。
后来知道在邻村坚壁的一个小战友牺牲了,因为他个子高,口音不对。
我在大娘家坚壁了一个多月。
现在想想,那会儿我们的军队还是很受老百姓拥护的,平时给烧个热水、腾出热炕头……关键时刻真拿命来保护我们八路军,特别是老乡看我们这么小就抗日,可心疼了。
(附记:抗日名将吕正操讲过这样一段话:“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
大娘(铅笔)
这枚奖章是父亲经历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军区颁发的
封门
1948年,我回献县方周村看我大娘。我给她留下缴获的日本人的丝绵裤、大蚊帐,还有围巾、棉被、衣服什么的。我说你别舍不得用,以后我只要打不死,缴获敌人的什么东西我都给你留着。
大娘一声一声地叫着“哎呦我儿呦……”
第二次回去是闹土改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叫韩洪彬的战士,他背着一支冲锋枪,我带着一把手枪,我们是骑马去的。
我到家一看,哎?我大娘家怎么给封门了?她住的那小间门也上着锁。怎么回事?我上街一问,说是村干部把你大娘家给抄了,说她有洋钱,还搞剥削。
我知道大娘家以前做过门箱柜买卖,家里有四亩地,大娘是小脚,干不了重活,让她叔伯侄子帮忙,就说她剥削人,还说她家里藏着浮财。土改把地富家里头的粮食、洋钱、工具什么的都算浮财。
村干部非要让她交出洋钱。她说没有洋钱。他们就给大娘圈起来不让出屋。
可能是我回来的消息传出去了,村上很快来人把锁打开。
大娘坐在炕上,看见我一下愣了。
屋里的箱子、柜子都贴着封条。
我说大娘你认不出我啦?
“哎呦,我儿呦——”抱住我就哭。
我问她怎么回事,土改怎么改到咱们头上来了?我在定县搞过土改,懂得点政策,我说整谁也不能整我大娘呀!
我要揭柜子上的封条,大娘说你可别惹事,还说我给她的东西都给抄走了。
我说,大娘你别哭,我不会惹祸,但是东西该还的都得还回来,一样不能少!
我带着韩洪彬上了村公所。村干部都吓跑了。
过了会儿,突然进来五六个民兵,拿着破枪。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是民兵组的。我说你们拿枪干什么?他们互相瞅瞅没说出话来。那个韩洪彬挺愣的,把冲锋枪一端:“都给我撂下!”他们乖乖地都把枪撂下了。
我让他们把村干部叫来,就提我的名字保胜,他们拿上枪就跑了。
待会儿,来了三个村干部,其中一个说:“哎呀,不知道是你来了,保胜,我们都知道。”他们告诉我,土改以后,好多部队的人因为家被抄了回来跟他们干仗,有的就动武。胡可写的《槐树庄》里就有这种事。我说我不是这里的人,我也不是地主,不会反攻倒算,我就想问问把我大娘家封门的事。大娘掩护过八路军,她一家都是革命的,儿子牺牲了,老头后来被日本人杀了,结果怎么会这样?
他们说是区里让这么干的,并告诉我区公所在六里外的孔庄。
到了孔庄,区公所院里没人,只见一烧水的老头。老头悄悄告诉我,一听部队来人了,还挎着大枪,都躲起来了。
我说我不是来打仗的,再说当兵的能没枪吗?
老头说最近老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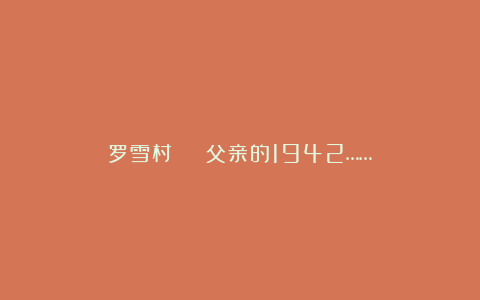
土改时,矛盾交错,军民关系不如抗战时期。我记得有一次正开干部会,外面突然“嘣”的一声枪响,一个团长在秫秸围起来的厕所里自杀了。原来,这个团长带着警卫员回家探亲,赶上家里人正挨斗,村上贫农团说他是给地主富农撑腰助威,到部队把他告了……那会儿闹土改没少死人。
再说那烧水老头,他叫我等着,就去叫人了。
不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干部。
我挺客气,问哪位是区委书记,一个说我是。
我说方周村段秀卿大娘曾经拿命掩护过一个小八路,她对革命有贡献,怎么现在土改改到她头上了?她老头子为了做掩护干过几年门箱柜生意,有没有俩钱我不知道,就是有也没什么错呀,最后还被日本人杀了;她唯一的儿子也在抗战时牺牲了。另外,她家那个四亩盐碱地收不了多少粮食,她是个小脚,种不了地,亲戚帮她代耕就成了剥削了?还给封门抄了家。我搞过土改,土改政策有一条,对贫下中农要保护,富农分一点东西出来也要保护。
那个区委书记跟我讲:地委书记说,土改就是头顶红点儿来。什么意思?就是顶着血来,就是要大刀阔斧干、玩儿着命干、豁出脑袋干,杀人也不算什么……
我说土改不是和敌人打仗,土改也要区别对待呀!
那个区委书记还真去了方周村。他们把房门都给打开了,封条也揭了,地也还给我大娘了。她高兴地——“哎呦,我儿呦!”
民国年间献县城门(铅笔)
民国年间献县一景(铅笔)
窝头成了粥
1958年春夏之间,我又回献县看我大娘,心想,这回别再出什么事。
那会儿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热闹劲儿还没过去。
一进屋,大娘一见我:“哎呦,保胜呀!我儿呦!你吃饭了吗?”我说:“吃饭是小事,我来看看你。”
“哎呀,你来该给你卧个鸡蛋,可大娘这儿什么都没有啦。”
怎么我大娘日子过成这样?
原来都吃公共食堂了。
中午,我去食堂给大娘打饭。大娘给了我一个罐,我说捡俩窝头就行了,拿罐干什么?
到了食堂,其实就是临时搭的一个简陋大棚子,里边好多人。有人跟厨师说,这是原来的老八路,得给人家多弄份客饭。
揭开蒸锅,嘿,看着是窝头,可厨师一手抻着笼屉布,一手拿铲子一铲,往罐里一搁,哎呀,连糠带什么的,哪有多少棒子面呀,全散成粥了,一个囫囵个也没有。
我让大娘跟我到北京去,我养活她。大娘不肯,说她老了,死也要死在这,听了怪难过。
我吃不下,也没忍心吃。
临走,我去找村干部,他们年轻,叫我“保胜叔”。我对他们说:“我大娘不容易,希望你们尽量照顾她,我忘不了你们的好处……”
人民公社化时期兴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宣传画
人民公社化时期大食堂一景
方周村大食堂旧址 2010年4月5日 雪村 摄
那天,村民张双耀老人指着村里一片空场,说当年大食堂就在那。“拿宰猪的大锅,把山药秧用铡刀铡成一截截的,煮熟,再剁烂,挤干铺在板子上,撒上点棒子面,再攥成团,最后上锅蒸。你问好吃吗,能好吃吗?
讨寿材
那次回去还有一件事,就是发现我大娘有心事,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说,她怕我惹事。
村上人告诉我,你大娘大跃进什么都没了,就剩口棺材,也叫寿材,是买来木材找人做的。没想,区里来人说卖她木材的那个人贪污,那棺材成了赃物给没收了。
我说这不对,不能因为卖木材的人犯事就没收她的东西。我问棺材给弄到哪去了,说在陌南村,还说村上好几个老人的棺材也给没收了。
陌南村离方周村不远,一个村干部陪我去了。
正巧县里干部正在那儿开现场会。我就跟他们讲了大娘掩护我的故事,说过去那么艰难都熬过来了,现在这把子年纪了,就剩这么一口棺材还给没收了。我来就是为她讨回那口棺材,好让她最后能入土为安。
他们让我先喝点水,说您别着急,我们了解一下。
过了会儿,县委书记来了,说老大娘对革命有贡献,不应该那样做,莽撞了,应该还给人家,还一个劲儿道歉,然后就让我去认是哪口棺材。
我一进院子,好家伙,满院子摞着几十口棺材。我说我也记不住是哪口,就让村干部回村里叫一个懂行的来。很快,村里来的人看上一口棺材,悄悄告诉我就说是这口,一看光棺材盖就老厚。我跟县委书记说就是这口。他说,那就拉走吧。村里还来了一辆小驴车,跟了几个小伙子,他们帮助搬到车上,拉回了方周村。
没想到,驴车还没进村,老远就看见村口站了黑压压一片人。等我们到了村口,“霹雳乓啷”放起了鞭炮,还有老乡在棺材上贴了一个红双喜字,说是“迎寿材”。
大娘一见我,抱着就哭。
我挺难过,说我应该养你的呀!哎呀,她说我这一辈子有这个就踏实了。
方周村段秀卿大娘家旧址 2010年4月5日 雪村 摄
那天,我来到方周村。迎面遇到一位大娘,一提“保胜”,大娘说:“俺叫他叔。”这位大娘叫张丛,74岁。跟她打听段秀卿大娘,她告诉我,她管段秀卿叫奶奶。段的老伴儿死得早,有个儿子叫柏穗儿,也死了,她是双烈属。
找到大娘家原来住的地方,房子是新翻建的,可惜门锁着。大娘家门前这条街,就是父亲讲的当年日本人把村民围起来的那条大街。
大娘来北京
1949年后,献县大娘来过北京,挎着一篮子鸡蛋,还有枣、花生、芝麻什么的。我们住东四七条。她住了几天。
东四七条旧家速写(铅笔)2025年6月
我给大娘捏了羊肉丸饺子,还在馅儿里滴了点儿香油。
我坚壁在方周村时14岁,她那会儿就像个小老太太,小脚儿,盘着卷儿,其实也就40多岁。
大娘走的那天,我去送她。
临走时,她对我说:我儿呦,别惦记我,我这把子年纪了,凑合着活就行了。以后你别再惹麻烦了,我就惦记你!说着说着就哭了。
后来,我给大娘寄过钱。
八几年,我搞战史,一次跟衡水军分区要了车去方周村。
我大娘已经没了。
我到村边看了看大娘的坟。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方周村。
(附记:妈妈记得是1952年冬天生我姐姐时献县大娘来的,她给我姐姐做了一件棉布斗篷。大娘人挺瘦小,穿一身黑棉袄,脚脖子缠一个绑腿,满脸的枯皱纹。“大娘特别善良,你爸可疼她了。”)
后记
父亲是中国一段革命历程的亲历者。
有历史学者说,中国革命史不缺宏大叙事,需要的是真实和细节。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个人组成历史,历史成就个人。
一个人的回忆留存越多,越利于还原历史真相,矫正历史谬误。
而那些经历过历史现场的幸存者,无论对自己,还是为后人,都不应该带走他们的记忆。
死亡不是终点,忘记才是。
庆幸在父亲生前,开始倾听、记录父亲的故事、细节甚至他的一声声叹息……
可惜,还是晚了……
(封面照片为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父亲(左四)归队并随部队转移到太行山里,这是他在易县小兰村与魏巍、钱丹辉、鲁易等战友们合影。刘峰 摄。)
(写于202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