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7日这天,湖南新化圳上的老屋门前,一场婚礼刚拉开帷幕,邻里街坊都挤满院子。谁也没想到,罗盛民和陈纯,竟然把一段故事走进了众目睽睽下。他们被议论,被拿捏,被怀疑,可这些陈纯都应下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很利落。有人忍不住问,这婚结得值吗?她倒笑了,不就为了个名字,谁傻?可她不傻,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说来还得倒回四年前。陈纯才十八,坐火车进长沙,是跟着爸妈。初来乍到啥都新鲜,却没几天就和罗亮香打了一堆照面。罗亮香是谁?著名烈士罗盛教的亲妹子。陈纯一听,愣住了,大英雄的后代!她总觉得自己守着一个理想要去参军,可家里不让,只得到头了把对英雄的那点敬仰,埋在心底不提。命运有点巧,学校军训那天,罗亮香问她敢不敢进部队营区,去见自己的哥哥罗盛民?她没犹豫,梳洗妥帖就等着行动。
两位女孩一身轻快地到了长沙军营门口,被哨兵拦住。罗亮香亮明身份,烈士家属,士兵敬了礼放行。罗盛民没马上到,陈纯在营房里左看右看。每个窗户、每道栅栏都像个小秘密,她问得细致,讲解的兵都快头大。那一刻她的好奇心就藏不住,自己都觉得有点冒傻气。后来终于见着罗盛民,和罗盛教的照片神似到让人窒息。俩人对上一眼,没讲半句套话,却生出点惺惺相惜的感觉。是偶像的光环,还是某种默契?连罗亮香都瞧出来端倪,不再拆穿。
那次见面后,陈纯总是念叨军营的事。她没机会穿军装,但有机会和罗盛民靠近。两人聊起来永远关不上话题。后来因为部队移防分隔两地,电话成了唯一联系。有说不完的家常,有些话带着小试探。其实军区禁外人打电话,罗亮香出主意,干脆冒充自己接线。陈纯紧张刺激地偷着乐,每次接通都激动坏了。结果两年下来,两人的情感像是荒原上被雨滴滋润,半点不枯。
陈纯毕业,家里想让她留长沙。她却偏要去新化当知青,她想离罗盛民更近,哪怕回绝了城市优渥的生活。罗盛民没撑住,坚持也就默认了。陈纯在新化落了户,头一件事不是安置,而是去罗家拜访。罗父罗迭开早已听说过她的事,对这未来儿媳妇相当满意。那个院子里,人来人往,烈士之家从不缺客人,妻子身体也不好。突然多了个陈纯,做事利落不对家里老人极有耐心,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罗迭开欣慰,看人太准。
而在这家里,罗盛教的荣誉被摆成传家宝。烈士故事说了许多年,到头来最难的不是讲光荣,而是有人把故事传下去。草稿、演讲、接待,陈纯都要管。婚还没结,这姑娘已经像儿媳妇一样进出了。这事搁现在看倒没啥,但那会村里村外,议论不少。说一句实话,陈纯没把这些闲话往心里去,她有她的主意。
后来罗盛民训练受伤,被部队送回家疗养。陈纯心里七上八下,赶去照顾。她等罗盛民慢慢好转,每天陪着他,屋檐下写字批卷,白天推着去晒太阳,偶尔会和罗父说说家常。一家人好像忽然有了主心骨。罗迭开那老爷子急脾气,看见儿子病好了,把两人拉进屋,就是一通说辞。罗盛民向来爽快,这次却憋了半天。到最后还是被父母压了一道线,“不成亲,别进家门。”这话搁谁也缓不过来。他终于单刀直入,向陈纯求婚,笨拙到让人哭笑不得。
结婚那天,院子里摆满了桌椅,罗迭开和妻子笑得合不拢嘴。陈纯嫁给了罗盛民,更像嫁给了这个家。两人头一年就生了儿子,日子也算热闹。不过天有不测风云。第二个孩子还没断奶,罗盛民病情复发,走路时常摔倒。看遍医院,南到广州,北到北京,所有能找的医生都见了一轮。陈纯哪怕身心俱疲,也一刻没松懈。罗盛民看到她瘦了一圈,才说“回家吧”。其实家里压力全到她身上了,老人,孩子,家务,教学,一样不能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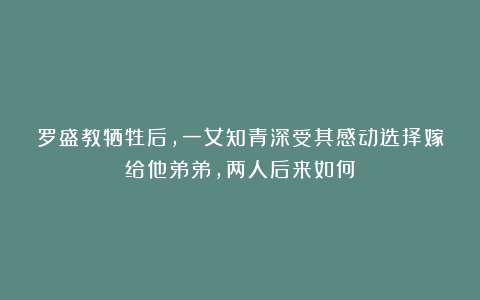
陈纯白天上课,晚上陪罗盛民批改作业。有人说她撑不住了?可每天黄昏,她自己咬咬牙就过去了。到1977年,罗盛民终究还是没挺住。陈纯一下沉到谷底,她没掉眼泪,只是继续撑着家。罗父母劝她改嫁,她摇头。老太太你这样太委屈。陈纯不答,她觉得家就在这。
有意思的是,罗迭开夫妇渐渐重新有了笑容。这家虽然失去了儿子,但人还在,总感觉天塌不下来。陈纯活得挺不容易,但她没表现出来。为了让老人走出丧子之痛,她提出修罗盛教纪念馆。想法一提出来,就真的被采纳了。馆子建成那天,老人头一次开怀大笑。谁能体会这背后的分量?
陈纯继续在学校任课。等到有一年,教材删掉罗盛教的文章。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却什么都改变不了。但她没放弃,在课堂上自己加内容,课余办讲座,三天两头就有学校、媒体请她过去,场场爆满。她觉得国际主义精神只要还有人讲,就不会消失。讲台上的她神采飞扬,不像日常的沉静。一讲起罗盛教救人事迹,细节历历在目。这群孩子也许不懂那种牺牲,但至少知道还有这样的人活过。
再过几年,罗父母也一个个走了。陈纯成了家中的接力棒,继续讲述罗盛教,还常接受媒体采访问答。等两个儿子都长大去外地工作,陈纯孤身一人守着故居。很多年轻人不太理解,为什么她非要留在这座老宅?有时想了又想,答案也模模糊糊。
其实很多看似波澜壮阔的故事,最后只归结于平淡的坚持。陈纯不是革命家,也没什么伟大理想。说到奉献,也许她不太认可。只是日复一日照料家人,照顾老人,把烈士的事迹一遍遍讲出去。她并没有渴望回报,也没觉得自己牺牲了什么。
以前她想进军营,后来自嘲自己其实和罗盛民走的是两条道。可这样不还是和罗家绑在了一起?有人问她后悔吗?她给不出标准答案。有人说幸福,有人说苦难,看你怎么选。可结果都在这新化小镇,没人给个标准。
到头来可能也没什么必须交代的。“伟大”这个词,有时候空空如也,也许更接地气吧?倘若非要说点什么,她活成了新中国身边那种再普通不过的人,不被谁定义,也没教条。
这些故事至今还会在村里巷子口被人提起。不必问后人怎么毕竟每个人眼里的现实,早就不是一回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