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作为绘画的基本语言,在中国画发展史上经历了从重彩到淡彩、由外显向内敛的深刻转型。南齐谢赫“六法”中“随类赋彩”一说,确立了早期中国画依物象类别施色的原则,体现了对自然色彩的尊重与规范。然而,自唐宋以降,山水画逐渐形成以水墨为主导的审美范式,“运墨而五色具”成为主流艺术追求。本文通过梳理山水画色彩观的历史演变,指出这一转变并非技术退化,而是士人审美理想与哲学观念演进的结果。
研究发现,“随类赋彩”在早期人物、花鸟画中仍具指导意义,但在山水画领域,随着“澄怀观道”“林泉之心”等理念的确立,色彩被视作可能干扰精神表达的外在形式,水墨则因其抽象性与书写性成为更契合文人理想的媒介。本文认为,中国山水画的色彩观经历了从“再现性用色”到“表现性弃色”的美学跃迁,其核心逻辑在于以“墨”代“彩”,实现“得意忘言”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中国山水画;色彩观;随类赋彩;水墨为上;谢赫;文人画
一、引言:色彩问题在中国画研究中的理论定位
色彩是视觉艺术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其运用方式直接关涉作品的风格、情调与文化意涵。在世界绘画传统中,中国画的色彩体系具有独特性:它既非完全写实,亦非纯粹抽象,而是在“类”“意”“理”等概念框架下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用色逻辑。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随类赋彩”,是中国画论中最早系统论述色彩原则的命题,标志着绘画色彩从实践经验向理论自觉的过渡。
“随类赋彩”字面意为“依据物象的类别赋予相应的色彩”,强调色彩使用的规范性与象征性。在早期中国画中,尤其是人物画与宗教壁画中,色彩具有明确的功能指向:服饰的等级、神佛的威仪、场景的氛围,皆通过特定色相传达。然而,这一原则在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水墨为核心的“黑白”体系。至宋代以后,“运墨而五色具”“墨分五彩”成为山水画的主导理念,色彩不再是画面的主角,甚至在某些文人画中被有意排斥。
这一从“赋彩”到“水墨”的转变,构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议题。本文聚焦于山水画领域,探讨“随类赋彩”如何从普遍原则演变为局部适用,而“水墨为上”又如何成为山水画的美学正统。通过分析历史语境、理论主张与代表作品,本文旨在揭示中国山水画色彩观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背后深层的文化与哲学动因。
二、“随类赋彩”的理论内涵与早期实践
谢赫“六法”中,“随类赋彩”位列第五,仅次于“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核心原则。这一排序本身即表明,色彩虽重要,但服务于更高层次的艺术目标。所谓“类”,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客观分类,而是基于文化认知与视觉经验的归纳。如树木为青绿,山石为赭褐,云天为浅蓝,宫殿为朱红,皆属“类”的范畴。
在南北朝至唐代的绘画实践中,“随类赋彩”体现为对色彩的程式化运用。敦煌莫高窟壁画是其典型代表:菩萨衣饰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背景山水以青绿勾填,色彩浓丽,对比鲜明。这种用色方式不仅具有装饰性,更承载宗教象征意义——金色象征佛光,蓝色象征清净,红色象征生命力。
在山水画初期,青绿山水占据主导地位。展子虔《游春图》以青绿设色,山体填染石青、石绿,水面施以金粉或淡蓝,树木点以深绿,房屋施以朱红,严格遵循“类”的规范。李思训、李昭道父子进一步发展青绿山水,创“金碧山水”一体,以金线勾勒山廓,富丽堂皇,体现盛唐气象。此时的山水画色彩,兼具写实与象征功能,是“随类赋彩”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随类赋彩”并非机械复制自然色彩。画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如增强对比、调整明度,以突出画面主题。因此,这一原则已蕴含主观能动性,为后世色彩观念的演变埋下伏笔。
三、水墨兴起的动因:技术、材料与审美转向
山水画从重彩向水墨的转变,始于中唐,成于五代两宋。这一过程受多重因素推动,包括绘画材料的普及、技法的成熟以及审美理想的转型。
首先,纸本与绢本的广泛使用为水墨表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相较于壁画或屏风画,卷轴画更便于文人案头赏玩,而水墨在纸绢上的晕染效果远胜矿物颜料。王维被传为“破墨山水”的开创者,其“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之论(见《历代名画记》),虽未必为其亲撰,却准确反映了当时文人阶层的审美倾向。
其次,笔墨技法的成熟使“墨”具备了替代“彩”的表现力。荆浩《笔法记》提出“墨法”四要:“焦、浓、重、淡、清”,虽列五种,实为墨色层次的系统归纳。通过干湿、浓淡、虚实的变化,水墨可表现山石的质感、空间的远近、光影的明暗。如董源《潇湘图》以淡墨晕染,山体浑厚,烟雨朦胧,虽无重彩,却意境全出。
更重要的是,审美理想的转型。唐代以后,士人阶层日益重视内心修养与精神自由,绘画不再仅是技艺展示,更是人格表达。色彩因其强烈的感官刺激与装饰性,被视为“俗”“艳”“匠气”的象征;而水墨则因其素朴、含蓄、内敛,契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文人品格。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所赞者,正是其“笔墨之外”的意境,而非色彩之华美。
四、“水墨为上”的理论建构与文人画的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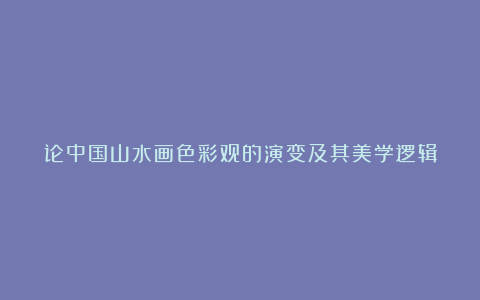
宋代是山水画水墨化的关键时期,理论家与画家共同推动了“水墨为上”观念的制度化。
郭熙《林泉高致》虽未明确贬抑色彩,但其对“远望取势”“近看取质”的强调,实则将重点置于笔墨结构而非色彩渲染。其画作《早春图》虽略施淡彩,但整体以水墨为主,山石纹理、树木枝干皆靠笔墨表现,色彩退居辅助地位。
至元代,文人画全面确立,“尚意轻形”“以书入画”成为主流。赵孟頫提倡“书画同源”,强调笔墨的书写性与抽象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通幅以水墨绘就,墨色由淡至浓反复皴擦点染,山体质感丰富,空间深远,全然不假色彩。倪瓒更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自况,其画作几无色彩,唯以枯笔淡墨勾勒疏林远岫,意境萧散孤高。
明代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将王维奉为南宗祖师,推崇“水墨渲淡”,贬斥“着色钩填”的北宗青绿。他在《画禅室随笔》中直言:“庭前柏树子,何须问西来意?水墨画者,正是此理。”此处将水墨画比作禅宗公案,强调其直指本心、不假外饰的特质。至此,“水墨为上”不仅是一种技法选择,更成为文人画的精神标识。
五、“随类赋彩”的转化与并存:色彩的隐退与回归
尽管水墨成为山水画主流,但“随类赋彩”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功能转化。
一方面,在宫廷绘画与职业画家中,青绿山水仍有延续。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以大青绿设色,山石遍施石青石绿,金线勾廓,气势恢宏,体现皇家审美。明代仇英亦擅青绿,其《桃源仙境图》色彩明丽,构图严谨,为职业画工典范。此类作品中,“随类赋彩”仍为基本法则,但更注重装饰性与理想化。
另一方面,在文人画内部,色彩被重新诠释。部分画家尝试将色彩融入水墨体系,如沈周晚年用色渐多,以淡赭、花青渲染山石,称“浅绛山水”;董其昌亦有设色之作,但色彩清淡,不掩笔墨。此时的“赋彩”已非“随类”,而是“随情”“随意”,服务于整体意境营造。
此外,花鸟画与人物画始终保留较强的色彩传统。恽寿平“没骨花卉”以彩色直接点染,不假墨线,是“随类赋彩”的创新发展。这表明,色彩观的演变在不同画科中并不同步,山水画的“水墨化”具有特殊性。
六、结语:色彩观演变的美学逻辑与文化意涵
中国山水画从“随类赋彩”到“水墨为上”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替代,而是士人文化、哲学观念与艺术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类赋彩”代表了早期绘画对物象的尊重与秩序的建立,其价值在于规范性与象征性;而“水墨为上”则标志着绘画从“形似”向“神似”、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向。水墨以其抽象性、流动性与书写性,成为表达“意”“境”“气”的理想媒介。
这一演变揭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逻辑: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再现世界的“真”,而在于传达心灵的“诚”。当色彩被视为可能遮蔽本质的“形”,而水墨因其“无色之色”更能接近“大道”,其主导地位便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