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核心文本,探讨艺术创作与审美过程中理性认知能力的构成与功能。通过对“模仿”(mīmēsis)概念的重新诠释,本文指出艺术模仿并非对现实的机械复制,而是一种基于普遍性与可能性的理性建构活动。在创作层面,诗人通过“普遍化”(katholou)原则,运用归纳与演绎推理,提炼经验现象中的必然性与或然性规律,实现对“可然律”与“必然律”的艺术呈现。在审美层面,观众的审美判断亦非纯粹情感反应,而是通过理性参与对情节结构、人物行为与命运转折的因果理解,从而获得“认知性愉悦”(katharsis的理性维度)。本文论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内在地将艺术活动纳入认知实践的范畴,揭示了美学经验中理性推理的结构性作用,为理解艺术的知识性价值提供了古典哲学基础。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诗学》;艺术模仿;理性认知;普遍性;净化;审美判断
一、引言:艺术与理性的传统张力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艺术与理性常被视为对立的两极:艺术归属于情感、直觉与感性经验,而理性则属于逻辑、科学与抽象思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诗人逐出城邦,正是基于艺术“远离真理”、“扰乱灵魂”的非理性特质。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不仅为诗辩护,更将诗置于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地位(《诗学》1451b)。这一判断的背后,蕴含着对艺术活动中理性认知功能的深刻洞察。
本文旨在通过对《诗学》文本的细致分析,揭示艺术创作与审美过程中理性认知能力的结构性参与。具体而言,本文将论证:第一,艺术模仿(mīmēsis)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活动,其核心在于对“普遍性”(katholou)的把握与呈现;第二,艺术创作依赖于诗人对可能性与必然性的逻辑推演,体现为一种“可然律”(eikos)与“必然律”(anankaios)的建构;第三,审美活动并非纯粹的情感体验,而是通过理解情节的因果结构实现认知深化,最终达成兼具情感净化与认知提升的“净化”(katharsis)效果。由此,本文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仅是一部关于悲剧艺术的理论著作,更是一部揭示美学经验中理性维度的哲学文本。
二、艺术模仿的本质:从再现到理性建构
在《诗学》开篇,亚里士多德即指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模仿”(1447a)。这一定义将“模仿”确立为艺术的根本属性。然而,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模仿”远非对现实的被动复制或表象再现。他明确指出:“诗人应是情节的模仿者,而不是现实的模仿者”(1460b),并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1451a)。
此处的关键在于“可然律”(to eikos)与“必然律”(to anankaios)的区分。前者指在特定情境下合乎情理、符合人物性格与社会常理的行动,后者则指逻辑上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并非历史事实的记录,而是基于其性格(高傲、执着)、情境(发现真相)与命运逻辑(神谕的必然性)所推演出的“应然”结局。这一结局虽未在现实中发生,却因其内在的因果合理性而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即“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
因此,艺术模仿的本质并非“再现”(representation),而是“建构”(construction)。诗人作为模仿者,其任务不是复制个别事件,而是通过理性筛选与重组,呈现事件背后的普遍结构。亚里士多德强调:“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物应既好又恰当……但首要的是,他们必须符合必然律或可然律”(1460b)。这表明,人物塑造与情节安排均需服从于一种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正是理性推理的产物。
进一步地,亚里士多德提出“普遍性”(katholou)作为诗学模仿的核心范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事物,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1451b)。这里的“普遍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抽象概念,而是指在特定类型人物、情境与动机下,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规律性关联。例如,一个“高傲者”在遭遇重大变故时,更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而非轻易屈服。这种普遍性不是通过统计归纳得出,而是通过理性对人性、命运与社会关系的深层洞察所建构的。
由此可见,艺术模仿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已从感性层面的“像似”(likeness)跃升为认知层面的“理解”(understanding)。诗人通过理性能力,将零散的经验材料组织为具有因果连贯性与普遍意义的整体,从而实现对世界深层结构的揭示。艺术创作因而成为一种“认知性实践”(cognitive practice),其成果不仅是美的对象,更是知识的载体。
三、创作中的理性机制:归纳、演绎与可能性推理
艺术创作中的理性参与,具体体现为诗人运用多种认知能力对材料进行加工与重构。亚里士多德虽未系统论述其“诗学逻辑”,但从《诗学》与《修辞学》《工具论》的关联中,可辨识出三种核心的理性机制:归纳、演绎与可能性推理。
首先,归纳(epagōgē)是诗人从具体经验中提炼普遍模式的基础方法。诗人观察现实中的事件、人物与行为,识别其中反复出现的因果模式,如“傲慢导致毁灭”“无知引发悲剧”等。这些模式构成其创作的“原型库”。例如,希腊悲剧中常见的“僭主命运”主题,即源于对政治权力与人性弱点关系的长期观察。通过归纳,诗人将个别经验上升为可应用于虚构情境的普遍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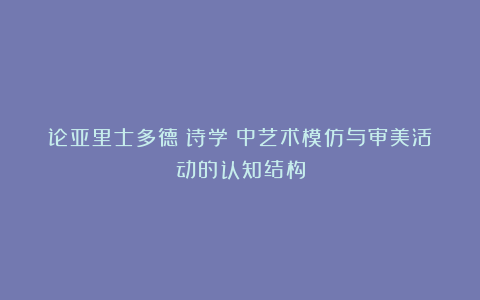
其次,演绎(syllogismos)在情节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应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有开端、中段和结尾”,且各部分之间应具有“必然的或可然的联系”(1450b)。这意味着情节的发展必须遵循逻辑推演。以《安提戈涅》为例:安提戈涅决定埋葬兄长(前提1),克瑞翁下令禁止埋葬(前提2),二者冲突不可避免(结论)。这一冲突的展开,正是基于人物身份、法律命令与道德义务之间的逻辑张力。诗人通过设定初始条件,推演出后续事件的必然发展,使情节具有内在一致性与不可逆性。
更为独特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可能性推理(eikos),即在缺乏确定性知识时,依据常理、性格与情境进行合理推断。他在《修辞学》中详细论述了“可然之事”的判断标准,如“同类人做同类事”“人在极端情绪下行为失常”等。在《诗学》中,这一推理方式被应用于虚构世界的建构。例如,为何俄狄浦斯未在童年即被杀?亚里士多德解释:“若诗人所写之事不合常理,但若其处理得当,仍可被接受”(1460a)。此处“处理得当”即指通过铺垫(如牧人怜悯、信使失误)使不可能之事变为“可然”之事。这种推理不依赖事实验证,而依赖于叙事内部的逻辑自洽与心理可信性。
此外,诗人还需具备对“突转”(peripeteia)与“发现”(anagnorisis)的理性设计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的悲剧情节应包含“由顺境转入逆境”的突转,并与“发现”相结合(1452a)。这种结构并非偶然安排,而是基于对因果链条的精密计算。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中,寻找凶手的调查(行动)导致身份真相的揭示(发现),进而引发命运的逆转(突转)。这一系列事件的衔接,依赖于诗人对信息控制、悬念设置与逻辑伏笔的理性规划。
因此,艺术创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绝非灵感闪现或情感宣泄的非理性过程,而是一种高度依赖理性认知能力的系统性建构。诗人如同哲学家或科学家,运用归纳提炼规律,通过演绎推演后果,借助可能性推理填补未知,最终创造出一个既合乎逻辑又富有普遍意义的“第二自然”。
四、审美活动中的理性参与:理解、判断与净化
艺术的理性维度不仅体现在创作端,同样贯穿于审美接受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观众对悲剧的体验并非被动的情感感染,而是一种主动的认知参与。审美愉悦(hedone)的根源,正在于对作品内在结构的理解与把握。
首先,审美判断依赖于对情节因果结构的理性理解。亚里士多德强调:“最完美的悲剧应是复杂型的,包含突转与发现,并以苦难结局”(1453a)。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断对人物行为的动机、事件发展的逻辑进行推断与验证。当“发现”发生时(如俄狄浦斯意识到自己杀父娶母),观众不仅感受到震惊,更体验到一种“认知的顿悟”——此前分散的线索突然形成完整图景。这种“啊,原来如此!”的领悟感,正是理性理解的直接产物。
其次,审美活动包含对人物行为的道德与逻辑判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人物应是“比一般人好,但并非完美”,其不幸源于“判断错误”(hamartia),而非道德败坏(1453a)。观众在同情其遭遇的同时,也需理性评估其选择的合理性。例如,是否应违背国王命令埋葬亲人?在神律与人法冲突中如何抉择?这些问题促使观众超越情感共鸣,进入伦理与实践理性的反思领域。审美因此成为一种“道德想象力”的训练。
尤为关键的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净化”(katharsis)概念,传统上被解释为情感的宣泄或净化。然而,结合其整体哲学体系,katharsis更应理解为一种情感与理性的协同净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是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状态。悲剧通过激发恐惧与怜悯,使观众在安全距离内体验极端情感,同时通过理解其成因(如傲慢、无知、命运错位),学会以理性调节情感。这种“通过理解实现情感升华”的过程,正是katharsis的认知维度。
此外,悲剧还能拓展观众的实践智慧(phronesis)。通过观察他人在复杂情境中的抉择与后果,观众间接获得应对人生困境的经验。亚里士多德认为,诗“告诉我们事物如何因必然性或可然性而相互关联”(1451b),这种对因果关系的认知,有助于提升个体在现实中的判断力。因此,审美不仅是享受,更是一种“认知训练”。
五、结论:艺术作为认知实践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洞见: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本质上是理性认知能力的体现与延伸。艺术模仿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归纳、演绎与可能性推理,建构一个揭示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意义世界。诗人作为“普遍性的模仿者”,其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式的探究。而审美活动也非纯粹的情感沉浸,而是通过理解情节结构、评估人物行为、体验因果逻辑,实现情感净化与认知提升的双重目标。
在这一框架下,艺术不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其补充与深化。它以感性形式承载理性内容,以虚构叙事揭示现实规律,以情感体验促进道德认知。亚里士多德由此打破了艺术与知识的传统界限,为美学赋予了认知价值。这一思想对后世启示深远:无论是文学、戏剧还是现代影视艺术,其伟大作品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正在于它们不仅打动人心,更启迪心智——在感性的帷幕之后,始终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文章作者:芦熙霖
声明:本人账号下的所有文章(包括图文、论文、音视频等)自发布之日72小时后可任意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如需约稿,可联系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