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成群,1978年生,现为北京邮电大学长聘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北邮)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少数民族预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教材1部,学术专著5部,散文集2部,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曾获北京邮电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本科教学特别贡献奖、移动奖教金等奖项。
元好问禅学思想及“援禅入诗”考论
内容提要:根据元好问的记载,可以梳理出多条关涉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的谱系,丰富了学界对金元时代北方禅宗传承的认知。元好问禅学思想富于特色,他倡导“合”,追求圆融无碍的境界;同时提出“不知有文字”“学至于无学”等颇具机锋的看法。在具体创作中,元好问尝试“援禅入诗”,追求一种圆熟空寂的禅学特征。但总体来看,元好问“援禅入诗”的成效并不显著,其儒学本位意识可能是影响发挥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元好问;禅学思想;援禅入诗;儒学本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界有关元好问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诗文层面,逐步走向了更为深广的领域。其中讨论元好问与佛道二教关系的文字并不乏见。元好问与道教的关系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故不赘言;至于元好问与佛教的关系,已有多篇论文从不同方面进行过探索。[1]然而具体讨论元好问禅学思想的文字则较为欠缺,本文尝试补足这一缺憾,以俟方家指正。
1
元好问的禅学因缘
元好问自幼熟读诗书,泛览佛老。在禅宗方面,除《坛经》外,他对《祖堂集》《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碧岩录》等禅宗灯录、语录著作也颇为熟悉,并且常将上述禅宗典籍中的典故运用于诗文创作中。如“是镜不名砖”[2]是撷取《祖堂集》中南岳怀让与马祖道一的一段公案。“盖头茅一把,绕腹篾三条”[3]是撷取了《坛经》中六祖慧能评价菏泽神会禅的话以及《五灯会元》中马祖道一对药山惟俨布下的机锋。又如“儿女团 庞行婆”[4]一句,关涉《五灯会元》中的庞蕴居士的一个偈子。“寄谢诸方五味禅”[5]一句,关涉《古尊宿语录》中一段公案。“百篇吾不惜眉毛”[6]一句,关涉《碧岩录》中的一段公案。“铁牛力负黄河岸,生被曹山挽鼻回”[7],上句关涉《碧岩录》中风穴延沼之机法,下句关涉《古尊宿语录》的一段公案。
《祖堂集》《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碧岩录》等禅宗灯录、语录,其实是“传灯”与“语录”的结合,是僧传与僧传叠加所形成的世系,包括各传主的师承、交游、著述和语录,综合起来就是一部禅宗传承的谱系。通过元好问诗文所采用的诸多典故来看,谓其谙熟禅史自不为过。
元好问生父元德明曾“居东山福田精舍,首尾十五年”[8],深受佛教影响。其存世不多的诗歌中与佛教相关者有4首,元好问对佛学的最初认知可能源自其父。金末崇佛,士大夫普遍喜欢与僧人相接,如赵秉文喜佛学,尝曰:“吾生前是一僧”;李纯甫师从万松行秀,也曾说:“吾生前一僧,岂敢不学佛?”[9]元好问“我本宝应僧”[10]的意识或渊源于此。此外,关于金代儒学,后世向有“苏学盛于北”[11]的论调,这自然是助益“三教合一”与禅诗融通风气的。元好问赖以成长的文化土壤,当是成就其深谙禅史的原因之一。
除了赵秉文和李纯甫这些士大夫外,元好问也接触了不少僧侣。据杨国勇统计,元好问著作所涉及佛教僧尼有125人,寺院庵阁有154座。[12]在此基础上,贾晓峰又统计出元好问涉及佛教的“诗有46题、76首,文有15篇”[13]。降大任对元好问所交往的僧道颇有研究,其中详细考证过的僧人凡26人。[14]这26人多数系禅宗僧人。元好问深谙禅史,除了博览群书外,与禅宗僧人的交游砥砺也不无关联。降大任考证虽精,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未明确区分26人的禅宗派别。为了更好地梳理元好问的禅宗思想,实有必要对其交往的僧人作禅宗派别层面的细分。在所交往的禅僧中,元好问与性英最为亲密,按其描述是“兄弟论交四十年”[15]。性英曾任少林寺住持,按照元好问《少林药局记》的说法,性英是接替东林志隆为少林寺住持的。[16]东林志隆是万松行秀弟子,王树林[17]和叶宪允[18]等学者认为性英也是出于万松行秀之门。现有资料虽无法直接支持这一结论,不过可以推断的是,性英即便不是出自万松行秀亲炙,也应与万松行秀一系具有紧密的关系。
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 年版
在元好问的记载中,开创少林药局的人物是性英前任住持东林志隆,所谓“故少林之有药局,自东林隆始”[19]。元好问曾提及东林志隆,如《皓和尚颂序》云:“虽东林隆高出十百辈,而皓于是中尤为上首。”[20]这里的“皓”是万松行秀另外一位弟子皓和尚。从《皓和尚颂序》所传递的信息来看,元好问与皓和尚是旧相识。另外,与元好问有过真实交集的洪倪,也是万松行秀的弟子,如其《寿圣禅寺功德记》记载洪倪生平曰:“闻万松道价,裹粮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见,即以座元处之”[21]。万松行秀属于曹洞宗的北传体系,其上可追溯到雪岩满、王山体、大明宝,再往上则可追溯到一个关键人物青州希辩。青州希辩上承投子义青、芙蓉道楷、鹿门自觉一系,因随辽军至燕京,驻潭柘寺、仰山栖隐寺,其道遂北。元好问曾多次论及青州希辩,如云:“每及青州以来诸禅老,皆谓万松老人号称辨材无碍,当世无有能当之者。”[22]又如其曰:“故百年以来,诸禅刹之有药局,自青州始。”[23]综上可知,元好问对曹洞宗北方的传承是十分熟稔的。
元好问《答聪上人书》云:“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24]令其“自幸”的聪上人就是刘秉忠。刘秉忠有《读遗山诗十首》《再读遗山诗》《细读遗山诗》等诗,对元好问极为推崇,如赞曰:“屈宋前头更有人”[25]。刘秉忠系海云印简再传弟子。海云印简为临济宗宗师,贵由曾颁诏书命其统领佛教,其影响力一度达到空前状态。现存文献中虽不见元好问与海云印简交往的记载,但其与刘秉忠的交集表明,元好问对这一临济宗体系并不陌生。海云印简—刘秉忠这一临济宗体系多为世人所知,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存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有多支临济宗的传承线索,如元好问记载曰:
慈明与琅琊觉皆法兄弟,共扶临济一枝。慈明而下十余世,得玄冥 禅师;琅琊而下亦十余世,得虚明亨禅师。玄冥风岸孤峻,无所许可,宁绝嗣而不传;虚明急于接纳,故子孙满天下,又皆称其家,加慈云海、清凉相、罗汉汴与法王昭公,皆是也。[26]
“清凉相”就是弘相禅师。弘相禅师曾就学于虚明亨禅师,坐道场于郑州大觉寺、沂州普照寺、嵩山少林寺,最后住持清凉寺,有弟子曰显、曰静、曰隽。弘相禅师擅长诗文,元好问评价云:“西溪道行清实,临济一枝以北向上诸人,至推其余以接物,则又以为大夫士之贤而文者也。”[27]“西溪”即弘相禅师,元好问有《寄西溪相禅师》可参证。[28]
罗汉汴”即福汴禅师。福汴禅师最初落发于告山赟禅师,后有机缘师事虚明亨禅师,得以接续临济宗体系。正如元好问记载曰:“汴南迁后,嗣法虚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后蒙印可,于临济一枝,亭亭直上,不为震风凌雨之所摧偃。”[29]虚明亨禅师曾坐道场于嵩山少林寺、法王寺。引文提及的“清凉相、罗汉汴与法王昭公”都是他在嵩山时吸纳的门人弟子,其中“法王昭公”就是法王寺的昭禅师。按照元好问记载,昭禅师曾为虚明亨禅师建塔,又以李纯甫所作墓志铭求书于赵秉文,并得其应允。可见虚明亨、昭禅师师徒与当时士大夫交契非同一般。
除了曹洞宗和临济宗外,元好问笔下还出现了较为没落的云门宗的踪影。在《徽公塔铭》一文中,元好问记载了澄徽禅师的生平履历,其人经过一番巡礼后,最后入见以“风岸孤竣”而著称的虚明寿和尚,成为首座弟子。在立僧佛事上,虚明寿和尚说法曰:“若谓见齐于师,宁不辜负徽首座!何止辜负徽首座,云门一枝,扫地而尽!”[30]可见虚明寿和尚与澄徽禅师师徒二人所传为云门宗,引文中虚明寿和尚的话语的确也具备云门宗截断众流的那种气魄。
在相关记载较为贫乏的金元时代,元好问在禅宗史上的一大贡献即记载了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等多支体系与多位人物,极大丰富了后世学者对当时北方禅宗谱系的认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元好问所勾勒出的禅宗图景,也成为了理解他禅学思想的有效支撑。
2
元好问的禅学思想
通观元好问涉及禅宗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对禅学事件与禅宗人物采取的策略多为“述”,即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叙述人物的生平经历,极尽铺陈之能事,笔力雄健,文采斐然。作为深谙禅学的学者,他并不愿意对禅学作出具体的议论,也不愿意另辟新说,甚至不愿意展示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元好问曾说:“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师当为予说,而予不当为师说。’”[31]其又说:“若佛法,则师当为予说,而予不当为师说”[32];“其语言三昧,盖不必置论。”[33]一般来说,曹洞宗倡导默照禅,临济宗倡导看话禅,而云门宗有函盖截断之风,均是个性鲜明,又各有千秋。描述这些不同宗派时,极容易突出其风格特点。然而元好问并未就此发表明确见解,仿佛是有意避开一样。高桥幸吉也发现过这一特点,他指出:“元好问评价佛教徒时,似乎没有在佛教思想或其教义角度来评价”[34],其中意味,实在值得深入挖掘。
元好问深受赵秉文、杨云翼等金末儒者影响,他把赵秉文视作“道统中绝,力任权御”[35]的人物。其“主盟吾道”并引领群公的情状,正与唐宋两场古文运动相似,就如同“唐昌黎公、宋欧阳公身为大儒,系道之废兴,亦有皇甫、张、曾、苏诸人辅翼之”[36]一般。也就是说,元好问思想中是有明显的儒家本位意识的。虽然金代“三教合一”文化氛围对元好问影响不少,但他在金元之际二教勃兴的大语境中对佛道产生了明显的排斥心理。如其曾愤然云:“道,则异术也;教,则异习也。梯空接虚,入神出天,与吾姬、孔氏至列为三家。”[37]又有诗曰:“何年胜果寺,西与姬公邻。塔庙恣汝为,岂合鲁城 。鲁人惑异教,吾道宜湮沦……”[38]
基于儒家本位意识,元好问在涉及佛道二教的文字中往往带有一种针对性的批评。道教暂不赘言,至于佛教,如“世之桑门以割爱为本,至视其骨肉如路人,今师孝其亲者乃如此!然则学佛者亦何必皆弃父而逃之,然后为出家耶?”[39]有时候还有一些嘲讽的意味,如“其说曰:’以力言者,佛为大,国次之。’吁,可谅哉!”[40]在元好问的涉禅文献里,往往带有一种警惕越位的意识,如曰:“佛之徒方以禅定为习,于世间法皆以为害道而不敢为。间有言医者,特儒者之谈禅尔。”[41]他常常不忘在比较中提炼儒家的优点,如云:“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跻之仁寿之域,又何直庄严佛土一端而已哉!”[42]更明显的是,元好问常为儒家处于弱势地位而感觉惋惜和不平,如云:“使吾圣人之门,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亩之宫,亦何遽有鞠为园蔬之叹乎?”[43]可能是由于儒家本位意识,深谙禅史的元好问往往于禅学述而不评。
然而金末儒学又是非常复杂的,儒士们虽然通过儒学重估思潮刻意地强化儒学认同感,但又一时难以割舍对佛道二教的喜好。如赵秉文晚年削去佛老二家刊为《滏水集》,但削去的文稿却编为《闲闲外集》,交给少林寺性英,使其刊布之。此即“既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44]之谓。元好问与之相仿,他倒不是另刊了外集,而是以诗论的方式表达了禅学思想,这可能是一种更为高明且隐蔽的阐释策略。在《杜诗学引》一文中,元好问写道:
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而名之者矣。[45]
《麻杜张诸人诗评》一文评论麻革、杜仁杰、张澄的诗歌曰:
仲梁诗如偏将军将突骑,利在速战,屈于迟久,故不大胜则大败。仲经守有余而攻战不足,故胜负略相当。信之如六国合从,利在同盟,而敝于不相统一,有连鸡不俱栖之势。虽人自为战,而号令无适从,故胜负未可知。光弼代子仪军,旧营垒也,旧旗帜也,光弼一号令而精彩皆变。第恐三子者不为光弼耳。[46]
元好问在此强调了一个关键的“合”字,譬如江湖合而为海的比喻、药材合而为剂的比喻、六国合从的比喻,原是各自分别的事物通过“合”互相涉入,彼此贯通。虽然元好问并没有提及禅字,但他“互用”“相入”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禅宗史上有名的“回互”说。“回互”说肇自石头希迁,却为曹洞宗所发扬,并成为曹洞宗的核心思想。[47]在曹洞宗看来,世间万物存在“回互”与“不回互”两方面的情状。其中“回互”追求万事万物相即相入、大小互含的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杜诗学引》《麻杜张诸人诗评》等所阐发的诗学理念很有可能受到了曹洞宗的启发。有学者指出:“中国禅宗各派,特别是石头法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都深受《华严经》和华严宗思想的影响”[48]。在金代,曹洞宗颇具华严特色,如万松行秀就“对《华严经》及华严教学,深具关心,并具有某一水准的知识”[49]。万松行秀弟子李纯甫认为:“至读《华严经》无佛无儒,无大无小,能儒,能佛,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50]总之,“金朝禅宗思想也受到唐辽华严宗等义学思想的重要影响,即在思想主旨上主张禅教’圆融’”[51]。有了华严思想的加持,曹洞宗“回互”说明显具备对圆融境界的追求。所谓“相统一”,所谓“一号令”,都是讲究互相融会、乃至同归于一的效果。
查慎行著,范道济点校,《查慎行全集》,中华书局,2017 年版
除了曹洞宗,元好问与临济宗禅师也多有接触,他也常常借助临济宗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对诗学的认知。如“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52]如“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53]又如“所可言者,其天资高,笔墨工夫到,学至于无学耳。”[54]“无学”一词虽见诸于《法华经》《俱舍论》等佛教经典,但形成“学至于无学”的搭配,却是出自临济宗杨岐派圜悟克勤所编写的《碧岩录》,该书云:“学至无学,谓之绝学”[55]。
禅宗自慧能起,皆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宗旨,为的是打破人们对文字乃至对一切表象的执着。然而《碧岩录》虽谓“学至无学”,却是根据雪窦的“颂古百则”加以注释和评唱而成,体现出明显的“学”的特点,从而成为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捩点。《碧岩录》不离文字的特点与“学至无学”的精神是相悖的,不过没有文字的记载,“学”又何以传承?无学也好,不立文字也好,大抵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状态。元好问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虽然崇尚“学至于无学”,但也指出:“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56]也就是说,虽然不一定能做到“无学”和不立“文字”,但是面对“学”与“文字”必须秉持一种超拔的意识。
元好问也曾谈及文字禅,如其曰:
予独记屏山语云:“东坡、山谷俱尝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为祖师禅,东坡为文字禅。且道皓和尚百则语,附之东坡欤?山谷欤?”余亦尝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皓和尚,添花锦欤?切玉刀欤?余皆不能知。[57]
所谓祖师禅,就是慧能禅法,即瞬间使人开悟,见性而成佛。所谓文字禅,即转捩话头,也称作绕路说禅,主旨是用艺术语言避开语言和逻辑。不立文字当然是第一峰头,然而“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语惊流俗”[58]是可行的,完全不立文字终究难于实现,于是绕路说禅的文字禅就成为可以操作的办法。元好问当然懂得文字禅的无奈,因而也并不轻易对其加以否定。
然而文字禅毕竟落入第二峰头,也有不少人反对文字禅。如临济宗大慧宗杲就将《碧岩录》刻版全部毁掉,此举可视为对文字禅的反拨。元好问也是一样,在文字禅盛行的时代,却特别期待达到“不知有文字”的效果。元好问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不知有文字”,如《陶然集诗序》[59]云:“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新轩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其又云:“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60]《木庵诗集序》云:“境用人胜,思与神遇,故能游戏翰墨道场,而透脱丛林窠臼,于蔬笋中别为无味之味。皎然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盖有望焉。”[61]而《杨叔能小亨集引》云:“优柔餍饫,使人涵泳于先王之泽,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62]“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出自皎然《诗式》,是其以禅喻诗的重要表述。在元好问笔下,“不知有文字”是“学至于无学”的另一种表达,即内蕴达到极致后不再依托于任何形式。
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 年版
“不知有文字”或“学至于无学”乃是来自禅宗的观念,这些观念的产生大概与元好问接触嵩山一带擅长诗歌的禅僧有关。兴定年间和元光年间,元好问居嵩山一带,与性英、弘相、福汴等曹洞宗、临济宗禅僧交游。此前,元好问居住在宜阳三乡,曾写下著名的《论诗三十首》。在组诗中,元好问集中阐发了他的“天然观”。如“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63]此时,元好问的主旨是“重自然而不重刻琢”[64],这一思路很明显是源出于陶渊明、李白等诗人的主张。如果说《论诗三十首》的“天然观”,其核心观念是“真”的话,“不知有文字”或“学至于无学”的核心观念就是“无”。元好问接触禅宗后,其文学观念实现了一个从“真”到“无”的跃迁。
3
元好问“援禅入诗”的尝试
如前所述,元好问居嵩山一带,多与禅僧交游。无论是属于曹洞宗,还是属于临济宗,嵩山一带的禅僧都是诗僧无疑。如性英的诗才就令元好问十分叹服,他评价性英曰:“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65]他还记载文坛巨擘赵秉文、杨云翼等人对性英“相与推激,至以不见颜色为恨”[66]。此话并非夸张,因在赵秉文的文集中可见《同英粹中赋梅》。[67]性英还担负了刊刻赵秉文《闲闲外集》的重任,可见交契非同一般。
元好问《赠汴禅师》一诗写道:“赵子曾相问,冯公每见招。”这里的“赵子”,施国祁认为是赵元[68],而狄宝心则认为是赵秉文。[69]“冯公”即冯璧,福汴诗才十分可观,冯璧有诗曰:“诗笔如君僧有几,文章愧我老无堪。”[70]推崇之情可见一斑。与性英、福汴等相似,弘相也是一位诗僧,元好问将其比作唐代诗人方干,曰:“清凉诗最圆,往往似方干。”[71]在《清凉相禅师墓铭》中,元好问又评价曰:“诗则清而圆,有晚唐以来风调,其深入理窟,七纵八横,则又于近世诗僧不多见也。”[72]除了性英、福汴、弘相之外,元好问接触过的禅僧还有子京禅师、僧源、昭禅师、鉴禅师、俊书记等,这些禅僧也无一例外都是诗僧。元好问赠子京禅师诗曰:“嵩少诗僧几人在,因君回望一凄然。”[73]其又评价僧源曰:“济甫诗最苦,寸晷不识闲。”[74]又有诗赠嵩山侍者俊书记曰:“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75]其中最后一首最为脍炙人口。
元好问对禅与诗的关系认识十分到位,他赠俊书记的诗歌又载入《皓和尚颂序》一文中,可见是平生得意之作。“添花”者,不添亦无所谓,“切玉”者,无其刀必不可行,意思是禅对诗的意义要明显大于诗对禅的意义。南宗禅讲的“顿悟”,其实是追求一种否弃逻辑的直觉体会;诗歌讲的意蕴,乃是追求一种语言背后的美的呈现。为了否弃逻辑,禅宗转捩话头的办法很多,可以是变易和扭曲的语言,也可以是充满机智和巧喻的语言,当然诗歌更好,但未必非得是诗,用“添花锦”形容自然是恰到好处。诗歌所追求的言外之旨,其终极理想就是禅宗的“不立文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用“切玉刀”来比喻也是十分传神。
元好问在观念上尊崇融会诗禅,对此学界曾有过一些简略论述。[76]在创作层面却少有学者讨论其如何做到融会诗禅,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讨论的余地。元好问“援禅入诗”,首先表现在:他在诗歌创作中,常常以超世拔俗的眼光,将世界万物打回妙有真空,同时也使自己明心见性,从而放弃一切执念。如《过邯郸四绝》其四曰:“死去生来不一身,定知谁妄复谁真。邯郸今日题诗客,犹是黄粱梦里人。”[77]又如《杂著九首》其八与其九曰:“昨日东周今日秦,咸阳烟火洛阳尘。百年蚁穴蜂衙里,笑煞昆仑顶上人。”“半纸虚名百战身,转头高冢卧麒麟。山间曾见渔樵说,辛苦凌烟阁上人。”[78]这几首诗其实都是说功名利禄乃至世间的一切皆为幻象,本来就不具备什么真实的本性,因而无须执着。明白了这一切,心态自然便可放平了。
自慧能以来,禅宗的重要旨归就是放下执念,很多诗人“援禅入诗”,以文学的手法做出了实践,譬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次韵法芝举旧诗》《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等诗词都是在探讨如何放下执念的问题,历来为人所称道。元好问向来注重学习苏轼,正所谓“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79]其自然也会取法苏轼放下执念的诗歌。《愚轩为赵宜之赋》一诗曰:“心生心化谁抟控,举世伥伥皆大梦。百年只办作朝三,争识群狙先汝弄。”[80]意思是说执着于世间假象,就像《庄子》中那群被“朝三暮四”欺骗的猴子一样愚蠢。此篇立意与苏轼极像,难怪查慎行评论说:“全篇俱学苏,用事亦恰合。”[81]
然而元好问对苏轼也有微词,他认为苏轼诗歌“其怨则不能自掩也”[82],既然“怨”不能自掩,则必有执念无法释怀。苏轼家族与蜀地云门宗高僧圆通居讷、宝月惟简交契深厚,其本人与云门宗高僧佛印、道潜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因此苏轼诗文禅风颇有云门宗截断众流的鲜明个性。苏轼一生坎坷,其便巧新奇的机锋中难免会流露出些许不平之气,只是接近生命的终点,才逐渐变得圆融无碍起来。元好问十分认同黄庭坚的看法,即《陶然集诗序》之“东坡海南以后”,才终至“不烦绳削而自合”那样圆熟的艺术境界。
如前所述,或许是受“辨材无碍”的曹洞宗影响,元好问特别提倡一个“合”字,其本质是追求一种圆融无碍的境界。这种追求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一种圆熟格调。元好问十分警惕诗歌创作中“有碍”的因素,其用于自警的二十九条戒律就是圆熟格调的细化,其内容如下:
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狡讦,无媕阿,无傅会,无笼络,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策》,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83]
如果上述条款均能落实的话,那确实是圆熟的艺术境界了。不过元好问的诗歌里还是存在怨气的,甚至可能比苏轼还要更重一些,“半废晨昏愧此身”[84]、“可怜出处两蹉跎”[85]、“空将衰泪洒吴天”[86]之类的句子比比皆是。不过也有一些作品戡破假有,从而使法我融会于一体,臻于圆融无碍之境。如《鹧鸪天》其二十有题注:“效东坡体”,此词写得十分洒脱,颇得东坡风韵,其文曰:“煮酒青梅入座新,姚家池馆宋家邻。楼中燕子能留客,陌上杨花也笑人。梁苑月,洛阳尘,少年难得是闲身。殷勤昨夜三更雨,乘醉东城一日春。”[87]《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一词更是浸透了沧桑,圆熟老苍,其文曰:“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唯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88]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
在“合”这一层面,元好问还有一位更为欣赏的对象——晚年的白居易。元好问早年称赞其曰:“当年香山老,挂冠遂忘返。高情留诗轴,清话入禅版。”[89]晚年则称赞其曰:“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90]可见元好问对白居易的推崇是贯彻其一生的。白居易与马祖道一门下惟宽、智常、如满等禅师过从甚密,深受洪州禅“平常心是道”思想的影响,兼以晚年生活优渥,所以其禅诗如《香山寺二绝》《闲咏》《在家出家》《寄韬光禅师》等都展现出闲适淡然的风格特征。在元好问看来,白乐天香山以后,也能做到“不烦绳削而自合”,同样是圆熟的艺术境界。
白居易《读禅经》曰:“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91]意思是破除对“相”“言”的执着,这与元好问倡导“不知有文字”和“学至于无学”如出一辙。在具体创作中,元好问也常常表达对“无”的体认,如《真味斋》一诗曰:“粗饭寒齑老此身,高人那计甑生尘。味无味处君知否,道著琴书已失真。”[92]又如《刘氏明远庵三首》其二曰:“世上无物碍虚空,宴坐经行一体同。老眼不应随境转,江山元只在胸中。”[93]“不知有文字”和“学至于无学”是对文字等形式的否弃,在具体创作中,元好问也一再表达同样的意思,如《周才卿拙庵》云:“诗笔看君有悟门,春风过水略无痕。庵名未便遮藏得,拙里元来大巧存。”[94]又如《刘君用可庵二首》曰:“末节繁文费讨论,经生规矩是专门。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着脚绳桥已足忧,邯郸匍匐更堪羞。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95]
无论是白居易的《读禅经》,还是元好问的几首作品,都可以追溯到慧能“本来无一物”[96]的表述。在佛学范畴上,“无”不等于“空”,但又常与“空”混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慧能“本来无一物”的表述,就将般若学的“空”观推向了极致。受其影响,唐宋文学家也热衷营造空寂的美学氛围,如白居易诗曰:“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97]四望不见人,烟江澹秋色。”“[98]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99]
在营造空寂这一点上,元好问也不例外,如《洛阳高少府瀍阳后庵五首》其一曰:“溪上弄明月,风露发新警。心空无一尘,万竹扫秋影。”[100]再如《萧寺僧归横轴》一诗曰:“山空秋草寒,露暗光已夕。悠悠松门月,静照禅客入。遥知夜堂深,疏钟动幽寂。”[101]在元好问的文集中,以“空”为字眼的诗歌不在少数。
按照《陶然集诗序》一文的说法,元好问十分崇尚一种“万虑洗然,深入空寂”的境界,联系该序上下文可知,此表述乃是因禅宗所引发。在元好问的此类诗歌中,“空”是最常见的字眼,此外,“寂”“静”“深”“清”“幽”“独”等也都成为元好问此类诗歌中的审美偏好。如《少林》一诗曰:“云林入清深,禅房坐萧爽。澄泉洁余习,高鸟唤长往。我无玄豹姿,漫有紫霞想。回首山中云,灵芝日应长。”[102]又如《少林雨中》一诗曰:“西堂三日雨,气节变萧森。偃卧复欹卧,长吟时短吟。钟鱼四山静,松竹一灯深。重羡禅栖客,都无尘虑侵。”[103]再如《阳泉栖云道院》曰:“方外复方外,翛然心迹清。开窗纳山影,推枕得溪声。川路远谁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锦峥嵘。”[104]元好问早年就写有富于禅意的诗歌,如:“山势巍峨翠竹围,楼台金碧影相辉。老僧托钵归来后,犹对斜阳补衲衣。”[105]晚年也写有富于禅意的诗歌,如:“廓达灵光见太初,眼中无复野狐书。诗家关捩知多少,一钥拈来便有余。”[106]然而总体而言,元好问禅诗的写作量并不为多。尤其是其晚年,并没有出现“乐天香山以后”那样一个集中的写作期。当然,元好问禅诗的质量与知名度也远远不如苏轼与白居易。究其原委,可能是因为元好问在方法论上更注重取法杜甫,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援禅入诗”。元好问编纂过《杜诗学》,给予杜诗无以伦比的评价。[107]元好问虽然在《陶然集诗序》中盛赞“乐天香山以后”和“东坡海南以后”,但在这两者之前,还有一个“子美夔州以后”,由此可见杜甫诗在其心中的地位。
元好问特别提倡“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108]的“以诚为本”说,并用这一学说指导了他晚年的诗文创作。[109]“以诚为本”说与取法杜甫并不冲突,可以说都是其儒学本位意识的体现。不过,儒学本位意识与“援禅入诗”的尝试就有抵牾之处了。元好问未能使“援禅入诗”发挥出更好的文学效果,其思想中的抵牾应该是重点考虑的因素。
结语
元好问作为文学巨擘,其禅学思想与文学实践展现了金元之际独特的文化风貌。他深谙禅宗典籍,与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僧人多有交游,通过诗文保存了北方禅宗谱系的珍贵史料。在禅学思想上,他追求“合”,倡导圆融无碍的境界;提出“不知有文字”“学至于无学”等观点,体现了对禅宗“不立文字”精神的深刻领悟。这些思想受到曹洞宗“回互”说以及临济宗“无”学理念的影响,反映出他对禅宗各派思想的兼收并蓄。
在文学创作层面,元好问尝试“援禅入诗”,通过禅诗表达对世间幻象的超越与对空寂之美的追求。其禅诗以超脱之笔描绘人生虚妄,风格圆熟空灵,展现出与苏轼、白居易相似的禅学境界。然而,他的儒学本位意识又非常鲜明,常以儒家伦理为评判标准,对佛道二教保持警惕。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使得其禅诗创作未能完全突破儒学束缚,数量与影响力亦不及苏轼等人。
元好问的禅学与文学实践,是金元时代的文化缩影。他既以儒家“以诚为本”为根基,又汲取禅宗智慧,形成了融会诗禅的独特路径。尽管其禅诗成就有限,但元好问对禅宗思想的吸收与转化,仍为后世提供了儒释交融和博弈的样例,彰显出传统文化在多元思想碰撞中的复杂面相。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1]参见姚乃文《元好问与佛教》,《五台山研究》1986年第4期;狄宝心、任立人:《元好问对佛教文化的弘扬兼蓄》,《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李正民、牛贵琥:《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高桥幸吉:《元好问与佛教——以嵩山时期为中心》,《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第271-278页;降大任:《元遗山交往僧道考》,《元遗山论(增订版)》,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年,第418-428页;冯大北:《元好问的佛教思想与信仰——以<寄英禅师>为切入点》,《名作欣赏》2020年第2期;黄惠菁:《论金元时期性英木庵与元好问之交游》,释永信主编《少林学辑刊》第1辑《少林寺与禅宗祖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237-257页;贾晓峰:《佛寺书写与元好问南渡后的诗文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2]元好问:《汴禅师自斫普照瓦为砚,以诗见饷,为和二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23 页。
[3]元好问:《赠汴禅师》,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216 页。
[4]元好问:《赠湛澄之四章》,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348 页。
[5]元好问:《愚轩为赵宜之赋》,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一,第 1 册,第 40 页。
[6]元好问:《答俊书记学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394 页。
[7] 元好问:《马云卿画纸衣道者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4 册,第 1668 页。
[8]元好问:《先大夫诗》,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癸集第十,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2681 页。
[9]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6 页。
[10]元好问:《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105 页。
[11] 翁方纲著,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56 页。
[12] 参见杨国勇《元好问对中国宗教史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13]贾晓峰:《佛寺书写与元好问南渡后的诗文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14] 参见降大任《元遗山交往僧道考》,《元遗山论》(增订版),第 418—428 页。
[15]元好问:《夜宿秋香亭有怀木庵英上人》,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3 册,第 1472 页。
[16]元好问:《少林药局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78 页。
[17] 王树林:《金末诗僧性英考论》,赵维江主编《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第 14 页。
[18] 叶宪允:《万松行秀门人弟子中的少林寺僧团》,释永信主编《少林学研究·少林学辑刊》第 1 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 年,第 260—261 页。
[19] 元好问:《少林药局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78 页。
[20] 元好问:《皓和尚颂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381 页。
[21] 元好问:《寿圣禅寺功德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439 页。
[22] 元好问:《皓和尚颂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380 页。
[23] 元好问:《少林药局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7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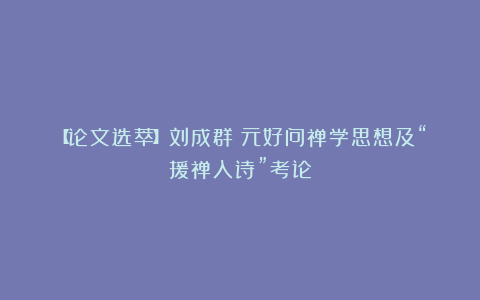
[24] 元好问:《答聪上人书》,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400—1401 页。
[25] 刘秉忠:《读遗山诗十首》,《刘太傅藏春集》卷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1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83 页。
[26] 元好问:《太原昭禅师语录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 401 页。
[27] 元好问:《清凉相禅师墓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100 页。
[28] 元好问:《寄西溪相禅师》,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294 页。
[29] 元好问:《告山赟禅师塔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470 页。
[30] 元好问:《徽公塔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 874 页。
[31] 元好问:《太原昭禅师语录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 402 页。
[32] 元好问:《寿圣禅寺功德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438 页。
[33] 元好问:《皓和尚颂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381 页。
[34] 高桥幸吉:《元好问与佛教———以嵩山时期为中心》,《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77 页。
[35] 元好问:《闲闲公墓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三,上册,第 276 页。
[36] 同上书,第 272 页。
[37] 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七,下册,第 1498 页。
[38] 元好问:《曲阜纪行十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3 册,第 1238 页。
[39] 元好问:《坟云墓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二,上册,第 128—129 页。
[40] 元好问:《竹林禅院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二,上册,第 189 页。
[41] 元好问:《少林药局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78 页。
[42] 元好问:《龙门川大清安禅寺碑》,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 952 页。
[43] 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七,下册,第 1498 页。
[44] 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九,第 106 页。
[45] 元好问:《杜诗学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91 页。
[46] 元好问:《麻杜张诸人诗评》,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二,上册,第 197—198 页。
[47] 伍先林:《曹洞宗的禅风与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佛学》2020 年总第 47 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168 页。
[48]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25 页。
[49] 木村清孝:《中国华严思想史》,李惠英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第 257 页。
[50] 李纯甫:《鸣道集说》卷五,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 26 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 年,第 868 页。
[51] 袁志伟:《辽宋佛学融合之下的万松行秀禅思想》,《中国哲学史》2023 年第 2 期。
[52]元好问:《陶然集诗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150 页。
[53]元好问:《杜诗学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91 页。
[54] 元好问:《米帖跋尾》,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436 页。
[55]圜悟克勤著,尚之煜校注《碧岩录》卷五,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37 页。
[56]元好问:《陶然集诗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150 页。
[57]元好问:《皓和尚颂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381 页。
[58]元好问:《告山赟禅师塔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469 页。
[59]元好问:《陶然集诗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147—1153 页。
[60]元好问:《新轩乐府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下册,第 1383—1384 页。
[61]元好问:《木庵诗集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 1087 页。
[62]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 1023 页。
[63]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一,第 1 册,第 48、52 页。
[64]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第 59 页。
[65]元好问:《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106 页。
[66]元好问:《木庵诗集序》,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 1087 页。
[67]赵秉文:《同英粹中赋梅》,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四,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97—98 页。
[68]参见施国祁注《元遗山诗集笺注》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327 页。
[69]参见元好问《赠汴禅师》,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218 页。
[70]冯璧:《元光间,予在上龙潭。每春秋二仲月,往往与元雷游历嵩少诸蓝。禅师汴公方事参访,每相遇,辄挥毫赋诗, 以道闲适之乐。今犹梦寐见之。儿子渭近以公故抵任城,禅师附寄诗以叙畴昔。未几,驻锡东庵。因造谒,间出示裕之数诗, 醉笔纵横,亦略道嵩游旧事。感叹之余,漫赋长句二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己集卷六,第 5 册,第 1479 页
[71]元好问:《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105 页。
[72]元好问:《清凉相禅师墓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101 页。
[73]元好问:《奉酬子京禅师见赠之什三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3 册,第 1203 页。
[74]元好问:《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105 页。
[75]元好问:《答俊书记学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394 页。
[76]参见李正民、牛贵琥《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冯大北:《元好问的佛教思想与 信仰———以〈寄英禅师〉为切入点》,《名作欣赏》2020 年第 2 期。
[77]元好问:《过邯郸四绝》,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4 册,第 1645 页。
[78]元好问:《杂著九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六,第 4 册,第 1808—1809 页。
[79]元好问:《又解嘲二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 2 册,第 981 页。
[80]元好问:《愚轩为赵宜之赋》,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一,第 1 册,第 40 页。
[81]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范道济点校《查慎行全集》第 19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091 页。
[82]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丙集第三,第 2 册,第 755 页。
[83]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第 1025 页。
[84]元好问:《帝城二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253 页。
[85]元好问:《除夜》,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343 页。
[86]元好问:《甲午除夜》,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四,第 2 册,第 701 页。
[87]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卷四三,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79 页。
[88]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卷四四,下册,第 215 页。
[89]元好问:《龙门杂诗二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114 页。
[90]元好问:《感兴四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4 册,第 1649 页。
[91]白居易:《读禅经》,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二,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716 页。
[92]元好问:《真味斋》,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六,第 4 册,第 1865 页。
[93]元好问:《刘氏明远庵三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4 册,第 1715 页。
[94]元好问:《周才卿拙庵》,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3 册,第 1129 页。
[95]元好问:《刘君用可庵二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4 册,第 1662—1663 页。
[96]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0 页。
[97]白居易:《香山寺二绝》,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一,第 2 册,第 705 页。
[98]白居易:《秋江晚泊》,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一三,第 1 册,第 263 页。
[99]白居易:《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一三,第 1 册,第 265 页。
[100]元好问:《洛阳高少府瀍阳后庵五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436 页。
[101]元好问:《萧寺僧归横轴》,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六,第 4 册,第 1739 页。
[102]元好问:《少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362 页。
[103]元好问:《少林雨中》,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364 页。
[104]元好问:《阳泉栖云道院》,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4 册,第 1398 页。
[105]元好问:《大乘夕照》,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二,第 1 册,第 334 页。
[106]元好问:《感兴四首》,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卷五,第 4 册,第 1649 页。
[107]元好问认为杜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参见元好问《杜诗学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上册,第 91 页。
[108]朱良志:《试论元好问的“以诚为本”说》,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元好问研究会编《元好问研究文集》,太原:山西人 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94 页。
[109]参见刘泽《元好问晚年诗歌创作论略述》,《文学遗产》1990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