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1899—1983)作为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其艺术生涯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历经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初期等重大历史阶段。在时代剧烈变革中,他始终坚守大写意花鸟画的艺术本体价值,既未因政治压力而放弃传统,亦未在文化断裂中迷失方向,反而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持续探索花鸟画的现代转型路径。
本文以李苦禅的艺术实践为线索,系统考察其在战争年代对民族精神的视觉建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艺术独立性的维护,以及在文革结束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弘扬。研究表明,李苦禅通过“鹰”“松”“荷”等具有象征意义的题材,将个人情感、人格理想与民族魂魄融为一体,使花鸟画超越“闲情逸致”的传统功能,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文化载体。他坚持“画品即人品”的艺术信条,在动荡岁月中守护了中国画的笔墨精神与审美独立性,彰显了一位艺术家在历史沉浮中的文化自觉与精神担当。其艺术实践为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兼具传统深度与时代高度的典范。
关键词: 李苦禅;20世纪中国画;花鸟画;艺术独立性;民族精神;文化传承
一、引言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与文化形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在这一历史洪流中,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以“写意”为核心、以“抒情”为功能的花鸟画,面临合法性危机。新文化运动倡导“美术革命”,主张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革命战争时期,艺术被要求服务于政治宣传;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文艺政策强调“为工农兵服务”;至“文革”十年,传统绘画更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压制。在如此动荡的时代语境中,花鸟画因其“非叙事性”“非功利性”的特质,一度被边缘化甚至否定。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中,李苦禅以其坚定的艺术信念与深厚的文化修养,成为守护大写意花鸟画命脉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持创作,更在政治高压下捍卫传统笔墨的尊严,并在新时期积极推动中国画的复兴。他的一生,堪称20世纪中国花鸟画命运的缩影。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李苦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实践,探讨其如何在时代沉浮中坚守花鸟画的独立性,如何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精神建构相结合,进而揭示其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意义。
二、战争年代:在民族危亡中建构花鸟画的精神高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深陷内忧外患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传统文化艺术面临生存危机。许多画家转向人物画或宣传画,以图“救亡图存”。在这一背景下,坚持花鸟画创作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表达。李苦禅的选择,不仅出于艺术偏好,更是一种精神抵抗。
1937年北平沦陷后,李苦禅拒绝与日伪合作,生活困顿,却仍坚持作画。他笔下的“鹰”在此时期获得全新的象征意义。鹰立于孤松之上,目光如炬,羽翼如铁,背景常以焦墨皴擦出嶙峋山石,整体构图充满张力与悲壮感。此类作品如《松鹰图》《铁骨雄鹰》等,已非传统文人画中“闲逸”的审美对象,而成为民族不屈精神的视觉象征。他在题跋中常书“独立苍茫自咏诗”“天地有正气”等诗句,明确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李苦禅并未将花鸟画直接转化为宣传工具,而是通过意象的升华,使其承载深层的文化精神。他坚持花鸟画的“抒情”本质,但将“情”从个人小我扩展为民族大我。这种“以物喻志”的创作方式,既保持了艺术的独立性,又回应了时代需求。正如他在笔记中所言:“画画不是喊口号,但心里要有正气。”这种内敛而深沉的表达,使他的花鸟画在战争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政治规训中维护艺术的独立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被要求反映工农兵生活,服务政治宣传。在此背景下,传统花鸟画再次面临边缘化风险。许多画家转向“花鸟画为政治服务”的路径,创作“百花齐放”“喜庆丰收”等主题作品,强调吉祥寓意与装饰性。
李苦禅虽顺应时代,创作部分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如《红梅迎春》《葵花向阳》等,但他始终未放弃大写意花鸟画的本质追求。他坚持认为,花鸟画的价值不仅在于“好看”或“吉祥”,更在于其笔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人格理想。他反对将艺术简化为政治符号,强调“画品即人品”,认为真正的艺术必须根植于高尚的人格修养。
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期间,他坚持传统笔墨训练,强调“以书入画”“笔墨为本”,反对以素描完全取代临摹。他主张学生“先懂物性,再谈笔墨”,要求在写生中理解植物生长规律与禽鸟生态特征,而非机械描摹。这种教学理念,实际上是在制度化教育体系中为传统艺术保留了一方净土。
此外,李苦禅在创作中继续深化“鹰”“松”“荷”等题材的精神内涵。如《荷塘清趣》系列,荷叶以泼墨写出,墨色淋漓,线条刚劲,既表现荷之清雅,又暗喻“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品格。这种将传统文人画精神与现代人格理想相结合的实践,使花鸟画在社会主义语境中依然保持其独立的审美品格。
四、文革结束后的文化复兴:弘扬传统与激扬民族魂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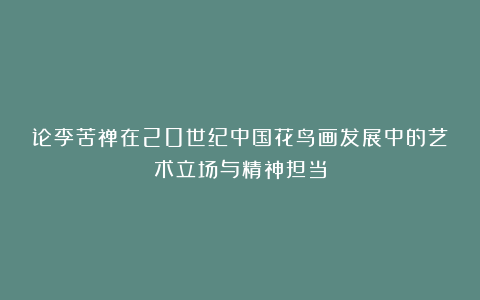
“文革”期间,李苦禅因“旧文人”身份遭受冲击,作品被毁,身心受创。然而,他始终未放弃艺术信念。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以近八十岁高龄重新投入创作与教学,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者。
这一时期,李苦禅的艺术呈现出更为开阔的格局。他积极参与中国画学会的重建,呼吁“抢救传统”,强调笔墨是中国画的“命根子”。他在全国多地讲学,系统传授大写意花鸟画技法,培养了大批青年画家。他主张“学古而不泥古”,鼓励学生在继承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其创作亦进入“人书俱老”的化境。晚期作品如《劲节凌云》《雄视》等,笔墨更加简练,气势更加磅礴。鹰的形象愈发雄健,松树愈加苍劲,构图多取全景式大景深,黑白对比强烈,极具视觉冲击力。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技巧的巅峰,更是其一生精神历程的凝结。他在题跋中常书“老夫聊发少年狂”“笔底波澜动九州”,展现出一位老艺术家在文化重建中的豪情与担当。
尤为可贵的是,李苦禅在弘扬传统的同时,始终保持开放心态。他支持中西融合的探索,但强调必须以中国画本体语言为基础。他认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古为今用”,使中国画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五、艺术独立性的坚守:从“抒写个人情趣”到“激扬民族魂魄”
贯穿李苦禅艺术生涯的核心,是其对花鸟画艺术独立性的坚守。他始终认为,花鸟画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有用”,而在于其能否表达真挚的情感与高尚的精神。
在战争年代,他将“个人情趣”升华为民族气节;在建设时期,他将“笔墨游戏”转化为人格修炼;在复兴阶段,他将“传统技艺”提升为文化使命。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使花鸟画突破了“闲情逸致”的局限,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文化载体。
他的独立性还体现在对艺术标准的坚持。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他始终以“笔墨”“气势”“神韵”为评价作品的核心尺度,而非政治正确或市场价值。他常说:“画画要耐看,要经得起时间考验。”这种超越时代的艺术眼光,使其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六、结语
李苦禅的一生,是与20世纪中国花鸟画命运共沉浮的一生。在革命战争中,他以花鸟画抒写民族气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守护艺术的独立品格;在文革浩劫后,他挺身而出,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他始终坚信,花鸟画不仅是“技”,更是“道”;不仅是“艺”,更是“魂”。
他的艺术实践表明,真正的传统不是僵化的遗产,而是活在当下的精神资源;真正的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李苦禅以“鹰”为魂,以“笔”为剑,在历史的沉浮中坚守文化立场,激扬民族魂魄,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审李苦禅的艺术道路,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画的复杂历程,更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守护文化根脉、建构民族审美提供了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