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背景下,传统文人画经历了深刻的世俗化嬗变,而“海上画派”的兴起与发展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海上画派”为研究对象,将其世俗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50s–1880s)为市场适应期,以任熊、任伯年为代表,绘画开始服务于市民审美与商品经济;第二阶段(1890s–1910s)为文化调适期,以吴昌硕为核心,实现“雅俗共赏”的艺术平衡;第三阶段(1910s–1930s)为现代转型期,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绘画走向公共性与个体表达。
文章指出,这一嬗变的内在动因源于文人身份的职业化转变、文人画性质从“自娱”向“他娱”的功能转向,以及西学东渐与都市文化的时代冲击。研究认为,文人画的世俗化并非艺术品格的降格,而是在新语境下的创造性重构,其强调艺术与社会、大众与市场的互动机制,对当代中国美术的公共性建设与文化传承具有深远启示。
关键词: 海上画派;文人画;世俗化;艺术转型;吴昌硕;任伯年;近代美术
一、引言
文人画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主流传统,自宋代以降,历经元、明、清三朝的发展,形成了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写胸中逸气”为核心的艺术理念。其创作主体为士大夫阶层,功能在于修身养性、寄情遣兴,审美标准强调“清逸”“古雅”“书卷气”,具有鲜明的精英性与封闭性。然而,进入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爆发、通商口岸开放、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文人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逐渐瓦解。在此背景下,文人画开始脱离士绅阶层的专属领域,进入市民社会与市场体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世俗化趋势。
“海上画派”(简称“海派”)正是这一历史转型的典型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绘画群体,其创作实践不仅反映了艺术风格的演变,更深层地揭示了文人画在社会功能、文化属性与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性转变。本文认为,“海派”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均对应着文人画世俗化进程的不同深度与面向。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系统梳理,本文旨在揭示近代文人画世俗化嬗变的内在动因——即文人身份的转变、文人画性质的转向与时代新潮的冲击,并阐明这一转型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二、第一阶段:市场适应期(1850s–1880s)——文人身份的职业化与艺术的商品化
“海派”的初步形成始于19世纪50年代上海开埠后的社会剧变。随着租界设立、工商业繁荣,大量江浙画家为谋生计迁居上海,形成了以任熊、任薰、任伯年兄弟为代表的早期“海派”群体。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文人身份的职业化与艺术创作的商品化,标志着文人画从“士人修养”向“职业技艺”的初步转型。
在传统社会中,文人画家多为官僚、地主或隐逸之士,绘画是“余事”,其价值不在于市场交换。然而,上海的都市环境打破了这一模式。新兴市民阶层——包括商人、买办、手工业者——成为艺术消费的主体,他们对书画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审美趣味与传统士大夫大相径庭。他们偏好色彩明快、题材吉祥、构图饱满的作品,以满足厅堂装饰、节庆馈赠等实际功能。
在此背景下,早期“海派”画家主动调整创作策略,将绘画视为谋生手段。任伯年即为典型例证。他出身平民,早年曾在苏州、宁波等地以画像为业,后寓居上海,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画家之一。其作品如《群仙祝寿图》《钟馗捉鬼图》《松下高士图》等,虽保留文人画的笔墨意趣,但在题材上大量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神仙、寿星、财神等形象,色彩浓丽,构图繁密,极具装饰性与观赏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润例”(书画收费标准)的公开化与制度化,标志着艺术生产的市场化完成。画家通过报刊登载润格,明确标价,接受订制,其身份由“文人”转变为“画师”或“艺术家”。这种职业化转型,使文人画首次大规模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开启了其世俗化进程的第一步。
然而,这一阶段的世俗化仍停留在“技艺适应市场”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自觉。画家多为迎合需求而创作,理论建构薄弱,艺术创新多限于形式层面。
三、第二阶段:文化调适期(1890s–1910s)——文人画性质的转向与“雅俗共赏”的实现
进入19世纪末,“海派”进入成熟期,以吴昌硕(1844–1927)为代表,开启了文人画世俗化进程的第二阶段:文化调适期。此阶段的核心特征是文人画性质从“自娱”向“他娱”的功能转向,以及“雅俗共赏”美学理想的系统实现。
吴昌硕的出现,标志着“海派”从“市场驱动”向“文化引领”的跃升。他虽以卖画为生,但始终强调艺术的文化属性与人格象征。其艺术实践建立在深厚的金石学、书法与诗文修养之上,主张“画气不画形”“我自用我法”,将文人画的“写意抒怀”传统推向新的高度。他以篆籀笔法入画,笔力雄浑,墨色苍厚,开创了“金石入画”的新风,其《紫藤图》《梅花图》《葫芦图》等作品,既具视觉冲击力,又蕴含深沉的文化意蕴。
尤为关键的是,吴昌硕成功实现了“雅”与“俗”的融合。他笔下的果蔬题材,如《白菜萝卜图》《荔枝图》《葡萄图》,虽取材于市井生活,寓意吉祥(如“百财”“多子”),但通过题跋点化,赋予其文化深度。如题《白菜图》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语源自宋代《菜根谭》,原为修身格言,吴昌硕借此既彰显文人清贫自守的品格,又暗合市民勤俭持家的美德,实现了“俗题雅化”的艺术升华。
此外,吴昌硕积极参与“西泠印社”“海上题襟馆”等文化团体,与章太炎、沈曾植等硕学鸿儒交游,其艺术被赋予“国粹”“遗民气节”的象征意义。这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使“海派”超越了单纯的技艺群体,成为具有文化自觉的艺术共同体。
此阶段的文人画,已不再是被动适应市场,而是主动塑造审美。其性质从“自娱”(为己)转向“他娱”(为人),从个人修养扩展为公共文化实践。艺术的功能不再局限于修身,更在于教化、交流与认同构建。
四、第三阶段:现代转型期(1910s–1930s)——时代新潮的冲击与艺术的公共性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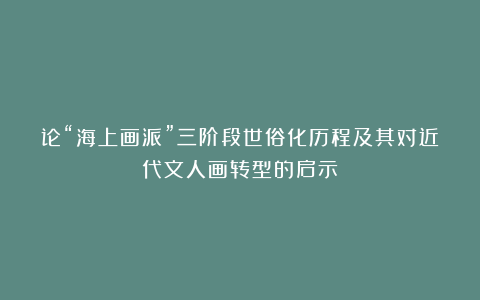
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学思潮的涌入与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这一时代新潮的冲击,推动“海派”进入第三阶段:现代转型期。此阶段以吴昌硕晚期及后继者如王一亭、潘天寿、刘海粟等为代表,其核心特征是文人画向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双重拓展。
新文化运动倡导“美术革命”,批判传统文人画的“陈陈相因”与“脱离现实”,主张引入西方写实主义与现代艺术理念。在此背景下,“海派”画家面临新的挑战与选择。一部分画家如刘海粟、林风眠转向学院派与现代主义,而另一部分则在传统基础上寻求革新。
吴昌硕晚年作品更趋简练、抽象,强调笔墨的纯粹性与精神性,如《墨梅图》《石鼓文对联配画》,已具表现主义倾向。其弟子王一亭则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以书画赈灾,推动艺术的社会化应用。潘天寿在继承吴昌硕雄浑风格的同时,强化构图的现代感与形式张力,探索“传统出新”的路径。
此外,美术学校(如上海美专)、画会组织、报刊媒体的兴起,使艺术传播从私人交往转向公共领域。画展、画册、艺术评论成为常态,艺术的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文人圈层,而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文人画由此进入“公共艺术”时代,其世俗化不再仅指“迎合大众”,更意味着艺术与社会的深度互动。
五、内在动因:身份、性质与时代的三重变奏
“海派”三阶段的世俗化嬗变,其内在动因可归结为三方面:
文人身份的转变:从“士大夫”到“职业画家”,身份的职业化使艺术脱离依附性,进入自由市场,成为独立的文化生产。
文人画性质的转向:从“自娱”到“他娱”,功能从个人修养转向社会交流,艺术成为文化认同与价值传播的媒介。
时代新潮的冲击:西学东渐、都市化、现代化思潮迫使传统艺术回应现实,推动其在形式、内容与传播方式上的全面革新。
这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文人画世俗化的深层动力机制。
六、结语:世俗化的时代意义与当代价值
“海上画派”的三阶段世俗化历程,揭示了传统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与创造性。文人画的世俗化并非艺术品格的降格,而是在新社会条件下的一次文化重构。它证明了传统艺术可以在保持文化内核的同时,实现功能转型与形式创新。
这一转型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提供了“在传统中创新”的可行路径,避免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断裂。其当代价值在于: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艺术如何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实现公共性与大众化?“海派”的经验表明,真正的艺术生命力在于与社会的深度对话。当代中国美术应继承“海派”的融合智慧,推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