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物画在题材拓展、造型突破、构图创新及材料实验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趋势,其叙事方式与审美取向亦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笔墨作为传统绘画的核心语言,其观念内涵经历了从技法承载到文化表征的深层转化。本文聚焦“笔墨观念”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构路径,探讨其如何参与并推动人物画意象体系的生成。研究表明,当代艺术家通过弱化笔墨的书写性规范、强化其表现性功能,并结合综合材料与跨媒介手段,使笔墨从“状物传神”的工具升华为情感与思想的直接载体。这种观念转变不仅回应了现代视觉经验与社会现实的需求,也使人物画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时,实现了意象表达的当代性建构。文章认为,确立契合时代精神的笔墨观,是实现中国人物画创造性转化的关键环节。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写实主义的引入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中国人物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从徐悲鸿倡导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到蒋兆和《流民图》中融合中西的现实主义表达,再到改革开放后形式探索与观念更新的多元并进,中国人物画逐步摆脱了传统文人画以山水、花鸟为主导的格局,成为反映时代精神与个体命运的重要艺术门类。
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人物画在题材上广泛涉猎都市生活、边缘群体、身份认同、历史记忆等议题;在造型上突破写实框架,出现夸张、变形、解构等手法;在构图上借鉴摄影、影视等视觉媒介的叙事逻辑;在意象色彩与材料运用上则大胆吸收装置、影像、拼贴等当代艺术语言,形成了开放而多元的创作生态。然而,在形式语言不断拓展的同时,如何维系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尤其是“笔墨”这一核心元素的当代价值,成为学界与创作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传统意义上,“笔墨”不仅指用笔用墨的技术规范,更承载着“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深层美学理念。在人物画中,笔墨长期服务于“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强调线条的书写性与墨色的层次感。然而,面对现代视觉文化的冲击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固守古典笔墨范式已难以充分表达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存体验。因此,重新审视并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笔墨观念,成为推动中国人物画意象创新的关键所在。本文旨在梳理当代人物画中笔墨观念的演变轨迹,分析其在多元创作实践中的具体呈现,并探讨其对意象构建的深层影响。
二、笔墨观念的历史沿革与当代挑战
在中国画理论体系中,“笔墨”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南齐谢赫“六法”中“骨法用笔”位列第二,唐代张彦远明确提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将用笔提升至统摄造型与意境的高度。宋代以后,文人画兴起,笔墨逐渐脱离单纯状物功能,发展为抒发胸臆、标示品格的独立审美范畴。元代赵孟頫倡导“书画同源”,强调笔线的书法性;明清之际,徐渭、八大山人等进一步以狂放笔墨表达孤愤之情,使笔墨成为主体精神的直接外化。
在传统人物画中,笔墨主要体现为“十八描”等线描体系,如顾恺之“高古游丝描”之绵延不绝,吴道子“兰叶描”之顿挫飞扬,均以线条的节奏与质感传达人物神态与气质。至近现代,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引入西方解剖、透视与明暗法,形成“中西融合”新体。他们虽重视素描基础,但仍强调“以线立骨”,力图在写实造型中保留笔墨韵味。例如,蒋兆和在《杜甫像》《阿Q像》中以枯涩苍劲的笔触勾勒面部结构,墨色层层皴擦,既具体积感又不失笔意,实现了写实与写意的初步融合。
然而,当代社会的视觉经验已发生根本变化。摄影、数字图像、短视频等媒介塑造了新的观看方式,人们对形象的感知不再局限于静态、完整的轮廓,而更关注瞬间、碎片、动态与心理真实。与此同时,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碰撞与身份焦虑,使艺术家需要更复杂、更具张力的语言来表达个体经验。在此背景下,传统笔墨的某些规范——如强调中锋用笔、忌讳“钉头鼠尾”、追求“温润含蓄”等——在表现激烈情感、异质空间或抽象心理时显得力不从心。若仅将笔墨视为装饰性元素或风格标签,则易陷入形式主义窠臼,丧失其应有的精神深度。
因此,当代人物画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尊重笔墨文化基因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观念性的拓展与重构,使其真正成为当代视觉表达的有效手段。
三、笔墨观念的当代转型路径
当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多种笔墨观念的转型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书写性”到“表现性”的转向
传统笔墨强调“写”而非“描”,注重运笔的节奏与气脉贯通,具有强烈的书法意味。当代部分艺术家则弱化其书写规范,强化其表现功能。如田黎明在《都市系列》中采用“没骨法”,以淡墨与色块平涂叠加,人物轮廓模糊,光影交融,营造出都市生活的疏离感与漂浮感。其笔墨不再追求线条的力度与节奏,而是通过墨色的氤氲与空间的虚化,传达现代人内心的迷茫与不确定性。
(二)笔墨与身体经验的结合
一些艺术家将笔墨视为身体动作的直接痕迹,强调创作过程中的即兴与偶发。刘庆和的水墨人物常以大笔泼洒、刮擦、拓印等方式完成,画面充满躁动的能量。他在《夜游》系列中,以粗重墨线勾勒扭曲的人体,背景则以浓淡不一的墨块堆叠,形成压抑的都市空间。这种笔墨语言不再服务于形象的完整性,而是成为情绪宣泄的通道,体现了主体与媒介的激烈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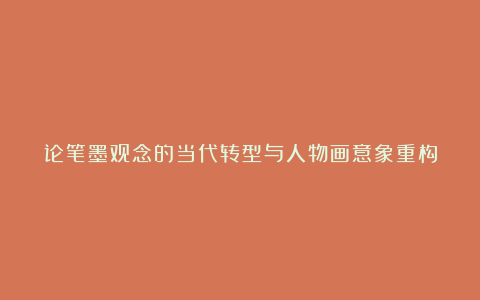
(三)笔墨的符号化与观念化
在观念艺术影响下,笔墨本身被赋予象征意义。李孝萱在《城市系列》中,以急促、痉挛式的线条描绘地铁中拥挤的人群,线条的密度与方向构成视觉压迫感,笔墨成为都市焦虑的隐喻。他有意打破传统“骨法用笔”的秩序,使线条失去支撑结构的功能,转而成为心理紧张的视觉对应物。这种处理使笔墨超越技术层面,升华为社会批判的符号。
(四)笔墨与综合材料的融合
许多艺术家将水墨与丙烯、拼贴、金属箔、现成品等材料结合,拓展笔墨的物质性与表现维度。如武艺在《写生系列》中,将宣纸与布面结合,以水墨与油彩并置,形成质感对比。笔墨不再局限于“水晕墨章”的柔和效果,而可呈现斑驳、锈蚀、撕裂等工业感肌理,从而更贴切地表现当代生活的复杂质地。
四、笔墨与意象构建的互动关系
在当代人物画中,笔墨不仅是形式语言,更是意象生成的核心机制。所谓“意象”,并非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是主客交融的心理图景。笔墨观念的转型,直接决定了意象的构成方式与精神指向。
首先,笔墨的“非书写性”处理打破了传统人物画的“正典”姿态,使意象更具现代性。传统仕女、高士形象往往端庄静穆,依赖规整线条维持其道德与审美秩序。而当代人物画中扭曲的线条、破碎的墨块、非理性的构图,恰恰解构了这种秩序,呈现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分裂与挣扎。如周京新在《水浒人物》系列中,以“积墨法”层层堆积,人物面部如雕塑般凹凸嶙峋,眼神空洞,笔墨的厚重感转化为心理的沉重感,构建出极具张力的悲剧性意象。
其次,笔墨的材料化倾向增强了意象的物质性与现场感。当水墨与工业材料结合,画面不再仅仅是“画出来”的幻象,而是成为承载时间、记忆与社会痕迹的“物”。例如,梁绍基以蚕丝包裹水墨人物,蚕丝的生长过程与笔墨的凝固形成时间对话,意象由此超越视觉层面,进入生命哲学的维度。
最后,笔墨的即兴性与偶发性赋予意象以未完成性与开放性。传统人物画追求“尽善尽美”,而当代作品常保留笔触的粗糙、墨色的渗化、形象的未定型,这种“未完成感”恰恰契合了现代人对确定性的怀疑与对可能性的期待。笔墨在此成为开放的意义场域,邀请观者参与意象的再创造。
五、结语
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多元格局,既是艺术自主性发展的结果,也是时代精神的投射。在这一背景下,笔墨观念的转型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其生命力的激活。通过从“书写性”向“表现性”、从“技法”向“观念”、从“单一媒介”向“综合材料”的拓展,笔墨得以重新融入当代视觉表达系统,成为构建新型意象的重要力量。未来的发展,仍需在创新与传承之间保持张力:既避免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简单模仿,也防止对传统笔墨的僵化复制。唯有在深刻理解笔墨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与对媒介的积极探索,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物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在全球化语境中持续发出独特而有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