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作为书法学习的核心方法,其观念在中国艺术史上经历了从“刻意摹古”到“入古出今”,最终走向“六经注我”的历时性演进。个体对书法的定位差异,深刻影响其临摹实践的取向。八大山人(朱耷)一生历经儒生、文人至画家的身份转型,其书法临摹亦相应呈现出基础性、综合性与融合性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通过梳理八大山人早、中、晚期的书法作品与艺术经历,揭示其临摹观的动态演变过程:早年作为儒生,以董其昌为中介,进行“刻意摹古”式的基础性临摹,重在笔法传承;中年作为文人,广泛取法晋唐诸家,形成“入古出今”的综合性临摹,强调风格整合;晚年作为画家,将绘画的笔墨意趣与空间构成融入书法,实现“六经注我”式的融合性临摹,使书法成为个体心性的直接显现。这一演变不仅体现了八大山人艺术思想的深化,更映射了其从文化承继者到艺术创造者的身份跃迁,是传统书法临摹观念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生动实践与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八大山人;书法临摹;摹古;六经注我;身份转型;笔墨融合;艺术演变
一、引言:临摹观念的历时性演变与个体差异
“临摹”是中国传统书画学习的基本路径,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审美与艺术观念的变迁而不断演化。从艺术史的宏观视角看,临摹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宋元以前以“刻意摹古”为主导的阶段,强调对古人法度的忠实再现,如唐代欧阳询“明窗净几,笔砚纸佳,向背如法,肥瘦适均,筋骨调匀,端正严密”之说;二是明清之际兴起的“入古出今”观念,主张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个人风格,董其昌提出“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倡导“能于同处求异”;三是晚明以降,尤其在心学与禅宗影响下,发展出“六经注我”式的临摹观,即以古法为工具,服务于个体心性的表达,如徐渭“出己意,以心驭笔”,强调“天机自动”。
然而,临摹观念的形成不仅受时代思潮影响,更与个体对书法的定位密切相关。若视书法为科举应试的工具,则临摹重在规范与工整;若视其为文人修养的体现,则重在气韵与格调;若视其为艺术创造的媒介,则重在个性与表现。八大山人(约1626—1705)的一生,恰好经历了从儒生(科举预备)、文人(文化精英)到画家(艺术创造者)的身份转型,其书法临摹实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从“基础性”到“综合性”再到“融合性”的三阶段演进。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其书法作品的风格演变,揭示其临摹观与身份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基础性临摹:儒生阶段的“刻意摹古”
八大山人早年出身明宗室,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教育,其人生最初目标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一名“儒生”。在此阶段,书法是“士”的基本修养,更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其临摹以“取法乎上”、掌握规范为首要目的。
据文献与作品考证,八大山人早年书法主要取法董其昌。董其昌不仅是晚明书坛领袖,更是“南北宗论”的倡导者,其书风秀逸清雅,笔法精微,深得文人推崇。八大山人早年临摹董书,极为忠实,力求形神兼备。其《行书临古诗帖》等作品,结体疏朗,用笔轻盈,提按分明,章法清秀,明显带有董其昌的影子。这种临摹属于典型的“基础性临摹”,即以掌握笔法、结构、章法等基本技法为核心,强调对范本的忠实再现。
此阶段的临摹观可归为“刻意摹古”。其目的不在创新,而在“入古”——通过反复练习,将古人的法度内化为自身的书写习惯。正如其早年题跋所言:“学书须临古人墨迹,方得笔法。”此时的八大山人,尚处于艺术学习的积累期,其书法定位是“承传者”,临摹是其进入文化正统的必经之路。
三、综合性临摹:文人阶段的“入古出今”
1644年明朝覆亡,八大山人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其儒生身份因国破而失效,转而遁入佛门,成为“文人”——一个以文化修养、精神独立与艺术表达为特征的群体。在此阶段,书法不再仅为应试工具,而成为抒写性灵、寄托情怀的媒介。其临摹观也随之从“刻意摹古”转向“入古出今”。
作为文人,八大山人开始广泛涉猎晋唐诸家,尤重王羲之、颜真卿、怀素等。其临摹不再局限于单一范本,而是进行“综合性临摹”——即在深入理解不同书家风格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与转化。例如,其《临王羲之<兰亭序>》虽以王书为本,但笔法较原帖更为凝重,结体略趋方正,已融入个人意趣;其《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则强化了颜书的雄强气势,用笔更加豪放,墨色浓重,体现出遗民文人的刚毅之气。
更重要的是,此阶段的临摹已非单纯的技术训练,而带有明确的风格追求。其书法在董其昌的秀逸之外,融入了王羲之的韵致、颜真卿的骨力与怀素的狂放,形成一种既古雅又雄健的独特风貌。这种“入古出今”的临摹观,强调“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寻求个人风格的萌芽。
其署款“八大山人”四字的演变,正是这一阶段临摹成果的集中体现:早期较为规整,中期笔法渐趋自由,字形开始拉长变形,为晚年的“八大体”奠定基础。此时的八大山人,已从“承传者”转变为“整合者”,临摹成为其构建个人艺术语言的重要手段。
四、融合性临摹:画家阶段的“六经注我”
约1680年还俗后,八大山人逐渐将艺术重心转向绘画,其身份也从“文人”进一步演变为“画家”。在此阶段,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书法不再是独立的艺术门类,而是与绘画笔墨融为一体。其临摹观也随之进入“融合性临摹”阶段,即“六经注我”式的创造性临摹。
所谓“融合性临摹”,指不再以古帖为直接范本,而是将长期临摹所积淀的笔墨经验,与绘画的视觉思维相结合,使书法成为绘画语言的延伸。其晚年书法,尤其是题画诗与署款,已完全突破传统书体的束缚,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八大体”:字形极度夸张变形,或拉长如孤竹,或压扁如顽石;笔法苍老滞涩,多用“颤笔”“战笔”,如“屋漏痕”“虫蚀木”;章法错落有致,字与字之间相互穿插,如同画中物象的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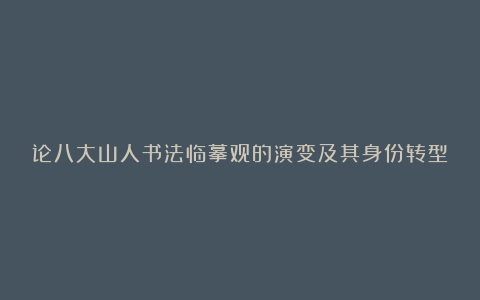
这种书法,已非“临摹”古人,而是“借用”古法以表达自我。其笔法源自篆隶的圆劲、行草的连带,但已被彻底改造,服务于整体画面的构成与意境的营造。如其画中题诗,字的大小、疏密、轻重随画面空间而变,书法线条与绘画线条浑然一体,共同构成“计白当黑”的视觉节奏。此时的临摹,实为“以我注六经”——古人法度成为其心性表达的工具,书法成为“心画”的直接显现。
此阶段的八大山人,已从“整合者”升华为“创造者”。其书法定位不再是“书写者”,而是“艺术家”。临摹的终极目的,已非掌握技法,而是实现“笔墨即心迹”的艺术理想。
五、临摹演变与身份转型的内在逻辑
八大山人书法临摹的三阶段演变,与其身份转型形成严密的对应关系:
儒生→基础性临摹:身份目标为“入世”,书法为工具,临摹重“法度”;
文人→综合性临摹:身份目标为“立身”,书法为修养,临摹重“风格”;
画家→融合性临摹:身份目标为“超越”,书法为艺术,临摹重“心性”。
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传统文人艺术从“技”到“艺”再到“道”的升华路径。其临摹观的深化,不仅是技法的积累,更是生命体验的沉淀与艺术自觉的觉醒。从“刻意摹古”到“六经注我”,八大山人完成了从文化承继者到艺术创造者的身份跃迁,其书法临摹实践,成为理解其艺术人格与时代精神的重要窗口。
六、结语:临摹作为生命历程的映照
八大山人的书法临摹史,是一部浓缩的个体艺术精神成长史。其从“基础性”到“综合性”再到“融合性”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临摹观念的历时性发展,更揭示了艺术创造与生命体验的深刻关联。
在“摹古”中,他学会了传统;在“出今”中,他找到了自我;在“注我”中,他超越了形式。其晚年书法,看似“怪诞”,实为“真率”;看似“无法”,实为“大法”。每一笔颤动的线条,都是其遗民孤寂、禅道体悟与艺术自觉的结晶。
八大山人的案例表明,临摹并非机械复制,而是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既是技艺的传承,更是生命的对话。当临摹从“学古”走向“我用”,艺术便真正获得了自由。八大山人以其独特的人生轨迹与艺术实践,为传统书法临摹注入了深刻的现代意义:真正的临摹,最终是为了不再临摹——而是让古人的灵魂,在自己的笔下重生。
文章作者:芦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