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朱耷)一生临习王羲之作品甚勤,尤以《兰亭序》为最,然其所有题跋中皆称此帖为《临河叙》,从未使用唐代以来通行的《兰亭序》之名。这一看似微小的命名差异,实则蕴含深刻的书法史观与文化立场。本文通过考证文献、比对版本与分析八大山人的艺术思想,揭示其坚持使用晋代原名《临河叙》的深层原因:八大山人认为,唐太宗时期由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摹拓的《兰亭序》诸本,虽标榜“存真”,实已掺入唐代的笔法规范与审美趣味,是对王羲之原迹的“二次创作”,背离了晋人“尚韵”的自然风骨。
其称《临河叙》,不仅是对文本原始出处的还原,更是对唐人“篡改”晋韵的批判,体现了其“直溯本源”的书法史观。这一命名行为,反映了八大山人作为遗民艺术家对“正统”与“异化”的敏感,以及在艺术传承中追求“古意纯正”的自觉意识,是其“入古出今”艺术理念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 八大山人;兰亭序;临河叙;王羲之;书法史观;唐摹本;晋韵;正名
一、引言:一个被忽视的命名现象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地位自唐代以来便已确立。历代书家临摹此帖者不计其数,多沿用唐人定名,称其为《兰亭序》。然而,在八大山人(约1626—1705)现存的所有书法作品与题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尽管他反复临写此帖,却从不称其为《兰亭序》,而一律称之为《临河叙》。
这一命名差异并非偶然或笔误。细察其《临临河叙》《书临河叙》等作品题款,皆严谨一致地使用“临河叙”三字。这一现象,长期未受学界足够重视,常被视为单纯的名称混用。然而,若结合八大山人的学术修养、艺术主张与历史语境深入考察,则可发现,这实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正名”行为,背后隐藏着其对书法传统、版本流传与审美本质的深刻思考。本文旨在揭示这一命名现象背后的书法史观,阐明八大山人为何坚持使用《临河叙》之名,并以此透视其艺术思想的核心维度。
二、“临河叙”与“兰亭序”:文本与名称的源流考辨
要理解八大山人的命名选择,必须首先厘清《临河叙》与《兰亭序》的关系。
(一)《临河叙》的原始记载
“临河叙”之名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临河叙》全文。该文共269字,内容记述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修禊集会之事,与今传《兰亭序》前半部分基本相同,但无“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等哲理抒发,亦无“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结尾。
据《世说新语》注,此文原题即为《临河叙》,是王羲之当时所作的集会纪事,属实用文体。其语言质朴,叙事清晰,符合晋人简淡文风。
(二)《兰亭序》的唐代定型
“兰亭序”之名始见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广搜其墨迹,尤重《兰亭》。据传,他命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以双钩填墨法精摹《兰亭序》真迹(后世所谓“神龙本”“虞摹本”“褚摹本”),并由欧阳询刻石于昭陵。此时,文本已扩充至324字,增加了大量抒情与哲理段落,文风更为华美,情感更为跌宕。
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何延之《兰亭记》等文献均称此帖为《兰亭序》,遂成定名。自此,《兰亭序》不仅成为书法经典,更被赋予“文翰双绝”的崇高地位。
(三)文本差异与版本争议
自宋代以来,学者如赵崡、郭沫若等即指出《临河叙》与《兰亭序》在文字、风格上的显著差异。《临河叙》朴实无华,《兰亭序》则辞采斐然,带有明显的六朝骈文特征。许多学者怀疑今传《兰亭序》文本为后人增饰甚至伪托,非王羲之原文。
因此,“临河叙”代表的是晋代原始文本与历史真实,“兰亭序”则是唐代重构后的文学与书法经典。二者虽同源,却分属不同历史层次。
三、八大山人的选择:为何坚持称“临河叙”?
八大山人精通经史,熟谙文献,其坚持使用《临河叙》之名,绝非无知,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判断与艺术立场。
(一)对唐摹本“笔法异化”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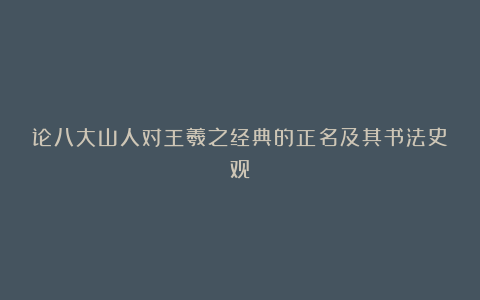
八大山人深知,今传《兰亭序》诸本皆为唐人摹本,非王羲之亲笔。更重要的是,这些摹本在“存形”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唐代的笔法体系与审美理想。
唐人书法崇尚法度、结构严谨、提按分明,如欧阳询之险峻、虞世南之温润、褚遂良之飘逸,皆具强烈的时代风格。冯承素“神龙本”虽以“下真迹一等”著称,但其线条的顿挫、转折的方硬、章法的规整,已明显带有唐人“尚法”的烙印,与晋人“尚韵”所推崇的“天然去雕饰”“风骨内含”的审美相去甚远。
八大山人在临写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异化”。他认为,唐摹本虽形似,却神非——它所呈现的,是唐人理解中的王羲之,而非真正的晋人风骨。因此,他拒绝使用唐代定名《兰亭序》,而回归晋代原名《临河叙》,以此强调其临摹对象的“本源性”与“纯粹性”。
(二)“直溯本源”的书法史观
八大山人的艺术主张一贯强调“入古出今”,但其“入古”并非盲目崇唐,而是追求“直溯晋魏”。他曾言:“写字之法,刚健婀娜,古人用笔,皆从此出。”其所推崇的“古人”,正是指钟繇、王羲之等晋人。
其称《临河叙》,实为一种“正本清源”的姿态。通过恢复原名,他试图剥离唐代附加的文化光环与形式规范,直接面对王羲之时代的书写语境。在他看来,《临河叙》的简朴文本与其想象中的晋人笔意更为契合——自然、率真、不事雕琢。这种对“古意纯正”的追求,使其临摹超越了技术复制,成为一种精神对话。
(三)遗民身份的文化隐喻
作为明宗室后裔与前朝遗民,八大山人对“正统”与“篡改”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清初政权对明朝制度的“继承”与“改造”,恰如唐人对晋人经典的“摹写”与“重塑”。他称《临河叙》而不称《兰亭序》,或许也暗含一种文化隐喻:真正的传统不应被后来者随意诠释与重构,而应保持其本真面貌。这是一种在艺术领域对“文化正统性”的坚守,与其遗民气节一脉相承。
四、艺术实践:从“临河叙”到“八大体”
八大山人对《临河叙》的临写,并非简单复刻,而是“以古为鉴”的创造性转化。
其临本多取《临河叙》文本,但笔法已完全个人化:线条圆劲滞涩,结体奇崛夸张,章法疏密错落。他并未模仿唐摹本的流畅秀美,而是以篆隶笔意入行草,强化骨力与拙趣。这种“反唐法”的处理,正是其批判唐人“异化”的实践回应。
通过临《临河叙》,他提取晋人“尚韵”的精神内核——自由、自然、超逸——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八大体”书法中。其晚年题画诗与署款,字形拉长变形,如孤竹擎天,笔意苍茫,正是对晋人风骨的现代诠释。
五、结语:命名背后的史观自觉
八大山人称王羲之名帖为《临河叙》而非《兰亭序》,是一个极具深意的文化行为。这一“正名”之举,揭示了他对书法传统的深刻反思:真正的经典传承,不应止步于形式的摹仿,而需追问其历史本源与精神实质。
他通过恢复晋代原名,批判了唐人对晋韵的“异化”,表达了“直溯本源”的艺术理想。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其渊博的文献学识,更彰显了其作为艺术家的史观自觉——在纷繁的版本与权威的定论中,保持独立的判断与对“真古意”的执着追求。
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八大山人的这一实践启示我们:对传统的尊重,不在于盲从既定的经典名称与范式,而在于深入历史肌理,辨别真伪,还原本源,最终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其“临河叙”之名,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面旗帜,标志着一种清醒、批判且富有创造力的传统观。
文章作者:芦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