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浮光掠影忆小学
作者 | 刘世华
原创 | 乡土中原
八岁那年,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万营小学。
(如今的万营小学完全没有了旧时的模样)
老师掏出一块糖,咬成两半,半块糖塞到我嘴里,余下的那一半塞到另一个新生嘴里,糖的甜味一直甜到了今天。老师教我们唱“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从此开启了我的学生时代。
那时我个子小,但也许是因为哥哥姐姐也在这所小学上学吧,也并没有人欺负我。我们跟着老师读书识字唱歌,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年级时是双班教学,教室里有一年级的学生,也有二年级的。
启蒙老师叫王录顺,他个子高,面容苍老消瘦,教我们拖着音调唱读“a—o—e—”,让我们比着黑板在自己的小黑板上写字,然后开始教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候进学校报到先准备一块小木板,上边钻俩小窟窿儿,绑上绳子斜挎到脖子上,走到哪儿,小黑板背到哪儿,上厕所也不取下来。
二年级的老师是刘海荣,按辈分,她是我本村的老姑奶。辈分长,其实年龄并不大。她是个温柔和美丽的人,个子高挑,面容清秀,性格慈祥和蔼,讲课条理清晰,但不苟言笑。她经常骑着自行车来校,后座上带着儿子刘东明。
听本村一个同学说,刘老师与王保泰事件受害者唐庄村支书有点联系,我不知道是否属实,当时社旗王保泰东北二王的事迹在同学中口口相传。我们一听到“敌特分子”这四个字就很害怕。
依稀记得有一天上学刚到校,班里一个同学造谣说“敌特分子”要到学校抓小孩,吓得我们几个同学躲到学校门外大桥下的桥洞里“潜伏”了一晌。
教我三年级的老师叫姚军坡,那时他还没有结婚,相貌英俊帅气,性格阳光开朗,他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看上去精神神的。
姚老师是队办老师,教了几年就不干了。那时候很少有国家分配的师专师范毕业生,差不多都是民办教师和队办教师。后来民办的45岁以下转正,队办的分流回家务农,也有交了八千一万五经过进修学校学习培训成为以工代教的在编教师。
三年级开始上早学。大概是我每天到校都比较早吧,老师让我拿着教室的钥匙。一天早上到校后,我翻遍口袋也找不到钥匙,老师来后,把教室后门的门轴摘下来,同学们猫着腰钻进教室学习。
老师让我回忆前一天放学后干了什么,我说我们几个同学在老沟逮鱼了,老师让我沿河去找。我顺着老沟一直走到宁庄西边大桥下,终于找到了教室钥匙。
我四年级的老师是徐继春和王文秀。徐老师对学生热情关心,讲课声音洪亮,情绪饱满,高兴的时候,她还给我们唱歌。王老师教数学,还代着音乐课,他性格幽默。我还记得他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家几口作诗,儿子屠夫写的是“一刀戳进肚肠肺,放出来的是屎尿屁。”
四年级时,我有幸代表万营小学到晋庄教办室参加竞赛考试,作文是让写一种熟悉的小动物。出了考场,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向老师汇报自己的选材。大充说,他写的是猫,“眼睛像铜铃,爪子像秤钩”,老师连连夸赞“写得好”。小海说他写的是大公鸡,“公鸡公鸡真美丽,大红冠子花外衣”,老师高兴地夸奖“写得也好”。
老师转过头来问我写的是什么,我说我把学过的课文《翠鸟》背默了下来。老师顿时连连叹气:“哎呀!你怎么这样写呢?你怎么这样写呢?看人家写得多好!”结果后来我的语文得了班级最高分。
考了一晌试,中午老师带我们去街上食品站院里吃饭,说是食品站,其实是屠宰场,在这里杀猪褪毛处理干净然后拉到街上卖。语文老师的弟弟在这里工作。
中午做的是心肺汤。对于很少有机会吃肉的我而言,又香又软的心肺汤简直是无上的美味。吃完一碗,老师说:“锅里还有,没吃饱的话再给你盛一碗?”我说好,老师又给我盛了一碗。吃罢,老师说:“锅里还有,能吃再给你盛一碗!”我又说好,老师给我盛了第三碗。三碗下肚,满口生香,饱嗝连连,心满意足。
老师说:“吃饱没有?吃饱了同学们把饭钱交一下,一碗三块钱。”我顿时面红耳赤,后悔不迭。出门时母亲特意塞给我三块钱让我上街买零食吃,真是羞坏人了。
好在小楠看出了我的窘相,小声说:“你钱不够的话我借给你。”我只好向小楠借了六块钱凑够九块交给老师。回家后悄悄给我妈说了,她皱着眉头抱怨我吃饭没个数,扬起巴掌要打我,却还是从墙上挂的纳底子做的新布鞋里掏出皱巴巴的六块钱让我还给了小楠。
五年级毕业班的老师是常杰龙和王永海,印象最深。常老师多才多艺,王老师治学严谨。我考到初中后,王老师调到初中教学,后来还担任了晋庄中学教导主任、校长。
我参加工作后,我们成了同事,他给我搭班,我当班主任教语文,他教我们班数学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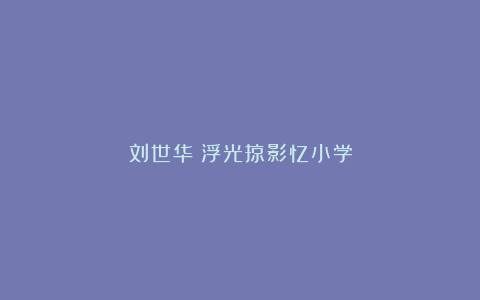
上体育课时,老师让我们在操场跑几圈,然后就自由活动。我们斗鸡,摔跤,踢毽子,跳大绳。
公路上走过一位老人,王茂环村朱庄村的同学们都大声喊起来:“老八路!老八路!”那人便来到操场坐在沙坑沿上。他身穿绿军装,解放鞋,戴军帽,腰扎武装带,衣服上系着几枚明晃晃的军功章,令人油然而生崇敬羡慕之情。
大家围坐在老八路四周,有人说:“老八路,唱个歌。”老八路就用沙哑的嗓音唱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大家仍不尽兴,拉着让他再唱一个,老八路就大声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唱完了,大家还不放他走,缠着要他讲革命故事,老八路又讲起战争故事来。
万营小学最令我敬佩的老师是常杰龙先生,他会用普通话读书,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说话也开始模仿他“洋气”的口音。他的字写得极好,粉笔字毛笔字都水平很高。学校办庆祝国庆特刊,他用整张的大白纸抄写学生优秀作文张贴在教室后墙上,还画上菊花牡丹兰草插图。
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幅:中间写着平躺的“甲”字,左边一个孩子说:“这是个甲字!”右边一个学生说:“这是个由字!”吃罢饭一到学校,我们就挤在一起看墙报读作文,看他画的画。现在想来,他对我接近文学书法爱好艺术有着多么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啊!
常老师还会拉二胡,吹笛子。他领着我们在老沟坝子下跑步,跑步回来后,他坐在讲台上拉着二胡教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教我们唱《我是一个粉刷匠》、《晚霞中的红蜻蜓》。
我们的小学校长是高永久老先生。他年近退休,身材高大,有些佝偻,颧骨突出,因为瘦,眼睛深陷,但却大而有神。
他经常戴着一顶深蓝色帽子,冬天还会围上黑白相间的方格围脖。他说话鼻音很重,瓮声瓮气的。他每天都会骑着二八大杠旧“永久”牌自行车来学校。
上初中时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到鲁迅先生对私塾先生寿镜吾先生的描述,我的眼前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高校长的形象。我们都怕高校长,其实他很慈爱。哪个小孩鼻涕“过河”了,他会俯下身去,左手搂着学生脊背,用右手帮他擤去鼻涕。看到哪个小孩哭了,他会问:“咋了?谁惹你了?给我说!”
当时,学校还流传着一个段子,据说是高校长自己说的,“你问我姓啥?你看看我的个子;你问我叫啥,你看看我的车子。”
万营小学三年级教室门外有一口土井,直径约一米五,青砖砌成。夏天的时候,中午家里经常吃蒜汁捞面条,上学就带一瓶面条汤。有的同学没带茶,就会撕下一张作业纸,交换一口面条汤。哪个同学要是不讲信用多喝一口,就要叫他“死皮子”或者“赖皮绞”。
面条汤喝完了,就有同学自告奋勇去井里打水。用铅笔杆缠着细细的红绳子,绳子一头绑着短木棍,竖立着放进瓶子,晃一下就横着提起瓶子了,趴在井沿上放下瓶子就打出水来。大家围成一圈,你一气他一气,咕嘟咕嘟喝完,换个同学又往井边跑去。
小学门外是条公路,离学校五十米有座桥,桥下流淌着老沟水,桥边修了个蓄水池,那里是我们的乐园。
上早学时我们爬到水泥拦河坝上,举着煤油灯高呼“平安无事”,还有喊“卖报!卖报!”的,爱搞恶作剧的男生趴在上面“嗷嗷”地学鬼叫吓唬上早学的女生。夏天我们在硬化过的蓄水池里洗澡,一旦岸上有同学报告“老师来了”,抓起裤子猫着腰就往庄稼地里跑。
三四年级上早自习都点煤油灯,油灯冒出黑烟,隔一会儿就得用笔尖挑去灯花。也有同学用细铁丝挂一串蓖麻籽,点着以后滋滋冒油,还发出幽香,没点灯的只好侧着身子“借光”。放学后,用手抠一下鼻孔,手指都是黑的。五年级时用上了电灯,前后梁头上各悬挂一盏15瓦的电灯泡,可是每生得交五毛钱。
小学的生活乐趣无穷,可是也有令人不愉快的回忆。有一件往事像一道伤疤,至少在当时伤害了我。
那是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教室里刚铺上青砖,老师让我们到学校前边大队部门口装沙弥住砖缝。大家就把书包里的书本掏出来,都有说有笑的背着书包去装沙。
妈妈用做衣服剩下的各色碎花布头剪成小三角状,给我缝了个大书包。我个子小,人又老实,装得满满的,踉踉跄跄朝教室走去。快要走到三年级教室门口时,“老冠儿”从后面跑过来。
“老冠儿”是我们班的“明星”,在学校无人不知。他上学不带书包不写作业,天天被老师批评,有时被老师拧着耳朵站教室外边。他爱打架,白白胖胖的脸上总留下打架新抠的指甲印。“老冠儿”当不上班干部,就自封“屁长”,要求哪个同学上课放屁都要先向他举手示意,“老冠儿”批准同意后发出信号大家都捏上鼻子才允许放。劳动这种事,“老冠儿”才不会参加呢!
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冠儿”跳起来,飞起一脚撞开了三年级教室的木门,随即逃之夭夭。王文秀老师正在三年级上音乐课,他冲出教室,看到我从门前经过,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揪到讲台上,用竹节教鞭狠狠在头上敲了几下。
我疼得哭起来,“老师,不是我,是’老冠儿’……”王老师说:“我就看见你了,还不老实!”“𠳐𠳐𠳐”又是几棍子,打得我眼冒金星,头上肿起了青包。
我哭得更厉害,“老师,真不是我,是’老冠儿’!他撞开门跑了……”“还不承认,还说是人家’老冠儿’!”王老师劈头盖脸又是几棍子,三年级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家的,只记得一路哭着回去,见到妈妈哭得更伤心。哭得声嘶力竭,委屈得上气不接下气,哽咽得天昏地暗,不省人事。多亏及时叫来了行医多年的外公打上点滴,次日上午才昏昏沉沉醒来。外公对父母说:“少嚷二娃儿,这娃儿气性大。”
将近40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脑门上还仿佛隐隐作痛。上初中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文秀老师,听说他调到桥头工作了。
后来,我考上唐师,毕业后成了人民教师。工作中,我偶尔也会想起这唯一的一次被老师打。我鞭策自己,处理问题要调查清楚,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并且,要大事化小,“得饶人处且饶人”。
作者简介
刘世华,又名刘铭,70后,社旗县晋庄镇万营村人,1997年至今在晋庄中学任教,爱好广泛,尤喜体育文学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