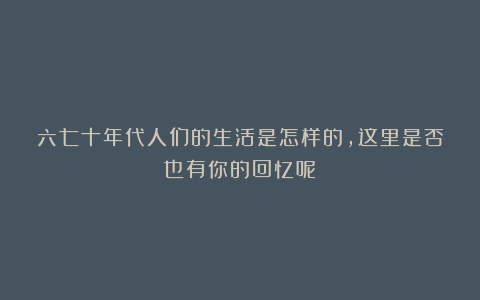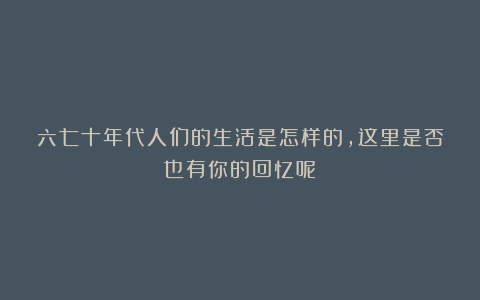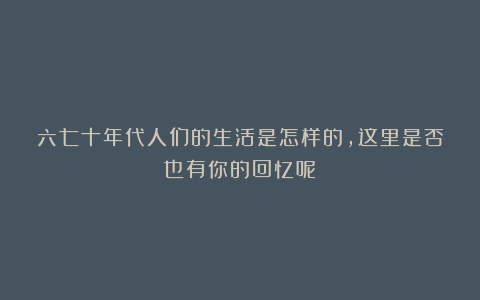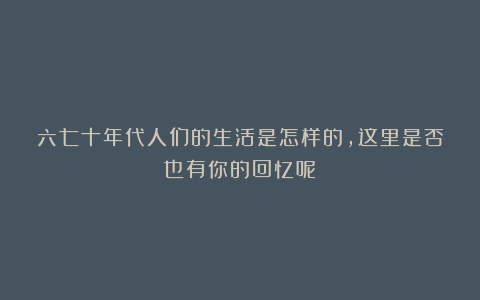
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因集体主义和物质条件的特殊性,留下了许多带着时代温度的记忆。这些事或许朴素,却深深烙印在亲历者的生命里,也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精神特征。
农村社员每天听着生产队的哨声出门,男人们扛锄头、挥镰刀,女人们拾麦穗、摘棉花,孩子们放学也会去地里 “捡遗漏”,凑够一定数量能换半分、一分工分。年底算工分时,全家围坐看账本,工分多的家庭能多分点粮食和现金,那是最实在的骄傲。
农忙时集体抢收抢种,全队人排着队插秧、割麦,地头有人送水送干粮,广播里放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累了就躺在田埂上歇会儿,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偶尔有技术革新,比如用牛拉犁代替人力,或试着用新式播种机,全村人都围着看新鲜。
城市工人常参与生产竞赛,车间墙上挂着 “比学赶超” 的锦旗,为了完成超额任务,大家自愿加班,晚上车间灯火通明,食堂会加一锅热汤面当奖励。师徒关系亲如家人,老师傅手把手教技术,徒弟端茶倒水、帮师傅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粮票、布票、肉票、糖票、肥皂票…… 每家都有个票夹子,夹着花花绿绿的票证。大人会把用不完的票攒起来,过年时换点紧俏货,比如用布票扯块红布给孩子做新衣服,用肉票买两斤排骨炖一锅,香气能飘满整个院子。
物资短缺时,关系很重要。邻居阿姨在供销社上班,会悄悄给相熟的人留一块肥皂;爸爸单位发了工业券,能换一辆自行车,街坊们会来围观,说 “你家运气真好”。这种人情往来没有功利,更多是能帮就帮的淳朴。
那时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很多家庭的梦想。小伙子结婚,若能凑齐 “三转一响”,比现在的豪车钻戒还体面。收音机里常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一家人围着听新闻、听样板戏,是最温馨的娱乐。
没有电子产品,孩子们自己创造快乐:滚铁环、打陀螺、玩弹珠。女孩子们则爱跳皮筋、踢毽子,嘴里念着 “马兰开花二十一” 的口诀,从白天一直能玩到天黑。春天在田埂挖荠菜、摘榆钱,回家拌玉米面蒸窝窝;夏天去小河摸鱼、爬树掏鸟蛋;秋天捡麦穗、摘野枣,揣一口袋甜滋滋;冬天在结冰的坑塘上打滑溜,或堆个雪人,用煤块当眼睛、红布条当围巾。
学校组织 “学农劳动”,孩子们去生产队拾麦穗,中午在农家吃饭,一碗红薯稀饭配咸菜,吃得香极了。“红小兵” 戴红领巾,列队唱《东方红》,去烈士陵园扫墓时,会偷偷把兜里的糖块放在墓碑前。
城市里的筒子楼、大杂院,一家做饭全楼香。张家包了饺子,会给隔壁李家端一碗;李家孩子没人接,王家阿姨顺手带到自己家吃饭。谁家买了新东西,全楼人会挤着来看,像过节一样热闹。
农村盖房不用找施工队,生产队会派工,街坊邻居自带工具来帮忙,男人们搬砖垒墙,女人们做饭送饭,孩子在边上跑跑跳跳,很快就能把新房盖起来。主人家只需管饭,一顿白面馒头配白菜炖肉,大家就吃得乐呵呵。
若谁家有人生病,生产队会派 “赤脚医生” 来看,邻居们会送鸡蛋、红糖;若遇灾年粮食不够,大队会调剂口粮,谁家有余粮,也会主动接济更困难的人家。那时的 “人情味”,是 “你有难,我搭把手” 的本能。
学雷锋、学王进喜、学焦裕禄是热潮。孩子们学雷锋做好事,帮老人挑水、扫大街;工人们学王进喜 “铁人精神”,再苦再累也咬牙干;干部们学焦裕禄亲民,下乡时和农民一起盘腿坐炕头,聊家常、问冷暖。
知青下乡时,背着行李唱着《知识青年之歌》,虽然条件艰苦,但很多人真心相信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会教老乡识字、帮生产队搞科学种田,夜晚在煤油灯下写日记,畅想未来的农村会更好。
那时的快乐很纯粹:分到新粮时的踏实,孩子穿上新衣服的雀跃,集体看露天电影的热闹,甚至只是雨后空气里的泥土香、夏夜院子里的蝉鸣。人们对物质要求不高,却对明天有笃定的期待,相信劳动能创造一切。
这些回忆,带着粗粮的质朴、汗水的咸涩,也带着人情的温度、理想的光芒。它们或许因时代局限而显得简陋,却记录着一代人在艰辛中彼此扶持、为集体奋斗的日子。对亲历者而言,这不是怀旧,而是生命里一段沉甸甸的时光 —— 那里有他们的青春,有不掺杂质的真诚,也有支撑他们走过风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