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暴风雨,漫山洪水,会冲刷走杂杂乱乱的尘埃粪垢乱石,但也会在山川间冲刷出一些深的浅的新的沟壑。
小小的李家堡,一场运动,竟死了两个人。谢九九实在是个狠人,生生把一个鸡鸣狗吠的农家院落弄成一座血腥凶宅。刘老宽心里哭笑不得,这个狠人竟留下一个荒唐遗嘱,送枕头,把个老婆托给自己。再一想,此人曾是怎样下了这个决定,确实,如把谢九九拉上台批斗,保不准也会有人用锥子刺的,他斤斤计较,不肯轻易助人的行为,一定民愤极大,早早了断,不失自尊。是明智还是胆小?刘老宽暗自叹息,这个悲剧其实本可没有的吧?
村中一有红白之事,多少年来,都请刘老宽管事。他虽不是村干部,但是,兄弟分家婆媳争吵,大多请他前来说合。在人们心中,这是个公道而有主张的老者。刘老宽与金叶主动帮助谢家料理谢九九的后事。一个新划出的漏网富农的丧事,很简单。家中财物,还是清点后没收了。空荡荡的墙上满是血手印的屋子,也没人敢住,丧事仍在这院子里,谢九九的两儿子各出些米面。他老婆夏美兰除了号哭外,什么主意也没有了。刘老宽出面请了几个人帮忙挖坟。三日后出殡。
村中已广泛传说着夏美兰给刘老宽送枕头的事,刘老宽从前的几个老弟兄见了他,都会问一句:“宽哥,瞌睡不?”老宽不好意思地说:“别开玩笑了,这是件伤心的事呀!你们不想想九九咋下了这狠心的!”王六小为人本分,他叹口气:“其实,九九脑子灵,把个富农分子老婆托付给一个好成分的男人,终会遮些风雨的!”老宽摇摇头:“要嫁就嫁远点吧!”
这个消息传到一个女人那里,她心一动:的确如此,这小九九的算盘真高明,自己一死,女人嫁个贫下中农,至少洗白了一半。先前,伪乡长王朝宗被镇压了,那小杏花嫁给了转业军人麻五,连儿子也改姓麻了。如今那日子过得比在王家还风光。嗯嗯……这一夜,地主分子孙秀莲一夜未眠。这一年,实在拖累了粉粉女婿了。尤其这四清运动里,五类分子经常在夜里开会,散会后,总是刘老宽背她回家的。儿子满仓一年回来一次,呆一个晚上便匆匆而去。孙子只在寒假回来,陪她过个年。将来会是怎样的日子呢?她有了一个主意了。
一九六五年三四月份,李家堡四清工作组撤走了,只留下一个叫何元宁的三十七八岁的队员,继续工作,有个名称叫:留守工作组。处理运动后的遗留问题。
其实,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老何是处理不了的。邢三小死了,邢家三亲六故从此仇恨上狄存娃这一门子人了。不是他那一拳,三小会自杀吗?谢九九死了,谢家这一干子三亲六故,自然也恨上了狄存娃为首的四清运动积极分子,人死鬼撺掇,就是他们白天晚上拼凑材料把九九划了个新富农。这让先前平和的李家堡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几条大裂缝。刘老宽是个善于思考的老农民,他反复思考这个运动的价值,土改,达到了均田,赢得了民心。公社化,国家掌控粮权。而四清呢?显著功效,整顿村政权的作风,但这声势有必要搞得如此浩大?又强化了阶层化,这乡村新的矛盾扩大了。
而且,人们从此有了“阶级”这个概念或烙印。同是一村人,从此分了等。就像社员的自留羊,合群放牧时,各家一定会给自家的羊身上做个标记。成分,成了社员的标记。在派工方面,也就有了明显差别。先前,掏厕所,清理猪圈这类脏活儿,刘家父子加倍工分,才能派出人手。而今,以狄存娃为头的新领导班子就省事多了,由地富反坏右去干就可以了。
于是,地主分子孙秀莲的好日子到了头,编织坊里,她不能容身了,队委会勒令她马上搬出编织坊。孙秀莲和刘老宽商量,刘老宽立即喜笑颜开:“好事,咱给满仓拍封电报,你就到后草地去。”刘老宽叫上儿媳金叶来帮忙整理东西。并去找狄存娃说:“等满仓来了,便搬家,拍了电报,恐怕也得三五日,狄队长,看能不能缓个三天五日的?”刘老宽作为个长者,无论是表情还是语气,十分谦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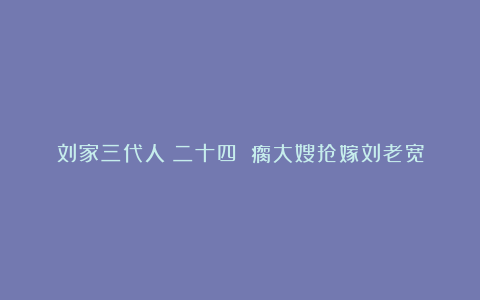
这时的狄存娃正在意气风发之际,作为经过运动洗礼后的新的村干部,处处表现出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的风范。确实,经过四清的如此清查,各地村干部作风面貌一新了,多吃多占之风戛然而止,干部欺辱女社员以及打骂社员的现象基本得到杜绝。
但是,这一批村干部有了一种“长官”意识,俗语: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先前刘家父子,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自己是替乡亲们的办事员,凡事不能对不起良心。而狄存娃他们是:我是一村一队之首,上听上级的一切指示,下呢?下面的社员都必须听我的。刘老宽一个全村威望最高的人,俯首请求,让狄队长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或自得。满脸笑意后,又板了板面孔:“可以缓个三五天,不过得抓紧!”
五天后,刑满仓吆赶着一匹大白马拉的小平车来到李家堡。刘老宽金叶都去帮忙,孙秀莲欢喜无比,大有当初初嫁人之感,从此后将与儿孙团聚,以享天伦之乐。
黎明时分忙碌,太阳将要升起,邢满仓要扶母亲坐上车时,孙秀莲推开儿子,却踉跄到刘老宽面前跪下了,并招呼满仓:“满仓,来跪下,这几年,多亏你姑夫照顾,不然……”说话间,泪流满面。刘老宽慌忙扶起孙秀莲:“胡话,这是胡话?他大妗子我扶你上车。”旁边的金叶也拉起满仓。
望着就要出堡的马车,刘老宽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几年,刘老宽为这个嫂子也费了不少劲,挑水劈柴不说,每次五类分子训话会,天气不好,都是他把瘸大嫂背去背回。
刘老宽抬头时,他不禁一怔,只见一群人围住了那搬家车。
狄存娃正把孙秀莲从车下揪,口中厉声喝道:“你个地主分子,竟妄想逃脱无产阶级专政!”
邢满仓拉着马缰,不知所措。刘老宽急忙走到狄存娃面前:“队长,能不能研究研究,你看满仓妈一个孤老婆子,腿又不给力,现在连个住处也没有,这……”金叶也想插话。狄存娃又瞪起大眼珠子:“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不能让地主分子孙秀莲从此逍遥法外!”又缓了一口气:“要么邢满仓你搬回来吧?”这时,孙秀莲又挣扎着爬上车,竟是笑着说:“我不走了。满仓,也不用回来!这样吧。满仓,你爹已死了三年了,你姑死了五年多了,现你姑父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就改嫁他了。满仓,送娘出嫁!”这个女人咬着牙齿说话。邢满仓哇地哭了。
车周围的人众,一时无话。晚春的大北方,早上仍是凉飕飕的。
从此,地主分子孙秀莲就嫁给小姑子的丈夫刘老宽。兄嫂嫁妹夫,比较稀少。初闻者,无比掩口发笑。当得知详情者,心善者,无不长叹一声。
下一节,叫刘老宽对天明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