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常永明
历史给我们留下一个谜,改朝换代很正常,夏商周……更替着变换着,政治制度土地分配诸方面发生变革是正常的必然的。人们头发,长短披卷,应该说与国家变革没什么重大联系,但与时政有了相关。远的不说,满清入关,男人扎辫子;民国革命,剪辫子。此中似乎有道理可讲。而到了现代,一九六六年夏秋了,又闹起头发革命了,实在想不通其中大道理。奋起破四旧,剪辫又复古。
当时,男人,大人要么光头,要么分头。小孩十二岁前,留齐眉小马鬃,如年画上的福娃。女的,小孩羊角辫;姑娘大辫子,一根或两根。当年龄大了,脑后盘个圆髻。实在想不通,这头发与革命有什么瓜葛纠结。
然而,从都市到乡野,又开始了头发革命。大井生产队男人们摧毁封建堡垒的同时,尤二英的革命队伍,正挨门挨户进行又一场革命。到了那一家,先查找旧物,古旧的陪嫁的梳妆盒,大红柜上的铜挂,刻了鸳鸯戏水图案的梳妆盒…当场砸个粉碎。女人当场就哭了,这是十几年几十年前娘家的唯一陪嫁物。铜挂件,则是主人闻讯后撬下收了起来。
到地主李忠的院里,革命掀起新高潮。这院子十分寂静,院内无鸡狗了。三间正屋,挂着锁但没有锁上。主人哪里去了?
这里有个隐秘事件,大约两个月前,一个寂寂人定后的夜晚,李忠老婆急性肠胃炎,李忠赶快叫来了刘老宽,刘老宽给十指放血,又将黑牛苦胆泡制的黍米粒给喝下一撮。李忠老婆胃疼有所缓解了。李忠便和老宽两人放心喝茶了。
老宽长吁一口气:“忠哥,从收音机里听到,恐怕又一个运动要来了。”李忠很坦然:“如今,咱要地没地了,就剩这处老房子,也没个怕的了,再说,咱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贫下中农的缺德事。”老宽笑了笑:“你们也老了,元礼虽说在咱本县,你们在,只能拖累他了。”李忠一怔,也是啊,四清后,由于家庭成分问题,元礼两口子被调到全县最荒僻的牧村教书了,半年回不来一次。老宽抿口茶:“正好,嫂子病了,好请假,不如到呼市看病,那里住处方便,元生可以照顾你们!”李忠老婆病情稳定了,插了一句:“老宽说得对,现在四类分子的义务工加大了,几乎天天夜里干活儿,我实在熬不下去了。”老宽很直接:“从前和你们李家有联系的政府老人,都不在当地了。先前那点情分还有谁会念叨?”
三日后,李忠请了假,因为到呼市,需公社批准。李忠跑了一天,总算有了着落。此日,老宽用一匹马拉的小平车,把从前的少东家老两口送到了县汽车站。
自此后,李家只剩下一处空荡荡的院子。而这所老房子,窗户则是独特的,一溜窗格,当初是卧龙山下最出名的老木匠雕刻而成,盘福字,寿字,游龙戏凤,二龙戏珠……
尤二英手一挥:“这是典型的四旧,砸了!”劈里啪啦,这曾经骄傲一方的老木匠毕生杰作,“粉身碎骨”了。据说,这位老艺人给李家做完这活儿后就卧病不起了。窗外的风,仿佛憋足了十分的好奇,呼地涌进去探寻屋中它早想揭示的众多隐秘。
其时,许多人家忙碌起来,赶快给自己雕了图案的窗户,在外又糊了一层白麻纸,把许多“封建主义”掩藏起来。
有女主人的,便当场剪了发辫,都是齐脖短发。时称“解放头”。马老三老婆梳有两根又粗又黑的辫子,被剪去后,两手捧着,泪恓恓地坐在檐下,马老三见了,笑着骂道:“张润兰,又不是剪了鼻子耳朵,看你……”说着,走到近前端详一番:“嘿嘿,像个女干部!”便俯身捋老婆的短发。润兰更是呜咽起来,其实,她为一向暴力的丈夫关爱而控制不住情绪了。这里有个道理,一般说,良家妇女她的一切打扮装束,只在意自己丈夫的喜好,即使赶个集市,着意梳妆,也只怕丢了丈夫的脸面。如果,为的是追求集市上的回头率,此妇便心旌摇晃了。这个性独特的马老三,要是以前,眼一横,上去一巴掌:“妈的,值得不值得!”而变了性子的马老三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转身回了屋内,几分钟后,出门走到饮泣的妻子面前:“孩他妈,你看我这样好看不好看?”润兰摸把泪抬头看时,不禁脱口哈哈大笑起来:“我的……妈呀,哈哈哈哈……”
原来马老三剃掉了眉毛:“这和你剪了辫子不一样?误了吃饭出气啦!”他说着满不在乎地朝外走去。把老婆一个人留在院里,自己笑得前仰后合,惊得七八只鸡呱呱乱叫……
马老三走上大街,人见人笑。马老三气昂昂地:“女人剪辫子,男人刮眉毛。这才叫男女平等。”人们必问:“谁给剃的?”马老三直往人堆处溜达,嘴里高叫:“咱们的尤二英同志亲自操刀!”这消息马上引起村中一阵动荡。正拆门楼的狄存娃放下手中工具,急匆匆寻找妻子尤二英,尤二英正带着队伍走向刘老宽孤独的院落去。狄存娃气吁吁赶上来拦住她:“上级有男人剃眉毛的指示?”二英子不解地:“没有啊,谁剃眉毛啦?”狄存娃一愣:“马老三,马老三到处嚷着说你剃了他的两道眉!”“胡扯淡,他是污蔑造反派,找他去。”
街心聚了一堆人,围着马老三笑闹不已。有人叹息道:“这是个啥运动,女人辫子剪短了,不难看。这男人少眉没毛的,咋看也不顺眼。”“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东汉时有过画红眉毛的赤眉军,这剃眉毛嘛,哈哈哈哈……”
尤二英气汹汹来了,大喊一声:“马老三,你胆大包天,竟敢污蔑我们造反派!到底是谁剃了你的眉毛?”
马老三卷着烟:“你啊!”
“什么时候?”
“就在今早上,你亲自给我剃的呀!”
“马老三同志!你大白天说鬼话,谁可作证?”
马老三呵呵笑道:“我那老弟摸你那一把,谁可作证?那是一个你一个他,这是一个你一个我,谁可作证?”这时满大街人哄笑了。尤二英一时语塞无语,狄存娃脸上挂不住了,大声呵斥:“正事还干不完,闲扯这些干什么!散了,散了!”
此时多家是闻风而动,自己先主动地“破”了起来。孙秀莲端详着乔金叶一头黑发,三十几岁的金叶,肤色尚好,春冬时节,最多抹上一点雪花膏而已。眼角浅现鱼尾纹,唇红齿白,别有风姿。一手持镜,一手攥着又粗又黑的发辫,眼溢上泪花,她想起母亲最后一次给自己结辫的情景了。
老宽正在房间整理东西,首先把摆放在一个古旧铜盘上的三颗石心(关帝庙泥塑中的)赶快收藏起来,放到地窝子里。出来看到金叶泪眼婆娑的,便说:“换个发型而已,大家都从桥上走,我们不能淌河过。”孙秀莲笑着说:“妹夫你过来,看我剪了发髻怎样?”老宽看了一眼孙秀莲,叹口气:“唉,管他呢,咱们人老啦,只求个没灾没病吧!”欲言又止……
下一节,叫老宽挥泪烧《三国》。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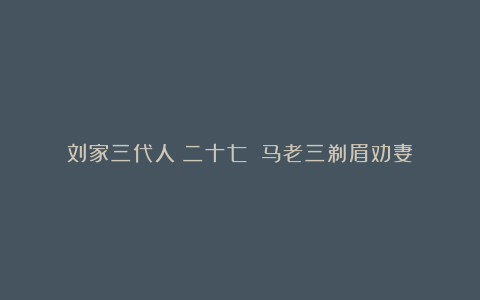
刘家三代人(十六):猫虎虎意外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