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微距摄影的方法,可以把握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鎏金铜晋式銙带的纹样、形制及金属工艺特征。通过加工痕迹分析,判断该例资料的主要部件系铸造成形,采用了合范铸造→錾刻→鎏金这一制作工序。在西晋中晚期的洛阳皇室附属作坊,晋式銙带的制作中出现了以平面呈三角形与凹陷的半球状痕迹为特征的錾刻技法。参考同类器物的出土状况,详细复原了该例资料的使用方式以及带头的纹样构图。
2011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工业路发掘了一座西晋中晚期的砖室墓(编号:ZSYM2,以下称郑州上街西晋墓),墓室填土中出土一套鎏金铜晋式銙带(ZSYM2:18)(图一;图二)。关于该例带具,2021年依据墓葬简报进行过探讨[1]。为进一步了解晋式銙带的特征,笔者于2023年5月对该遗物进行了调查。遗物现存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基于调查结果,本文拟对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晋式銙带的纹样、形制及金属工艺特征做详细分析,并整理相关认识。
图一 郑州上街西晋墓晋式銙带使用示意图
图二 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晋式銙带
一、出土概况
郑州上街西晋墓是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过道、耳室、后室组成的砖室墓,正南北方向,长约16米。甬道与过道均为券顶,前后室为穹窿顶。大部分遗物都出土于墓室填土中,难以把握准确的分布位置。仅确定后室东北处及中部偏东南处,分别出土一件陶空柱盘和陶碗。根据形制与出土遗物,简报判断墓葬的营造年代为西晋中晚期(图三)[2]。
图三 郑州上街西晋墓
该墓仅出土2件铜器,分别为博局镜(M2:19)(图三,7)及鎏金铜带具(M2:18)。出土位置不明。简报线图中晋式銙带的山形銙与胜形銙相间分布,可能反映了出土时各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
二、遗物特征
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的带具由带扣、带头、山形銙、胜形銙和䤩尾等部件构成,计14件(表一;图四;图五)。由于铜锈覆盖和残损,保存状态不佳。
表一 带具部件一览
注:()内为残存数值,-为难以确认。
图四 晋式銙带(1)
图五 晋式銙带(2)
(一)带扣
带扣1件(图四,2)。带扣是由边框、纹样板、台座、扣舌用铆钉组合而成的弧角长方形部件。边框在前端中央有一处铆钉孔,铆钉缺失。边框上下端各有1枚钉帽缺失的铆钉,铆钉处施以浮雕风格的胜形纹样。边框后端上下角留有L字形的平坦面,各有1枚铆钉,钉帽缺失。边框局部残存有鎏金。边框多处断裂,右上角残存纺织物痕迹,纺织物经纬分明。
纹样板是施以纹样构图的金属板,平面为前弧后方的长方形,前端留有用来穿过带鞓的扣孔。纹样板上侧略宽于边框,残损严重,经拼合后可辨别纹样构图。纹样板左侧为振翅向右的禽鸟,翅膀表面有绵密的錾刻痕迹。纹样板右侧为朝左的龙,颈部及头部残缺,躯干有錾刻痕迹。纹样板背面有质地坚硬的不规则凸起,并非铜锈。由此推测纹样板系铸造成形,不规则的凸起则是浇铸时铜水在铸范中流动不良的结果,抑或是铸范的型腔不平整所致。同样的保存环境下,纹样板表面并无凸起,由此推测表面在錾刻纹样前进行了研磨修整。
楔形扣舌用细铜轴固定在台座上,台座用两颗大头铆钉安装在纹样板前方。
(二)带头
带头1件(图四,1)。平面呈前弧后方的长方形,由边框和纹样板用铆钉组装而成,前端残损。边框的形制特征与带扣边框相同,锈蚀严重。纹样板表面覆盖一层纺织物痕迹,可以辨认出经纬。没有纺织物痕迹覆盖的地方显现出鎏金与錾刻痕迹,背面没有鎏金。錾刻痕迹由平面呈三角形的痕迹首尾相接组成,似也有其他形状的錾痕,但因锈蚀难以确认。纹样板背面的不规则凸起与带扣纹样板相同,系铸造成形所致。
纹样构图为躯干呈 C字形的蟠龙纹,角、牙、爪等部位均可辨识。
(三)山形銙
山形銙5 件(图四,3~8)。该类部件由銙板与垂饰组成,其中垂饰由边框和纹样板用小铆钉缀合而成。5 件个体的銙板在形制特征上基本相同,但纹样构图各异。銙板底端伸出 3 个倒钩,穿过垂饰后折叠用铆钉固定。主要纹样为龙纹,躯干造型呈 C字形、S 字形或螺旋状,遗物保存状态不佳。
銙1出土时,銙板与垂饰的表面向内折叠(图四,3)。銙板与垂饰的背面均有不规则的凸起,纹样轮廓边缘有范线(图七,1),推测部件是铸造成形。垂饰背面边缘保存着鎏金,此外还附着一层薄薄的靛蓝色颜料与纺织物痕迹,颜料性质不明。
銙2的垂饰残损过半,銙板的龙纹躯干呈逆 C字形,龙纹的角、牙、尾、爪等部位均用錾刻线条描绘出纹样细节(图四,4)。线条是用平面呈三角形的錾痕首尾相接形成的,錾痕里有鎏金,表明先錾刻纹样细节再鎏金。根据不规则凸起和范线,推测属于铸造成形。因此该部件大致的制作工序是铸造→錾刻→鎏金。龙的尾部有连续的凹陷半球状纹样(图七,4),与日本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藏带具的山形銙类似(图六,3、4)[3]。纵观迄今发现的晋式銙带资料,半球状纹样一般仅分布在带扣与带头的龙角或龙尾处,山形銙上錾刻半球状纹样的案例较为少见。銙板与垂饰表面均附着有纺织物痕迹。表面鎏金,背面无鎏金痕迹。
图六 日本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收藏晋式銙带
图七 晋式銙带加工痕迹
銙3的表面,与銙1垂饰一样附着一层靛蓝色颜料(图四,5)。锈蚀严重,难以辨认銙板表面錾刻痕迹的加工技法。背面有铸造留下的不规则凸起。垂饰施以躯干呈逆C字形的龙纹,用平面呈三角形的錾痕表现出纹样细节。整个部件表面鎏金,背面仅边缘鎏金。
銙4表面覆盖铜绿,背面覆盖一层纺织物痕迹(图四,6、7)。整个部件表面鎏金,銙板背面仅边缘鎏金,垂饰背面的边缘和中央局部有鎏金。
銙5残损严重,銙板残件表面确认有凹陷的半球状纹样与纺织物痕迹(图四,8)。垂饰边框的鎏金保存较好,右上部和底部中央有细小的铆钉。垂饰的纹样板残损近半,表面和背面均附着有较厚的纺织物痕迹。垂饰背面有不规则凸起,系铸造痕迹。
(四)胜形銙
胜形銙6件(图五,1~8)。胜形銙由銙板与垂饰构成,大都为表面瑬金。銙板四角各有1枚大头铆钉,中央用小铆钉将棒状部件固定于銙板上。棒状部件较厚,横截面近似半圆形,用来防止銙板发生形变。棒状部件的两侧,施以对称的三叶纹,纹样边缘有一圈錾刻痕迹。銙板底部伸出T字形倒钩,用来悬挂垂饰。根据垂饰的形状差异,可分为心形垂饰与马蹄形垂饰。
銙6(图五,1)锈蚀严重,难以观察表面的錾刻痕迹。銙板虽有裂痕,但基本保存较好,垂饰残损过半。部件附着有纺织物痕迹,特别是垂饰背面的经纬纹路清晰可辨。銙板背面有薄薄的一层靛蓝色颜料。銙板背面有铸造留下的不规则凸起,并且在三叶纹处因浇铸时铜水溢出型腔,导致三叶纹和銙板边缘粘连在一起。铆钉脚穿过銙板后,在背面用片状垫圈防止铆钉脱落。
銙7(图五,2)保存较为完整,左上部有缺损。銙板表面局部有一层靛蓝色颜料,因锈蚀和纺织物痕迹,难以辨别錾刻痕迹的加工工艺。銙板背面的棒状部件铆钉处,有铁锈痕迹。垂饰表面錾刻有水波纹,难以辨识錾刻工艺。垂饰上端有长方形穿孔,肩部和内侧有单叶纹和半圆形凸起,最内侧有三叶纹。
銙8的銙板表面在纺织物痕迹下,鎏金保存完整(图五,3)。纹样细节为平面呈三角形的錾刻痕迹相连而成(图七,3),錾痕里鎏金保存完好,推测先錾刻后鎏金。左下部的三叶纹因铸造时铜水溢出型腔,使得三叶纹和銙板边缘粘连在一起。銙板背面棒状部件铆钉处,有铁锈痕迹。铆钉脚穿过銙板,在背面用片状垫圈固定铆钉。T字形倒钩的表面,有纺织物的经纬痕迹。马蹄形垂饰较厚,两面均有鎏金和纺织物痕迹。垂饰的表面有錾刻纹样,难以辨识加工工艺。垂饰表面附着有山形銙的垂饰残件,包括边框和纹样板。
銙9仅存銙板,鎏金剥落严重(图五,4、5)。可以观察到三叶纹周围的錾刻纹样,碍于铜锈难以确认錾刻技法。底部倒钩表面残存纺织物痕迹。銙板背面有不规则的凸起,推测该部件系铸造成形。铆钉脚处有片状垫圈。
銙10(图五,6)与銙11(图五,7、8)仅保存銙板局部,其中銙10的棒状部件缺失。表面和背面均覆盖铜锈及纺织物痕迹,并附着有靛蓝色颜料。从不规则的凸起来看,部件系铸造成形。
(五)䤩尾
䤩尾 1 件(图五,9、10)。由一大一小两件圭形铜板构成,均为用一片铜板折叠而成的双层构造。小型铜板中部装饰双叶纹,用3枚铆钉缀合。大型铜板施以双叶纹与三叶纹,残存4 枚铆钉。两面皆有錾刻纹样、鎏金与纺织物痕迹。錾刻的线条由平面呈三角形的錾痕连接而成,镀金保存良好,推测是先錾刻后鎏金。
三、认 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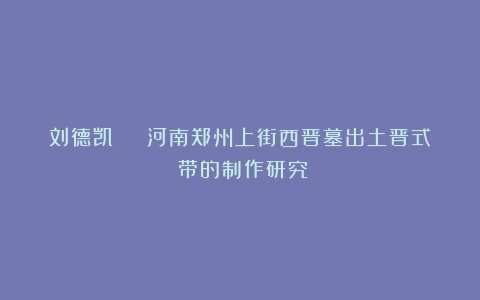
先行研究依据纹样构图等特征,对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晋式銙带的时空定位做了探讨[4]。并认为该例资料与辽宁北票喇嘛洞Ⅱ M275 鲜卑墓、韩国金海大成洞88号坟出土晋式銙带同属于西晋中晚期,制作地是位于洛阳的皇室附属作坊,反映了西晋中央与慕容鲜卑及金官伽耶首长层的政治关系[5]。通过观察实物可以进一步把握该例带具的特征,对上述既存认识进行反思与拓展,尤其是加工痕迹所见制作技术。
本次调查,对该例资料的制作技术特征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由不规则的凸起与范线等加工痕迹(图七,1、2),推测该带具的主要部件系铸造成形,制作工序为合范铸造→錾刻→鎏金。二是制作过程中,使用了平面呈三角形与凹陷的半球状痕迹这两种錾刻技法(图七,3、4)。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晋式銙带为了解西晋皇室附属作坊的金属品制作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与该例属于同一作坊内制作的韩国金海大成洞88号坟晋式銙带[6],在錾刻技法上也是有三角形与凹陷的半球状痕迹两种(图七,5、6)[7]。就迄今为止所调查与详细公布的晋式銙带而言,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西晋中晚期洛阳皇室附属作坊所生产的晋式銙带,在錾刻技术上倾向于使用以平面呈三角形与凹陷的半球状痕迹为特征的加工技法。这两种錾刻技法,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也有出现。
其次是关于该例带具在使用时的形态复原问题。带扣的系结方式虽然大体相同,但每一套晋式銙带在部件数量和形制上存在些许特异性。该例资料有5件山形銙与6件胜形銙,按发掘简报中线图所示,山形銙与胜形銙相间分布。各种部件组装在带鞓上后,䤩尾从上往下穿过带扣的扣孔,这样不会遮挡带扣纹样。带鞓绕过腰际,将䤩尾折叠后倒插在后腰(图一)。䤩尾的使用形态复原依据是同类器物的出土状况,如广州大刀山东晋墓[8]、辽宁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晋式銙带[9]在出土时带扣、带头与䤩尾粘在一起,且銘尾均为折叠状态。参考《新唐书·车服志》:“腰带者,搢垂头于下,名曰䤩尾,取顺下之义”[10],可知䤩尾应该是朝下垂在后腰。以北宋对唐代服饰的记载来复原西晋时期的带具并不可靠,但在没有描绘晋式銙带的壁画、陶俑、文献记载的状况下,《新唐书》可为䤩尾使用形态提供一定参考。
其三,关于带头纹样构图的复原。带头的纹样板破损,残存的纹样构图是旋回的蟠龙纹(图八)。迄今所见东亚地区出土的晋式銙带中,仅有4例带头的纹样构图为旋回的龙纹,此外3例为北票喇嘛洞ⅡM275墓例[11]、香港梦蝶轩藏GI-017b例[12]、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出土A-642例(图八)[13]。从蟠龙各部位的构图进行类比,推测郑州上街西晋墓例的带头纹样同样为两条旋回的蟠龙纹。带头是两条旋回的蟠龙,带扣是禽鸟与龙相对的纹样构图,在目前所有带具资料中仅有该例与北票喇嘛洞Ⅱ M275墓例。根据纹样细节与形制特征的共通性,更进一步证实两者系同一作坊生产。
图八 蟠龙纹带头诸例
四、小 结
晋式銙带在3-5世纪初广泛分布于东亚各地区,对把握该时期的地域间交流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限于资料的公布情况,中、日、韩的既往研究只能着眼于遗物的纹样与形制特征,而难以触及作为金属制品的晋式銙带的工艺特征。魏晋时期的金属工艺与生产体制等课题,受资料制约长年难以展开研究。因此对考古资料进行详细观察,利用微距摄影捕捉的加工痕迹进行金属工艺上的分析,正是本次调查研究的意义所在。
通过资料调查,本文详细观察了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晋式銙带的纹样、形制及金属工艺特征。该例资料的主要部件系铸造成形,大致的制作工序为合范铸造→錾刻→鎏金。在西晋中晚期的洛阳皇室附属作坊,晋式銙带制作中出现了以平面呈三角形与凹陷的半球状痕迹为特征的錾刻技法。参考同类器物的出土状况,详细复原了该例资料的使用方式以及带头的纹样构图。
附记:近些年进行资料调查,给各方添了不少麻烦。本文所用资料的实地调查,得到武汉大学王然、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建和、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楚小龙、辽宁省博物馆张力、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霞、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上野祥史等诸位先生的鼎力相助,兹致谢忱。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刘德凯:《郑州上街西晋墓出土晋式銙带研究》,《中原文物》2021年第4期。
[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郑州上街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2期。
[3]〔日〕諫早直人:《古代東北アジアに书ける金工品の生産と流通》,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2018年,第19页。
[4]同[1]。
[5]刘德凯:《魏晋时期晋式銙带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0期。
[6]韩国大成洞古墳博物館:《金海大成洞古墳群—85호분 ~91호분—》,金海市大成洞古墳博物館,2015年,第95页。
[7]〔韩〕金跳咏:《》,《》,2020年第117辑,第49页。
[8]刘德凯:《广州大刀山东晋墓发掘回顾与探讨》,《四川文物》2024年第5期。
[9]a.田立坤:《论带扣的形式及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b.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10]《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车服,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页。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燕文物精粹》,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71页。
[12]Julia M. White, Emma C. Bunker,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Denver: Denver Art Museum, 1994,p.132.
[13]日本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集:《古墳関連資料一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资料図録8》,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2012年。
作者:刘德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文物季刊》 2025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