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鲁迅的仙台叙述,既重要又争议颇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都众说纷纭。然而,叙述并不等于记忆,而记忆也不等于客观的史实。仙台进入文学文本之中,至少存在“仙台记忆”与“仙台叙述”两个不同层面,它们各自盘旋在鲁迅精神世界的多种维度上,既有联系也有分野。作为语言文学的“仙台叙述”充满张力,在鲁迅一生的文学追求中十分重要,属于鲁迅文学思想基本构形的基点。
■
关 键 词
仙台叙述 鲁迅思想 复义
鲁迅就读仙台医专时的教室
从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鲁迅在仙台生活、学习了大约一年半,这一段并不太长的日子却成了尽人皆知的“鲁迅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所谓“弃医从文”的历史性转向,所谓“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蒙”的开启都根源于仙台的体验。仙台之于鲁迅人生与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有了“仙台神话”的概括。
然而,就是这一段重要的文学经验,却一直充满了质疑与争论。归纳起来,意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鲁迅仙台叙述的真实性,二是鲁迅仙台经验的重要性。这两个问题在事实上又是相互联系的,在过去的鲁迅认知史上,正因为仙台的一系列经历——包括“幻灯片事件”“泄题”风波真切到铭心刻骨,才深深地激发了鲁迅弃医从文、疗治国人灵魂的重大选择,也就是说,真实性加强了重要性,如果真实性变得虚幻动摇,是不是也会挑战仙台经验的重要性呢?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真实/虚假这样简单,仙台进入文学文本之中,至少存在“仙台记忆”与“仙台叙述”两个不同层面,它们各自盘旋在鲁迅精神世界的多种维度上,既有联系也有分野。作为语言文学的“仙台叙述”充满张力,在鲁迅一生的文学追求中十分重要,属于鲁迅文学思想基本构形的基点。
藤野先生
一
对于鲁迅仙台叙述的真实性的质疑,最早来自日本重要的鲁迅学者竹内好。早在1944年出版的《鲁迅》中,他就尖锐地提出:“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1]竹内好的质疑主要还是基于他对鲁迅文学价值基点的理解,在他看来,作为个人主义的、对虚无有着深刻体验的鲁迅才是文学世界中最独特的存在,是他所首肯的“回心”,而鲁迅真正的“回心”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北京抄碑帖的时期,仙台故事中的民族性关怀与思想启蒙多少有点缥缈不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柢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2]
日俄战争幻灯片
如果说,竹内好是从他所认定的思想重要性的角度反过来质疑仙台叙述的真实性,那么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则是从实际考证入手,对鲁迅所叙述的仙台体验的细节提出了大量的疑问。从半泽正二郎、仙台鲁迅会在1966年查证细菌学教授石田名香雄当年的德国制幻灯机、幻灯片,班级总代表铃木逸太1974年对“泄题”事件的回忆,到1978年2月日本平凡社出版由“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编写的调查报告等,都在不断披露《〈呐喊〉自序》《藤野先生》中的细节真实问题,包括反映国人麻木不仁的幻灯片、表现异族歧视的“泄题”事件的过程,当然也延伸到更多的生活事实,如仙台并非没有中国留学生,鲁迅还和浙江老乡施霖同舍同合影同校址,鲁迅隐去施霖,也隐去了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敷波重次郎教授,对于恩师藤野先生,也可能隐去了内心深处的某些不满……总之,鲁迅的仙台叙述充满了不少难以确证的内容,甚至因此遭到了文体上的根本质疑——这并不是真实叙事的回忆性散文,而是有较多虚构的小说。
被隐去的同乡施霖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中日学者表达了充分的理解。日本学者吉田富夫将鲁迅的这一手法称作“体验的集中”和文学的“象征”,[3]中国学者廖久明则从细致入微的考证入手,一一澄清了这些细节瑕疵中足以令人认可的写作状态,尽力恢复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作家鲁迅的追求。[4]不过,质疑者和辩护者都还是基本笃信文学表达的“真实性”原则,只不过,质疑者觉得鲁迅的叙述存在某些不尽真实的成分,而辩护者则断定目前所达到的真实已经没有挑剔的必要了。至于作为鲁迅的文学,如此亦真亦假或者说真中带假的叙述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追求和价值,似乎都还没有进一步展开。
竹内好,第一个质疑“仙台叙述”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考察是以思想的发掘而不是以文献史料的考证与辨析见长,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位思想者,却在提出传记质疑的时候出现了对仙台叙述的这样一个判断:“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5]竹内好承认了“幻灯片事件”之于鲁迅创作的意义,但是他还是将“事件”视作一种客观的经历,而不是渗透了鲁迅思想与情感的自我意识的生长,是鲁迅对自我文学追求的一种重要的“叙述”。
幻灯机
在过去,我们倾向于将人的经历、遭遇和人自身的思想意识、情感状态严格区分开来,前者被视作纯粹客观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而后者属于人主观的内在的精神感受。其实,所谓客观的社会遭遇本身是无法陈述的,它们最终能够被记录、被表述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人的精神感受的一部分了。在人自我表述出来的人生经验之中,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社会“事件”,也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记忆”,所有的“事件”都不过是被人截取和转述出来的一部分,所有的“记忆”也都从属于自我“叙述”的结果。这已经在20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威廉·詹姆士说过:“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经验领域,这个经验领域是直觉地被认为是精神领域而且是(并且被感觉到是)完全由意识作成的,它在性质上同被物理的东西所享有那种填满空间的存在不一样。”“本身是同一的实有的东西有可能像这样地在不同的结构里具有不同的功能,这是极其纷歧复杂的关系网的一种自然的结果,我们的经验就在这样的复杂关系网中。”[6]
换句话说,我们经由《〈呐喊〉自序》《藤野先生》《自叙传略》等文字所获知的“仙台故事”归根结底就是鲁迅对自身经验(或者说特殊体验)的一种记录,这种记录不会也不可能是纯粹客观事件的实录,自然不应该与其他当事人的经验叙述完全一致,它们本身已经渗透了鲁迅本人的心理感受,也传递着鲁迅自己在后来“再叙述”之时的自我评估和精神追求,是客观经历与主观体验、过去与当下相互结合的“复杂关系网”。
鲁迅在仙台居住过的地方
至于这样的“叙述”究竟属于“散文”还是“小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要紧了。散文素来以“真”自诩,然而文学之“真”本来就不等于是客观的实录,而是主体体验的真切;“小说”理当“虚构”,但虚构的文学恰恰也是为了更好地破除接受的迷障,以幻致真,传达深沉的真相。单纯囿于“真实”之说已经不能概括散文与小说的本质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写的作时代,纷繁复杂的文体观念正在中外融会中聚集,中国传统的“大散文”传统,小品文的流绪,西方的essay,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小说”呢,从班固眼中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到千年流转的史传传统,直至晚清“小说界革命”、五四新文学的主流,历史发展风云际会,跌宕起伏,鲁迅出现在现代文学文体的多样化生成年代,“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本来就是他自觉尝试的取向,[7]我们又岂能用规范后的现代文体观念来约束一位开创者的视野和襟怀!
二
鲁迅的仙台故事是他远离仙台种种“事件”近二十年之后的叙述,此时此刻的鲁迅,历史的沧桑与现实的际遇交织在一起,让他对自我、对世界都涌现出万千感慨,这无疑将转化为对既有经验的提炼、组织、强化或者削弱;已经穿梭于新文学文体实验的他也将自如地运用多样化的“叙事与抒情”来自由表达精神的感受,从记忆到叙述,其中的迁移和改变可谓理所当然,否则也不会呈现出一个独特的灵魂,一个崭新的文学精神的世界。正如法国生命哲学家也是文学家的亨利·柏格森对意识、记忆的分析:“我把我的意识作为受情感支配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意识以感觉或情感为形式,对当前的形象作出反应,作用于我自认为的起始动作中的所有步骤,一旦我的行动变为自动的活动而表明不再需要意识的时候,它就立刻淡化而消失了。”“所以,意识的确为宇宙及其历史增添了一些新的东西。”[8]“如果存在记忆(即存活下来的以往形象),那么这些形象肯定会不断地与我们的当前知觉混合在一起,甚至会取代当前知觉。因为如果它们存活下来,那它们的目的就在于应用;它们在每一个瞬间都参与完成我们的当前体验,用已经获得的体验丰富当前的体验。”“记忆只有通过在它介入的间隙中将某种知觉借用为其实体,才能变为切实的记忆。知觉与回忆这两件事实经常互相渗透,而且始终在通过细胞浸透过程来交换各自性质中一些东西。”[9]
鲁迅所叙述的仙台故事与其他经验者的故事有着差异,重要的不是通过其中的差异寻找所谓历史事实的“真相”,也不是对鲁迅时过境迁的记忆状况有所“理解”的问题,我们就是应该以这样的文本形态为基础,体察鲁迅思想情感的构形特点。我们所谓的文学研究归根到底不是辨析实际生活在文学文本中被呈现的真实度和完整性,而是已经完成的构形究竟有什么特点,在相应的文学精神史上它们作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贡献。不仅是虚构的小说,就是包含了人生“真实性”的散文甚至日记其实也属于这种“建构”的产品,只不过,建构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而已。因此,阅读这样的文本,应该改变一个基本的思路,即不是索隐“这个人”(作家本人)的人生事迹,而是探究由这样的文本形态出发作家实现了怎样的精神塑造,这里的“成功”不在于究竟多么真切地反映了作家真实的经历,而是提供了多少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精神样本——当然,这不等于说仙台记忆的真实性完全不再有关心的价值,而是说,这里关于真实性的把握更需要与鲁迅的叙述联系起来,观察他如何叙述其中的“真实”,或者有意无意地改变了某些“真实”。总之,鲁迅的叙述本身更需要解读和剖析,这是我们最终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关键。
在鲁迅的叙述中,那些从漫漫人生中被抽样记录的部分承载了值得深究的思想情感内涵,而其中被调整被改编的部分可能恰恰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指向。
细菌学教授石田名香雄的幻灯片中究竟有没有鲁迅所描述的那一张,这可能并非我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幻灯片可能就在尚未现身的5张遗失的片子中,但更可能属于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的意象迁移,当时的仙台四处都是热烈的战争庆典场景,令鲁迅无法回避:
战争期间,在仙台市市长早川智宽的组织下,前后举行了五次市民祝捷大会: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八日,第一次陆海军祝捷大会,庆祝日军占领九连城的胜利,有市民五千余人参加,市内各校师生一万余人游行祝捷;九月六日,第二次祝捷大会,庆祝日军占领辽阳,有六、七千人参加;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五日,第三次祝捷大会,庆祝日军占领旅顺,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三月十五日,第四次祝捷大会,庆祝日军占领奉天,有五千余人参加;六月四日,第五次祝捷会,庆祝日本海海战大捷,全歼俄舰队,有一万余人参加。
这些与日俄战争有关的情况,都发生在周树人身边。……全市充满祝捷气氛,各家各户都挂旗庆祝胜利。
……
五月二十七日进行日本海海战。三天后的三十日,医专举行了“海军祝捷大会”。下午三时开始,在校园举行祝捷仪式后,在市内举行了举旗游行,游行队伍里举着校旗战胜旗,在祝捷进行曲的伴奏下从大门出发,从市内东北方第四连队驻地到西边的川内师团司令部驻地,从东至西游行一遭,然后登上仙台青叶城旧址天守台,高呼“万岁”三次后解散。[10]
仙台《河北新报》上的图片
鲁迅将当时在仙台所获得的日俄战争的零散印象(课堂、校园、市街、报纸等)攒聚在一起,构建了自己对这场战争氛围的最具震撼力的叙述,包括同班同学的“万岁”呼喊,也包括身为中国人目睹同胞猥琐表现之时的悲愤与尴尬。比照同学铃木逸太记忆中安静有序的观影过程,对于历经人生波折、遭遇种种人性悲剧的1920年代的鲁迅来说,则更可能处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心境之中,异族的“万岁”之声生成于精神世界的深处,周遭国人的沉沦更是挥之不去的影像,这张幻灯片早已经定格在鲁迅的脑海里了。对于文学艺术的表现而言,真切地传达体验者的主观感受其实是最难的,朴素地刻绘当时的“耳闻目睹”往往并不足以再现那种强烈的情绪体验,因为阅读时刻的情景已然不同了,如何在平静的阅读中“重建”感受的深刻,形成必要的冲击效应,是每一个杰出的作家都在认真处理的重要问题。
关于“泄题”风波,日本同学的追忆简明平和:班级总代表铃木逸太和同学们有理有节地处理了这件事。是铃木首先将漏题的“谣传”求证于藤野先生,并立即得到了澄清,又“把大家集合起来”解释,同时,“什么也不要对周先生说”,仿佛事情就云淡风轻地一掠而过了。[11]鲁迅的叙述则曲折起伏,包含了一系列的枝节,充满了公开的与心底的矛盾冲突。首先是学生会干事召集同学大会,在黑板上刻意勾画“漏题”之“漏”字,以示讽刺;然后“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径直入室检查笔记;接着又收到了匿名信,勒令“你改悔罢!”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将事情禀告了藤野先生;最后,有幸得到“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的帮助,终于澄清真相,平息了风波。显然,鲁迅在这里生动地揭示了生活中的耻辱和伤害,这是自“家道中落”以来,少年鲁迅在世态炎凉中开启人性观察的延续,既切合当时留日中国学生“读西洋书,受东洋气”的普遍心理氛围,也从属于鲁迅在人性体察中寻觅文学之路的既有逻辑,是20世纪初年的真切体验,也是1920年代业已成形的人生观照方式。而且,鲁迅就是在这一段个人耻辱的基础上引出了“幻灯片事件”,民族的耻辱和个人的耻辱交织在一起,烘托出了从医学知识的课堂上出走,转入人类和个体精神世界考察的必要: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12]
就是在如此耻辱的个人体验中,鲁迅为我们引出了“幻灯片事件”——民族耻辱的主题,显然,这是一种极具文学感染力的思想情感传达,作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可谓是匠心独运,在文学之真的向度上,再纠缠于絮絮叨叨的细节过程,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
透过“幻灯片事件”与“泄题”风波的鲁迅式叙述,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所述仙台经验的重要性。其实,这两大重要事件在有机关联中的连续叙述,构建起了鲁迅个人-民族体验的不可替代性。
学界的考证也曾发出疑问:鲁迅对于国民性的关注和探究,并不是始于仙台时期,早在第一次东京求学之时,他就常常与许寿裳探讨“理想的人性”,[13]也对清国留学生的行为举止颇多不满,自我放逐到偏远的仙台就是离群索居的一种选择。那么,为什么还要如此强调仙台的种种事件让他“弃医从文”,走上“改造国民性”的道路呢?至少在竹内好这样的学者看来,这样叙述的文学理想过于“功利主义”,难以令人信服,也不及后来北京沉默时期的“虚无”感更具有“个体”的深度。然而,竹内好认定鲁迅的北京沉默是他所谓的“回心”,这样的判断归根到底还是基于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历史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他们试图在“回心”中强化日本的主体性,以摆脱二战失败后日本之于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而“抉心自食”的鲁迅被视作“回心”,刚好是充当了日本批判的一面借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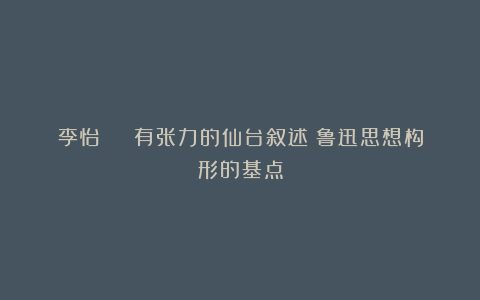
这样的逻辑击中了日本历史文化的症结,但也误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验和选择。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面临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需要在学习西方文化中自我更新,另一方面也需要摆脱被殖民的危机,重建独立的自我。在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自我的道路上,首先需要解构和重组的便是自我与家国的关系。因为,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格局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自我精神的成长,也阻碍了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发展。对于现代中国的启蒙文化而言,首先要重建的便是个人与自我的思想,但同时也需要重建国家民族意识。可以说,个体意识与国家民族意识的共同生长就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每个知识人必须严肃面对的现实。在竹内好的观念中,“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也就是我所谓的“泄题”风波),一个属于国家,一个源于个体,差异甚大,很难理解它们如何相互结合,因而颇觉牵强,但事实是,在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双重危机中,像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恰恰准确地感受到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刚刚结束了“泄题”风波之后,鲁迅“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这个“接着”如此顺滑如此流畅,这不是叙述的强制逻辑,而是心理感受的同一性逻辑,这是鲁迅的个体之痛,也是他作为民族一员不得不承受的群体认同之痛。仙台之前,他对国民性的观察是有距离的,来自理性的审视;因为仙台,所有的人性故事都切近到了自己的身边(如唯一的浙江老乡施霖),也波及自我的命运,多重焦虑的袭扰无疑激发了鲁迅关于自我、人生、命运以及文学选择的强烈感受,比起以前的任何一段经历和遭遇,鲁迅都更加看重仙台体验的集中和强烈,以及推动他个人选择的决定性意义。因此,仙台叙述之中就包含了鲁迅人生转向的最重要的信息。
三
鲁迅的仙台叙述不仅内蕴着人生取向的最重要的体验和密码,而且还呈现着他思想构形的基点。这就是一种“有张力”的叙述的基本特征。
所谓“有张力”,指的是在文学的叙述中不是传达某种单一方向的思想情感,而是多种意识和情绪的混合,而且这些思想和情绪常常还不是相安无事地并存,很可能处于相互抵牾、矛盾甚至冲突的状态,有张力的文学叙述包含了作家对自我和世界有多重的感知和体验,他努力通过复义的叙述保留这些多重体验,从而为未来的精神走向预留广阔的空间。
鲁迅所叙述的仙台体验原本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留学生与日本生存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跨国别跨民族的生存体验;二是作为中国人对自身特别是对在日中国同胞的交往体验。两个方面的叙述都显得格外纠结和复杂,难以用单一的语言来简略概括。
鲁迅和他的日本同学
在第一个方面,鲁迅叙述了留日学生最普遍的生存感受:敏感、紧张和耻辱。从“泄题”风波到“幻灯片事件”,这是我们读到的印象深刻的核心内容。与留学英美的见闻有别,日本刚刚完成了国家地位的翻转,作为亚洲近代化势头强劲的国度正直线上升,反过来战胜了昔日的文化中心——中国,那种以强凌弱的气势对两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在被抛入异国他乡之后,个人与民族意识都不得不重组,一时间难以适应。郁达夫的深切体会是:“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利争权的黄帝之子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一国去住上两三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14]
只不过,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处理和叙述这一共同感受的方式还是有所差异的。更年轻的如创造社一代一般都将异域的压力直接化为倔强的自我肯定,而将责任推及国家的落后,个人仅仅因为国家的落后而背负了历史的重担,这是一种伊藤虎丸所说的“屈辱”体验[15]。郁达夫在《沉沦》中高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这里有“泪浪滔滔”的委屈,却没有多少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复杂感受。鲁迅的不同就在于同样的敏感和耻辱体验中,他也发现了异族的共同人性,感受到了他者的真诚和温情,这就是来自藤野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16]鲁迅所叙述的藤野先生展开了现代民族关系的另外一重维度,它和国家间的竞争、族群间的心理隔阂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复杂性。
在第二个方面,对于民族自身的思想情感表达同样也是多维度的。在多种关于仙台的叙述中,鲁迅都一再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本民族同胞的批评。那些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为了掩饰文化的差异而打扮得奇形怪状,这是自我精神迷乱的写照:“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17]逃离东京远赴仙台,就是“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18]。然而,仙台也有他所熟悉的“中国主人翁”[19],即便合影,并且同住一舍,也不愿提及。意外出现在幻灯片中的同胞,却“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20]。但是,这样的批评并没有造成他丝毫精神上的优越感,因为,在自我精神的深处,恰恰是一种深切的民族认同,他以改变民族的现状为当然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1]所以说,“鲁迅从留日初期开始就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精神在他这里未能与现实生活中对国民的认识统一起来。相反,二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热爱祖国却厌恶某些同胞,国家与国民因此无法获得同一性”[22]。
鲁迅的矛盾性还体现在他继续反思和追问着这样的民族意识的不确定性,他多次叙述教室观影的热烈气氛中,还有一个“随喜”从众的“我”,“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23],“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24]。这是一个我们过去尚未留意过的意味深长的镜头,在民族对立与族群耻辱的“示众”之中,端坐着一个无从抉择的尴尬的“我”,它是这复杂的现实感受的象征,是多重价值观念纠缠冲撞的缩影,是多种思想力量相互拉扯的焦点。仙台叙述,是鲁迅多重体验和心迹的“复义”性表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其实是实现了文学的最高真实——不是生活故事的还原,而是思想情感体验的最大程度的真切呈现。
因为一系列特殊的甚至是不无传奇性的流传,鲁迅的仙台叙述也被比喻为“神话”。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说这里存在某种“神话”的色彩,那也属于我们曾经的简单化理解所形成的神圣化错觉,而不是鲁迅刻意夸大的超人故事。鲁迅的叙述,其最大的愿望应该还是丰富和复杂化的思想表达。在1920年代中期,在离开仙台近二十年之后,鲁迅通过这一番历史的叙述,似乎也是在为自己开始成形的思想和情感寻找一个历史的“起点”,或者说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某种自我说明的“基点”。今天的我们,仿佛听到了他试图告诉我们,自己就是从这样的繁复感受中起步,走向了艺术形态复杂的《呐喊》《彷徨》,走向了既“油滑”又严肃的《故事新编》,更走向了晦暗与光明并存的《野草》、梦幻又现实的《朝花夕拾》,还有,非文学又自我欣赏的大量的杂文随想。总之,后来那些复义的文学效果,可能就是从这里的“张力”开始的。
李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6期)
一审:张永新
二审:李蔚超
三审:李宏伟
注释
向上滑动阅览
[1][2]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 53,57、58页。
[3]吉田富夫:《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前后》,李冬木译,《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4]廖久明:《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5]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第53页。
[6]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8][9]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肖聿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49页。
[10]江流编译:《鲁迅在仙台》,《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7、468页。
[11]参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著《鲁迅在仙台的记录》,马力、程广林译,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99页。
[12]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1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14]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92~93页。
[15]对此,伊藤虎丸先生有过深刻的概括,他将鲁迅一代人的民族意识称之为“耻辱”,而将郭沫若一代的民族意识称之为“屈辱”。他借用丸尾常喜的说法,认为鲁迅式的“耻辱”感指向的是“中国人的奴隶的国民性”,而创造社在日本人歧视眼光中的“屈辱”感则“和对中国落后的焦虑直接地联结在一起”。(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16][17][24]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8、313、317页。
[18]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19]鲁迅:《致蒋抑卮041008》,《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20][21]2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39、438页。
[22]董炳月:《“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以〈仙台书简〉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0期。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