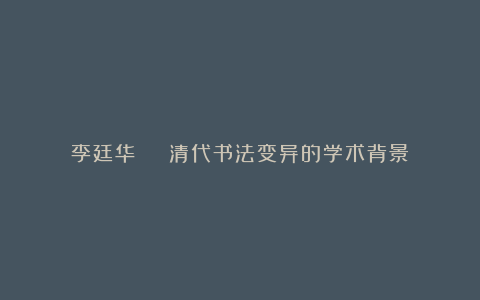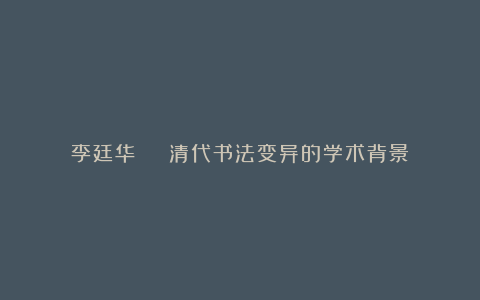|
考察清代中叶以后至于民国的书法现象,可以发现:一般文学家、诗人,即习惯称为“文人”者流,还是以“帖学”为宗,若谢无量、沈尹默等。而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即沾涉考据之学者,则多以“碑学”浸馈书法。“碑”、“帖”分立,其间可以探辨其幽微乃至悖论处甚多,先不赘论,大约分判其美学风格之不同,“碑”之所尚,为金石气;“帖”之所骛,实书卷气。为什么日日与书卷为伴的“学者”,其书风又多耽于“金石”?此一现象造成的诸多话题乃至于疑问,实际上影响到中国书法的百年发展,至今也还在漫漶之中。
清代300年文化学术表现,义理、辞章之学,均远逊前代,惟考据之学大彰。而在考据学中,又以金石器的发现运用与学术关系最为密切。清代书法受其影响,也最为明显。金石刻镂,皆为远古文字,其直接的学术价值是在“小学”即文字学方面。“小学”本为经学附庸,在有清一代,却蔚为大观,此间学者戴东原、段茂堂等毕生浸馈,使“《说文》学”风起水涌,在清代学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与金石学成为显学,是互为呼应的时代风景。当其时,欧洲以温克尔曼为代表的田野考察学派也被普遍接受,“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以考察历史遗存蔚为风气。金石学则与历史学发生密切关系。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写道:“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甲骨文。”他论列了此类对于史料研究的价值:大量碑志铭文,若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史料价值不高。少数石刻如《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为研究中外宗教联系史之难得珍宝,《莫高窟造像记》则永传各族文字。梁氏细述《小盂鼎》、《虢季子白盘》、《梁白戈》之价值,甚至以为:“余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籍以传者盖多矣。”又认为:“金石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更‘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近世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72页)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梁启超几乎没有言及“书法学”。综观清代以前学术史,“书法学”也没有成为专门学科。在梁启超以前,有包世臣与康有为作《艺舟双楫》及续书,大倡“碑学”,使其远逸证史之用,而成为近代中国书法的一段主流。时过百年,在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宕迭之后,分析这一段历史,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清代300年统治,是以血腥军事镇压和文字狱交并而施。以学术而论,考据之学的大盛,是文人学士对统治者消极反抗的表现。梁启超在论清代学术时认为:顾炎武虽然只在清初短暂表现,但他的学术,即以其《日知录》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在考据方面,已成一代高标;而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沉埋近300年后,终于与现代民主精神汇合,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先驱。以后,陈寅恪先生治史,以其博学精通,对乾、嘉考据之学亦多发扬,但陈寅恪最钦佩的历史学家其实是司马光,他在语言、宗教、制度、人物等方面的撰著,其实还是在为效法司马光撰写通史作准备。此义在其弟子蒋天枢先生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阐发甚明。清代历史学家若章学诚,德、才、识三难并具,却难施其功,终于郁郁而终。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附庸风雅,在学术上提倡的居然也还是程朱理学,但理学是论辩之学,在孔夫子的万古纲常面前,作为臣下的读书人和最高统治者是可以有辩论的。明代黄道周等人与皇帝的“平台论辩”及东林党人以气节言论为标榜,竟至士子知有文章领袖,不知有朝廷。这样的风气,清代统治者是一天也不允许出现的。故尔,有清一代,言国学,即为朴学,而不论理学。曾国藩为一代理学巨擘,但当时后世,言者皆佩其功而不论其学。在书法艺术方面,“碑学”的张扬,也与统治者的提倡大异其趣。康熙喜欢的是董其昌,乾隆心仪的是赵子昂,但“碑学”所倡,恰恰是将此二人的书法大加贬弃,目为阴柔卑弱之代表。清代学术,在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在严酷统治下的逃避,基本精神状态的消极,不可能产生真正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巨大作用的学术。比较汉、唐、宋诸代,学术虽独张朴学考据,是歪打正着,其总体文化成就不能与三代并肩。后世侈谈“康、乾盛世”,以为游牧民族之雄强且能涵泳中原古文明,可为文治武功之标榜。这使人想起一则著名的西洋趣谈,萧伯纳为文豪而其貌不扬,某女智弱而面目佼好者,欲与萧结姻,其谓:倘得宁馨儿,则汝吾之慧美并矣。萧翁对曰,胡独不料此儿集汝蠢及吾丑哉!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曾经引述此趣谈,嘲讽一厢情愿之撮合。最近,高尔泰在《读书》杂志撰文谈清代国势得失又引述此例,意谓清代之弊,恰是野蛮与虚弱结合而至于蠢丑交加,中华文明及于清代,已经处于败弊之象。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清代书法论著中最有影响的两大名著。二子之著,恰恰缺乏清代学人在朴学考据中“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功夫,而喜作大言奇论。包世臣其人,做地方官吏甚有作为,性情亦倜傥豪爽,论述书法,颇见痛快之言。但他以自己与邓石如的交谊为可居之奇,将近世书家分等罗列时,在“草书”一类中,竟将邓石如草书列于王铎之上,仅此一端,即可见其为学之蔽。邓石如之书,以巨幅篆隶直接先秦两汉之风,在文人书法难以振作之际,一新当世眼目,但品其行草书,则远未入大家之门。人无完人,艺难尽美,完白山人不能任其咎;包氏滥美,则难免后世之讥。梁启超曾经批评那种随心所欲的治学:“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驺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此论适宜以道乃师。康南海本无意于书法,为与喜好碑版的当朝大学士翁同龢交通,撰写斯著以投其好。在当时学术蔽败之间,又以其政治影响而蜚声夺誉。康有为自己在晚年曾经对人言:“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遵帖矣。”(夏晓红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470页)一言之间,说明问题不少,一则康氏早年对中国书法的全部精华尚未领会通透,以急功近利之心匆忙撰作,晚岁自见其陋。再则其人之处世为文,或并无宗旨,承窍煽风,已成习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际,已俨然文章领袖,这在三百年文禁森严之下,不啻当年东林热烈再现,狂热青年很难不受影响,及于书法,当时名士,不论简札翰墨怎样儒雅爽丽,不能为擘窠碑书,则不配谈书。究其柢,康有为之影响,积数十年而难散。后世书家,若于右任本为天纵之才,又倾心于草书,但在康有为书风笼罩之下,摹晋终在魏,草而不能狂,使人把读之倾,难免大才不能尽发之憾。
谈及康有为等人张扬之“碑学”,固然应该承认在当时士大夫书风绵延千年,造成集体“审美疲倦”之际,酿成时代风气,有其内在基础。以后的“碑学”书家,不乏真诚潜研且自成风貌者,但教徒之虔诚,未必说明教宗之正确。越是近入书法研究本质,其悖论即见显明。举一个简单例子,被康有为列为“北碑”翘楚的《张猛龙》楷书,与欧阳询楷书,在年代上相去不远,在美学风格上也同属于“劲健”、“铣利”、“谨严”之俦。为什么北朝楷书皆入“碑”,而唐代诸巨子楷书又不在“碑”列?两者的师法都应该是钟繇楷书,何以被人为分判两造?如果说,“碑学”之书崇尚“金石”气的雄强劲健,王羲之书法早有“韵高千古,力屈万夫”的魅力。离开了“韵”,专尚于力,就难免康有为书法所表现的鼓努为力。实际上,王羲之所继承的,不仅是张芝、钟繇的“帖学”先脉,先秦两汉的金石擘窠,也在其潜研涵泳之间,如果谈到篆书的中锋用笔,含蓄内蕴,在王羲之书法中实际比大量的“北碑”楷书体现得更加明显。这其中,也得到了远古先民的“金石气”。后世所谓“北碑”,若《张猛龙》、《张黑女》诸碑,全是楷书,在书体上及美学风格上,并未逸出以往书法美学的范畴。所谓“碑学”的发展,实际使得心骛此间者缩小了自己的美学视野,在广义书法中的一域画地为牢。其发展之尤,则是对中国书法精神的疏离。
前面谈到,“碑学”之兴起,本来是考据学、“小学”发展中的副产品。以碑刻文字证史,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在书法艺术中张扬过甚,对“金石气”膜拜过甚,却难免偏离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也影响到书法艺术的发展。在康有为等人以前很久,就有学者对金石学倾心研究,北宋文化巨擘欧阳修应算此中先哲。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王献之书时有一段话,在褒扬“金石”之时,不意间言明了中国书法中真正艺术命脉之所在。他说:“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刘熙载对这段话直截了当地评论说:“高文大册,非碑而何?公之言虽详于论帖,而重碑之意亦见矣”。(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第148页)重碑还是重帖,学者书家有自己的自由,不可勉强。但是,恰恰在“重碑”的欧阳修笔下,“碑”与“帖”的美学内蕴被阐发得十分清楚。“百态横生”,“骤见惊绝”,“意态无穷。比较“何尝用此”的“高文大册”,何为艺术创造?何为工具书写?还不清楚吗?如果真正承认中国书法艺术的情趣意蕴并且倾心致力于斯,难道不该向那“百态横生”,“骤见惊绝”,“意态无穷”之间去上下求索吗?在“崇碑”而实际“拜帖”的欧阳修的真心流露之前,还应该注意,醉翁所云的书法艺术之种种魅力,全是以毛笔在绵纸上自由挥发而得。摩崖擘窠,金石甲骨,都是“刀笔”凿刻而成。在世界各大文化流脉里,先民造字之初,都是凿刻文字,“书画不分”的。唯有中国人以后发明了毛笔绵纸,使得书写成为艺术。书法艺术的优势,先因其物质属性的优势。不去深入发挥其优势,不“师笔”而“师刀”,是舍本求末,遑言“师古”,侈谈“融合”,亦如萧伯纳所遇之女。萧伯纳是清醒的,他敢于拒绝;中国书法经历了百多年的宕迭,应该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