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兰2:《永乐大典》里当然没有微积分,微积分是清末李善兰发明的
前面我们分析过,在墨海书馆出版的书籍中,从《重学浅说》到《重学》出现了质的飞跃,从《数学启蒙》到《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出现了质的飞跃,因此我认为《重学浅说》、《数学启蒙》确实是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是西方窃取250年的中国科技后的学习成果,他们代表了当时西方数学、物理的真实水平。此后李善兰的贡献把他们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天文略论》和《谈天》。
在《重学》2:伽利略是19世纪传教士编造的、《重学》2:伽利略是19世纪传教士编造的(补充)两篇中我已经通过《天文略论》与《西国天学源流》的对比发现了伽利略是伪造的。现在再来仔细看看《天文略论》。没想到第一页发现的问题就出在望远镜上。
为了证明西方有多么先进的天文观测方法和仪器,合信画了一幅天文望远镜的图片,是一架长四丈的天文镜。如果你了解一些基本的望远镜知识,就能看出这是瞎编的。
传教士错误的以为望远镜只要越长越大,就可以观测的更远更精准。实际上在天文观测时最大的障碍在于星体距离我们很远,传到地球的光量过低,只有捕获了更多的光才能在望远镜上形成足够清晰的像。想要获得更多的输入光要做的是把物镜的直径加大,增加物镜的受光面积。也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望远镜是口径越大越好,而不是越长越好。望远镜的大小受限于镜头玻璃的口径而不是镜筒的长度。
我们今天想买望远镜,要看的指标是用“倍数x物镜口径”来表示,8*30表示该望远镜放大倍数为8倍,物镜口径30mm,以此类推。从来不会有人刻意去追求望远镜的长度,而上图恰恰标记的指标是镜长四丈上下。
摄影师使用的长焦镜头,焦距加大,为了满足成像的要求,镜筒会相应的加长,因此会让人产生镜头越长越好的错觉。今天我国最先进的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口径4米,墨子巡天望远镜口径2.5米,天眼Fast口径500米,却没有一台望远镜会宣称他的长度。
而西方科技史却记载很多类似的记录: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记述的数据都是由123英尺长的望远镜观测的。
——赫歇尔造过40英尺长的望远镜。(大概就是本图的原型)
——爱尔兰的罗斯勋爵(Lord Rosse,原名William Parsons,1800—1867)所造的望远镜长达16米。
但是往往都伴随着一句说明,“这个巨大的望远镜难以操作,很少使用。”这些巨大的望远镜造出来只是摆设吗?那么那些天文观测结果又是从何而来呢?
合信在内容里继续吹嘘西方的大望远镜,但是观测月球需要这么大的望远镜吗?1849年西方能生产直径四尺八寸的玻璃透镜?要知道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光学镜头直径也只有1.554米,还是2019年制造的。清末西方难道已经掌握了天顶星科技?
2019年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制造了史上最大的光学镜头,直径5.1英尺(1554mm)
西方人虚构了伽利略、牛顿这些天文学家以及他们的理论,为了证明这些数据的真实存在又虚构了天文望远镜,但是不理解望远镜的基本原理,虚构的望远镜露了马脚。
1849年的《天文略论》配图只有大望远镜,而到了1855年《博物新编》再版时又加入了观星镜。1852年李善兰加入墨海书馆,这个变化和李善兰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可以从《谈天》中找到答案。
《谈天》中李善兰介绍了两种使用望远镜结合计时来观测星体的方法,如果是观测子午面,就使用上图中的子午仪。如果不是子午面就需要加装带刻度的铜环,用刻度体现测量角度,如下图。
合信的《博物新编》虽然又一次放大了望远镜的规格,但是原理别无二致。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测,立刻就有证据跳出来证明它,这种巧合不止一次出现了。
可惜的是李善兰接触的天文知识显然不是当时中国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清朝的科技中心钦天监始终被传教士把持着,他们使用的观测仪器可比这些要先进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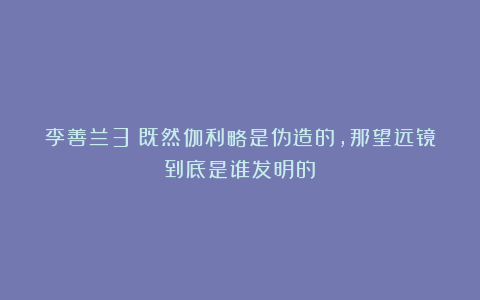
这架双千里镜象限仪出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皇朝礼器图式》,是当时钦天监日常使用的观测仪器。两支望远镜一支是定标,一支是游标,测量精度比单筒象限仪要高几百倍(游标刻度为500)。而且是可以自由旋转的,并不局限于一个子午面。这可比100年后李善兰记述的子午仪先进多了。
有人会说双千里镜象限仪本来就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可是《皇朝礼器图式》明明写的是“本朝制”。英国进贡和传教士进献的仪器中也从来没有这台仪器的记录。如果双千里镜象限仪真是西方制作的,又如何解释100年后传教士带来的制器知识如此简陋呢?
既然伽利略是伪造的,那么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是哪来的?顺着望远镜这个线索回溯到1600年前后,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关于望远镜的发明目前主流的说法是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并把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近来打补丁的说法是1608年荷兰眼镜商汉斯·李波尔(Hans Lippershey)制造了第一台望远镜,伽利略是改进的。明末传教士来华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把望远镜带到了中国。
首先,在利玛窦的《耶稣会远征中国记》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望远镜,利玛窦用来贿赂明朝官员的礼物是玻璃三棱镜,说中国官员喜欢这种光闪闪的东西。1608年才发明望远镜,而此时利玛窦在中国已经呆了26年了。显然利玛窦把望远镜带到中国是不成立的。
其次,《重学》2:伽利略是19世纪传教士编造的、《重学》2:伽利略是19世纪传教士编造的(补充)已经分析过了伽利略是清末在墨海书馆编造出来的,所以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也是虚构的。
那么把望远镜带入中国的是汤若望吗?汤若望是1622年来到中国,4年后汤若望写了一本《远镜说》,当然也是中国人李祖白笔授的。
《远镜说》记载了使用望远镜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包括月球的环形山,金星围绕太阳运动,观测到了太阳黑子,木星有四颗卫星,土星有双耳(土星环),以及肉眼不能看到的恒星如北斗开阳星的辅星等。这部分内容基本是1615年阳玛诺写的《天问略》关于望远镜介绍的扩写,并附上了配图。可阳玛诺也是1601年就离开欧洲前往中国了。
之后介绍望远镜的应用场景,即“利用”。在这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夫远镜者,二镜合之,以成器者也。其利用既如斯矣。乃分之,而制造如法,则又各利于用焉。即中国所谓眼镜也。试言之。
汤若望说望远镜是用两个镜片组合制成,把镜片分开,单独也可以被利用,就是中国的眼镜。注意,这里提到了“中国的眼镜”,也就是说此时的欧洲并没有眼镜。既然欧洲没有眼镜,又怎么能发明出两组透镜组合而成的望远镜的呢?而从近几年新编的伪史看,汉斯·李波尔是一位眼镜商,恰恰证明了望远镜的发明是来自于眼镜业的发展。
造镜至巧也,用镜至变也。取不定之法于一定之中。必须面授方得了然。若但凭书,不无差谬。今亦撮其大略而已。
对于望远镜的制作方法,汤若望好像是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可以确定的是汤若望并不清楚如何才能做好一架望远镜。西方所吹嘘的科学的、系统的、定量的研究,在《远镜说》中并不存在。说好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怎么在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中毫无体现呢?
有人说汤若望不会造望远镜也可以把望远镜带来中国啊,事实上并没有,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了汤若望进献过望远镜给明朝皇帝。直到崇祯七年(1634年)李天经的奏折上才提到“若夫窥筒,亦名望远镜。……此则远西诸臣罗雅谷、汤若望等从其本国携来而葺饰之,所以呈览者也。”(出自《西洋新法历书》)。利玛窦汤若望这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进入钦天监为明朝修历,汤若望的望远镜是显示其天文成就的重要工具,竟然在手里攥了12年才进献给皇帝,我不得不怀疑汤若望的望远镜就是在中国制造的。
那么1600年前后的中国有能力发明制造出望远镜吗?答案是肯定的。这里会涉及到几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老熟人徐光启,另外两个是苏州人薄珏和孙云球。
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李之藻就曾上书称西人“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窥天窥日之器”显然就是望远镜了,这比阳玛诺的《天问略》又早了两年。
再往前,有一本书值得关注。浙江图书馆收藏的一本《开成纪要》抄本。书中注明“太西利玛窦传,松江徐光启校”,流传自徐氏四代孙徐朝俊,是一本徐氏家传且流传甚少的利徐著作。
《开成纪要》可以证实望远镜是中国人发明的。
《开成纪要》既然是利玛窦口授,那么显然他的成书年代就是在利玛窦生前了,利玛窦是1610年死的,以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传播速度,利玛窦不可能在生前了解1608年发明的望远镜,而且徐光启1607年就与利玛窦分别回家丁忧了。
种藕
柿漆
《开成纪要》介绍了很多农业、手工业技法,如造瓷器泑法、柿漆、种藕等。众所周知制瓷是中国特有的手工业,传教士殷弘绪1712年才到景德镇窃取了制瓷工艺送回欧洲。而柿子、漆树、藕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植物,你见过现代欧洲人吃藕吗?何况是明朝。这就表明《开成纪要》完全是一部介绍中国科技的书,其中也包含了望远镜。
《开成纪要》详细介绍了望远镜的制作方法:
体制:前镜要突出,则所视物大于本体,远则其大无尽。远者则前镜去目稍远也。故以后镜收之。后镜要窪下,其所视物形小於本体。前后相合。又二镜相去如法,则远体成近,小体成大矣。
造模:铜板如窪镜,径七寸上下,其深中规,规之半径即远镜筒之长。为前后二镜相去之度。先作半径尺,取圆分作两曲背尺。又作铜钅与曲背尺相合。以旋模令与曲背尺相合,乃矣。此曲背尺留取常用试模。恐磨久模损则不准也。
这里懒得敲字了,详见图。
把材料、体制、造模、造镜、造筒的详细工艺过程都一一列出,其细致程度远超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望远镜制作的书籍记载。也难怪汤若望《远镜说》写的如此含糊,这个复杂程度显然超过洋人的理解能力了。可以明显看出,这是源自于专业从事制作的工匠的实用工艺。说明在成书之时制作望远镜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了。
造筒:或用铜皮,或用铁皮,以锡焊,或用布裱,浆用白芨麪,内外用绫作面,以便抽拔。筒之数,或二或三以上,同前后镜相去之度,酌量为之。
白芨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植物,绫是中国特有的手工业品。《开成纪要》中提到了“西土不用铅锡”,这里却说“以锡焊”,制作工艺也是中国的。只能说这望远镜从里到外是纯纯的中国血统啊。
如果望远镜源于中国,那么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任何一个传教士携带、使用望远镜就都解释得通了。徐光启和利玛窦在161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制造望远镜的方法。
这些制作技艺来源于何处呢,我的答案是来自苏州。苏州自古是我国琢玉业的中心之一,《吴郡志》记载早在唐代苏州就有琢玉的工场和名艺人了。《天工开物》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可见明代苏州琢玉已经闻名天下。在雕琢水晶、玛瑙的过程中,发展出了磨镜片业。苏州市郊的新郭自宋代就出现了磨制眼镜片的作坊,这也和汤若望说的“中国所谓眼镜”相符。
这幅图是明末清初的《苏州市景商业图册》之一,记录了明末清初苏州的街市景象。在山塘街五人墓碑的旁边有一家“益美斋精制水晶眼镜铺”,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眼镜店的图像记载。说明当时已经有成熟的眼镜销售体系。明清两代苏州发展成为了全国的眼镜业集散地。如今上海著名的吴良材眼镜公司正是苏州老店的分号。
从《开成纪要》的内容来看,包含了玉器、水晶、玻璃、远镜的加工制作方法,还多处提到了苏州地区使用的独特技巧,与苏州制镜业的发展演变是吻合的。可以确定苏州地区的生产活动是其内容的重要来源。正是苏州的行业积累才能发展出这些生产制作方法,才能发明出望远镜。也正是这种行业积累才会孕育出薄珏、孙云球这样的制镜专家。
薄珏、孙云球都是苏州人,根据多位学者的研究,薄珏和孙云球都制作过开普勒式望远镜,传教士根据《开成纪要》制作的都是伽利略式望远镜,孙云球记述过包括望远镜、万花筒、显微镜在内的72种制镜方法,说明此时的制镜技术处在快速发展快速迭代的阶段。也正是因为处于发明阶段,才使当时的中国人对望远镜很陌生,误认为望远镜来自于西方,误认为西方科技发达远超中国,造就了流传400多年的谎言。
对了,当年一手促成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全过程的瞿太素也是苏州人,瞿太素作为苏州显贵家族的浪荡子,对苏州的琢玉制镜必定是了解的,瞿太素在这个谎言的编造过程中又发挥了多少作用呢?抑或本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