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李瑞生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二)
五妮叔家的地主成份说起来有点冤。民国时期他爷爷做点小生意,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从别人手里一点点买地,到他父亲这一辈又发展壮大积攒了几十亩地。
解放前他父亲及其家人自己耕种管理这些土地,农忙季节才舍得雇佣部分长工,在当时应该算是自力更生的富农阶层,算不上地主的范畴。说巧不巧解放后土地改革划成分时,按人均亩数刚好达到地主标准,不仅没收了土地还扣上地主的帽子。
五妮叔虽然年轻能干,然而历史遗留的地主狗崽子身份,却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走里快了别人说他地主戴个先进帽—一假积极,走里慢了别人说他地主少爷吊儿郎当的本性难移,平常不得不规规矩矩夹起尾巴做人,不敢有丝豪造次。
五妮叔的人生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当时的情况是地主家的孩子不允许当兵、考大学,因此他也就无心“恋战“,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大字也识不了几个,然而天资聪颖的他却敏而好学,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难”字,会木工、泥工、烧砖制瓦等多种当时应景的手艺,人称“百事摊”。
当时有手艺的人很吃香,讨老婆本来不成问题,但由于弟兄多成分高,根正苗红贫农家的闺女因为怕受牵连,谁也不愿嫁给地主家的儿子,五妮叔快三十的年纪依然还是孤家寡人。
六七十年代农村女孩找对像,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她们的目标很简单,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只要成分不高,小伙子踏实肯干,能吃饱饭、有住的地方,就愿意跟你搭伙过日子,铺盖卷搬到一起就算一家人了。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个社会保持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能吃饱饭,娶上媳妇,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大部分兄弟多家底薄的人家,很多时间是揭不开锅吃不饱饭的,因此取不上媳妇就成了生活中的常态。地主家的子女就更不用提了,除了换亲转亲和娶外地女子,剩下的就只有打光棍了。
五妮叔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通过换亲的形式解决了终身大事,于是便造就了那个年代独有的有舅没妗子、有姑没姑父的亲戚关系。
当时还有三家转亲的,转亲与换亲性质基本相同,最大不同在于他们的子女可以转着圈称呼舅和妗子、姑和姑父,换亲则只能喊舅而不能称姑父,也无法称呼自己的姑为妗子。
换亲和转亲这种畸形的婚姻看似两家或三家都不吃亏,都是一家出个闺女换个儿媳妇,实际上到头来牺牲的却是几个家庭女孩子的利益,因为她们迫于家庭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追求个人的幸福而去成全自己家族的“利益”。
当然换亲和转亲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迫不得已实在没招了才出此下策,他们当中总有一对不会那么称心如意,感觉憋屈的女孩想想自己年迈的父母,看看自己可怜的兄弟,大部分都会选择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因为这种亲戚模式牵一发而动全身,小不忍则乱了双方或多方父母苦心经营的大谋。
近门四叔四婶家梅姐就是那个年代的牺牲品,她既不是换亲,也不是转亲,但和换亲转亲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梅姐的哥哥人长的不孬,美中不足的是先天性兔唇,四叔四婶为了本家哥哥的终身大事都快急疯了,好不容易托媒人给撮合一个姑娘,就是彩礼要的有点多,其它应用之物不算,光彩礼就要六百块钱,六百块钱对于农村当时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大部分人家来说,就相当于天文数字,上哪儿弄钱里?
四面净八面光的光景让四叔四婶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最后把目光聚集在了正在读书的梅姐身上,于是初中没读完的梅姐就被四叔四婶强迫休学,准备让她嫁人为同族哥哥筹备彩礼。
梅姐不仅书念的好,而且人长的也水灵,既是班干部又是班里的尖子生,老师和同学们都替梅姐感到遗憾和惋惜,为此事梅姐哭肿了眼睛伤透了心,但也经不住四叔四婶苦口婆心地劝,就差没给她跪下了。
最后妥协的梅姐嫁给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乔满银,就这样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前途不可限量的梅姐愣是毁在了包办婚姻上。
梅姐出嫁那天,也是她哥迎娶她嫂子的日子,四叔四婶那一天既打发闺女又娶儿媳妇可谓是双喜临门。
按约定梅姐出嫁的队伍先走,她嫂子进门的人马后到,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梅姐出嫁的队伍刚走出村口却被紧急叫停,原来是她嫂子娘家通过媒人传来话说,再拿二百块钱才肯发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哪儿去弄二百块钱,无奈之下四叔四婶不得不效仿媳妇娘家的作法,让梅姐的婆家也再拿二百块钱再发人。前头拉车后头有辙,一个萝卜顶一个坑,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最后整里几家人心里都不愉快。
后来得知梅姐她嫂子的娘家也是为了自家儿子筹备彩礼才又多要了二百块钱,转了一圈梅姐最终成了那个“替罪羊“。
恶少乔满银常以买来的媳妇为由,动不动就拿梅姐出气,梅姐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时常以泪洗面,婆子也不是什么善茬,不但对儿子的恶行假装视而不见,有时候还火上浇油纵容她儿子,故意刁难梅姐。
天性善良的梅姐对自己受的家暴选择忍气吞声,从不回娘家诉苦告状,表现出少有的刚强,因为她深知娘家人为她做主出气之后,极有可能换来乔满银更加变本加厉的打骂,她想独自饮下爹妈亲手为她酿的这杯苦酒,而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梅姐很少回娘家。
几年之后,再次见到梅姐时,已是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少有了从前的活泼与灵动,那个充满理想与抱负的花季少女,转眼间成了让人不忍直视的黄脸婆,不得不感叹命运真是太能捉弄人了。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利就有弊。利就是换亲和转亲确实解决了老大难们的婚姻问题,而且有的感情还挺好,日子过得也不错。弊端就是强行捆绑在一起婚姻没有感情基础,差距确实太大实在没有缘分引起悲剧的也不是没有。
五妮叔的年龄眼看就要过墙,他爹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为他张罗女人,对外人讲只要有手有脚,饿了知道吃饭,下雨知道往家跑,哪怕是带小孩的寡妇也不嫌弃,然而五妮叔的婚姻却一直风平浪静,悬而未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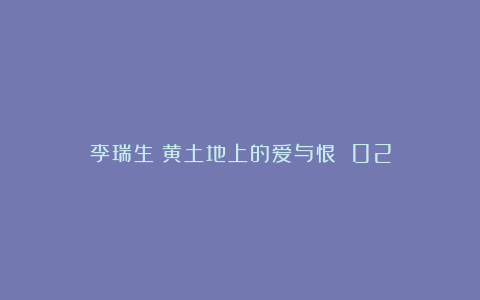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然间刮起了一股川女远嫁河南、安徽等省的风暴。这其中的原因有人说因为平原地区的生产劳动比四川偏远山区要轻松的多,川女为了摆脱老家肩扛背驮的重负荷劳动而选择走出了大山,有的说是婚姻市场供需关系导致的,也有人说是人贩子从中兴风作浪,我觉得还是后来的“传帮带“起的作用最大。
我们村有好几个都是先入者从四川娘家带回了表姐妹、堂姐妹以及村上其它想走出山窝窝里的小姐妹,于是就有了一波儿又一波儿的川女跟风,千里迢迢远嫁到了河南,这给当时很多成分高、年龄大的光棍汉们解决了单身问题。
尽管当时有大量的四川女子涌入河南,但也只有成份高年龄大的才愿意娶,本地适婚男青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娶的,因为背地里怕人说闲话,说某某某娶不到本地女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娶个四川老婆,这里并没有歧视异地人的意思,这只是当时本地男青年骨子里的一种思想认识而已。
这些来自异乡的川女大都出生在偏僻的穷山窝里,她们不仅能吃苦,而且很能干,不娇气会持家,从刚来时机关枪似的带有“麻辣味“的四川话,到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通过几十年的磨合最后完全融入了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
我所知道的嫁到我们村的川女,通过努力后来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也有极个别年龄悬殊男人脾气暴躁,挨打受气实在过不下去偷偷跑路的。
五妮叔和哑巴婶能走到一起,让人们相信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魔力,明白了什么叫前世缘今世情。
哑巴婶娘家四川达州的,被人领到河南时年方二十,个不算高人很漂亮,两条麻花辫子又粗又长,小模样长得无可挑剔,是那种驴见不踢鸟见不飞的小家碧玉型,除了哑巴没别的毛病。
媒人领她相头两个又黑又老和她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时,哑巴婶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哇哇直叫。
也许命中注定的有缘人都心有灵犀,直到看见年轻白净的五妮叔,她才不知所措地揉搓着衣角,并娇羞地低下了头。
哑巴婶虽然只看了五妮叔一眼就再也不敢看他,但她心里明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个道理,潜意识里认为只要人对了,世界肯定错不了。她根本没有考虑五妮叔的地主成份会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哑巴婶不仅心灵手巧,而且聪慧过人,纳簰子、串蓖子、织布纺花、裁衣做鞋、缝缝䃼补、下地劳动,但凡眼见之活没有不会的,正所谓家里地里都能干,十人见了九人夸。家母人慈心善,哑巴婶有空总喜欢粘在俺家向她讨教,她的手工活大都是我母亲所教。
五妮叔自从抱得美人归,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对哑巴新娘体贴入微犹如珍宝。哑巴婶也算不虚河南之行,千里之外终于寻到一个知冷知热有情有义的如意郎君。她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她心里明白着呢,这女人一辈子图个啥,不就是寻个对自己好的男人吗?
一晃多年过去了,哑巴婶给五妮叔陆续生了三男并二女,本来生活就困难再加上五张嗷嗷待哺的小嘴,让这个来之不易的小家更是举步维艰,于是让全家人能吃饱饭就成了五妮叔奋斗的头等大事。
空怀一身本事的五妮叔没有用武之地,于是农闲时节就找队长商量想出去搞副业䃼贴家用。
那个年代集体经济下的大锅饭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只有集体生活,没有个人自由,是不允许私自外出打工的,要想出去干,首先要经过生产队同意,还要通过大队审批,不是你有手艺就可以随便出去挣钱。
当时地多劳动力少,外出搞副业必须按约定三夏三秋,抢收抢种季节归队搞生产。搞副业挣的钱需按外出天数和约定的份额给队里交钱,只要向生产队交钱,队里就给你记工分,年底结算就能分到口粮。计划经济制度下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粮食不允许自由买卖,人们的吃、穿、用都是凭票证计划供应的。
就这样种罢麦走,快过年回,五妮叔赚回了他人生的第一捅金,对窝居在家的人们来说也算来了个弯道超车。
他心里暗自盘算外出搞副业虽然时间短,却比在生产队干一年赚的还多,在生产队干活吃的是自己家的粮食,外出做手艺一天三顿都是吃别人,并且吃的还是细粮,看着孩子们能吃上饱饭、哑巴婶笑着竖起的大拇指,五妮叔终于松了一口气。
世界虽然是光明的,但也总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这个世上最难测的就是人心,你永远也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会给你当头一棒。
当五妮叔还沉浸在幸福的日子从此有奔头的时候,可惜好景不长,纸终究包不住火,他外出搞副业的事被眼红的人直接告到了公社,举报他地主阶级剥削的本性不改,资本主义尾巴都翘上天了。
那时候阶级斗争抓的紧,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也不要资本主义一颗苗。公社革委会把他这种行为定性为农民队伍里的老鼠屎,偷偷搞副业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薅社会主义的羊毛,是不折不扣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我记得生产队时期的会特别多,大队开大会,小队开小会,开了大会开小会,开了小会开大会,不是批判会,就是斗争会,白天干一天活累的够呛,晚上还得熬夜开会,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跟着大人屁股后面去开会的情景。
在大队部举行的斗私批修大会上,公社革委会主任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忘记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坚决抵制五妮叔这种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歪风邪气。
五花大绑的五妮叔受进屈辱,还必须如实交待自己投机取巧的问题。经此一劫五妮叔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得既彻底又干净,大会批小会斗的经历就像一场噩梦,让他毛骨悚然、心有余悸,若不是放不下哑巴婶和未成年的孩子们,死的心都有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他再也没有出去搞过副业。
六七十年代的饥饿岁月,是父辈们一路走来心中永远的痛。尽管当时人们的劳动热情很高,但由于那时候科学技术跟不上,农药化肥几乎没有,种地全靠粪当家,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始终都无法摆脱物资短缺的局面。人人吃饱饭,也只能是一句暖心的口号,遇上灾荒之年,别说黑窝头了,有时候甚至连汤都喝不上。
记忆中集体经济下的生产队年代,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余粮户不多,很多都是缺粮户,不愁吃饭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那个年代父辈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在他们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中,就连做梦都在苦苦寻找不受穷的秘方,总想着怎么才能把黑面馍变成花卷,再把花卷变成白面馍,他们始终相信人总不能一辈子受穷,黄河水总有清的那一天。然而当他们为此耗尽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悄悄爬上他们的眼角、两鬓斑白的时候,那真正意义上属于他们想要的幸福,还远远没有到来。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瑞生,1969年出生于社旗县太和镇闫店岗村。1988年毕业于饶良三高,90年入伍当兵四年汽车兵,目前在外跑运输。乡土中原铁杆粉丝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