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 击 上 方 蓝 字 “ 心 香 文 艺 ” 关 注
心 香 文 艺
心香文艺音频已入驻喜马拉雅
车到山前
散文
六岁那年的往事,像北国窗棂上凝结的霜花,虽历经岁月摩挲,触及时仍带着刺骨的凉意,却又在阳光下折射出晶莹的光斑。那时的山东老家,日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爹攥着发小从吉林山乡捎来的信,手指在粗糙的信纸上摩挲良久,终于牙一咬:“闯关东去。”
那时的远行,粮票是命根子,介绍信是护身符。爹把攒了不知多少个寒夜的路费贴身藏着,在火车站角落里蜷成一只虾米——能避开驱赶,便觉得是老天垂怜。火车轰鸣着穿越苍茫大地,我紧贴车窗,看那些枯槁的树木和荒芜的田野向后飞驰,仿佛在逃离一个时代的贫瘠。
待真摸到那片陌生的黑土地,盼头却碎了一地。爹的发小正在批斗会上挨整,关在土坯房里,连面都见不上。有好心人压低嗓门劝:“回吧,他自身都难保了。”那句话轻若羽毛,落在爹肩上却重如千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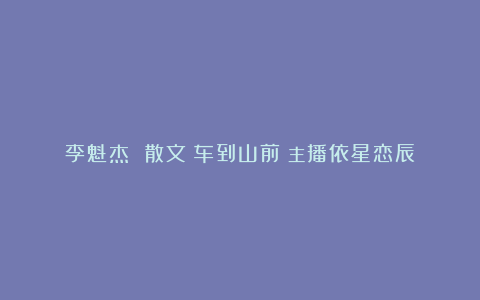
几千里的跋涉,那点路费是爹娘从嗓子眼里省出来的,是蘸着咸菜疙瘩数出来的。我偷瞄爹的脊背,方才还挺得笔直,此刻却像被抽了主心骨,一点点佝偻下去。暮色四合时,他望着远山轻轻吐出一口气。那气息在寒夜里凝成白雾,模糊了他眼底深藏的无奈。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心中无所不能的神祇,原来也有血肉之躯的脆弱。
他牵起我的手走向黑暗。陌生的山野裹着墨色,星星在天际冷漠地眨眼,月亮不知藏到了何处。爹的脚步声在旷野里格外沉重,每一步都踏在绝望的边缘。我攥着他微微发抖的手,六岁的心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走投无路。
就在黑暗快要将我们彻底吞噬时,身后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大叔!等一等!”一个姑娘的声音穿透夜色,带着奔跑后的喘息,“俺爹让追你们!这黑天瞎火的要往哪去啊!”
许是跑得急了,她额发被汗水濡湿,在凛冽的寒风中蒸腾着白汽。后来才知道,是公社书记老许听说山东来了父子俩投亲不遇,急得拍桌子吼女儿:“还带着娃娃呢!这冰天雪地的要出人命的!”这个腿脚不便的老书记,自己追不出来,却把焦急化作了女儿脚下的疾步。
许书记见到我们时,煤油灯在他脸上跳动出温暖的光晕。“胡闹!”他嗓门很大,却让人莫名安心,“都是山东老乡,到了这儿就是到家了!”热腾腾的玉米糊糊端上来,黄澄澄的粥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膜,那是饥饿年代最动人的光泽。
饭后,老许就着昏黄的灯光写下字条,纸页沙沙作响像是夜曲。“明天去新开河找李队长,”他把字条塞进爹手里,“就说我老许让去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咱山东人到哪儿都不能丢了相互帮衬的本分。”
那张薄薄的纸片,后来成了我们在黑土地扎根的凭证。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夜追来的脚步声、那碗滚烫的玉米糊、那句质朴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将人从冰窟里打捞起来的温暖。东北人的热肠,就这样钻进了一个异乡人的骨头缝里,化作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永恒暖意。
每当人生遇到坎坷,我总会想起那个夜晚:黑暗中最深的绝望,如何被一盏油灯温柔点亮;冰天雪地里的绝路,怎样被一颗热心踏出通途。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路,从来都不是踩在脚下,而是铺在人心上的。
2025年9月14日
以文会友,推广交流、相互促进,我在这里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