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天一阁文丛》第16辑第22-3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又载李开升《古籍之为文物》第18-34页,中华书局,2019年(2022年重印)。此据word稿本,引用请据原书。
天一阁作为中国古代藏书楼的代表,和绝大多数藏书楼一样,都发生过的藏书流散之事。天一阁现存原藏书只有总数的大约五分之一,有五分之四的藏书在不同时期、通过各种途径流散出阁。流散书研究对复原天一阁藏书原貌至关重要,是天一阁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藏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拟从阁书流散的历史、流散书的研究史、研究方法及设想等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天一阁藏书之流散,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清易代之际。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云:“自易代以来,亦稍有缺佚,然犹存其十之八。”①细味其言,似乎是说入清以后至其写此文时(乾隆三年,1738)②,天一阁藏书散失十分之二,其中包括易代之际的散失。全祖望曾多次登临天一阁③,对天一阁藏书有所了解,他的说法应该有一定依据。大约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约1780年代),吴翌凤在《东斋脞语》中云:“鄞县范氏天一阁……迄今三百年,虽十亡四、五,然所存尚可观也。”④吴氏为清代苏州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题跋中曾多次提到他,他对天一阁藏书也比较关注。在吴氏撰成《东斋脞语》不久之前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天一阁应清廷要求,进呈六百多种藏书,以供编纂《四库全书》之用。这批进呈书除了访归的两种以外,全部流散在外。因有《天一阁进呈书目》(图1)传世,故进呈书是天一阁流散书中最早一批有详细目录记载的。吴翌凤所云“十亡四、五”是否包括进呈书,还不是很清楚,其数字也不一定能准确落实。这是截止到清廷征书的乾隆时期(约18世纪末)天一阁藏书流散的大概情况。
注释:
①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藏书史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325页。
②董秉纯《全谢山年谱》乾隆三年:“重登天一阁,搜括金石旧搨,编为《天一阁碑目》,又为之记。”《全祖望集汇校辑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③董秉纯《全谢山年谱》雍正元年、乾隆三年;又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有“吾每登是阁”云云,《全祖望集汇校辑注》,第10、16、1062页。
④吴翌凤《东斋脞语》,《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影印《昭代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9页。此书当撰于吴氏馆于陶家东斋时(1768—1787),参见王幼敏《吴翌凤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7、111-112页);又其中陈世华条云其卒于“甲辰”,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则当撰于此年之后。陈登原以钱大昕登楼时间(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后谢山(全祖望)五十年”,大致准确;而又以吴翌凤为钱大昕“后五十年”,则误差太大,实则钱、吴时间相近。陈氏大约是以吴氏所云“三百年”来计算的,实际上吴氏所说不确。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陈登原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图1 《天一阁进呈书目》
19世纪天一阁藏书的两次流散都与近代史的重要事件有关。第一次是鸦片战争,“道光庚子,英人破宁波,登阁周视,仅取《一统志》及舆地书数种而去”①。其时间稍有出入,庚子为道光二十年(1840),实则英军据宁波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10月至次年5月②。所云“《一统志》”可能是《大明一统志》,此书在嘉庆时阮元倡议、范邦甸等编《天一阁书目》(图2,下简称“阮《目》”)尚有著录,在道光末年刘喜海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下简称“刘《目》”)中已无著录③。据此记载,此次阁书损失不大。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战争,这次损失比较大。虽经范邦绥等范氏后人努力追回一部分,然未能追回者恐亦不少,惟其具体损失何书尚乏细致研究④。
图2 阮元本《天一阁书目》
除了战争外,还有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的藏书流散。刘《目》之《例言》第二条云:“御赐《图书集成》一万卷,见缺一千余卷。”冯贞群云:“盖范氏子姓抽出参考,阅毕未归。”⑤这是发生在乾隆赐书之后、道光末年编目之前的事。御赐书尚且如此,其他书也未必没有这种情况。
天一阁最后一次、也是目前所知最大规模的一次藏书流散是民国三年(1914)的藏书失窃。乡人冯德富指使贼人薛继渭潜入阁中多日,将藏书窃出,售予上海的书店。虽最终冯、薛二人皆被判入狱,藏书却未能追回。这次损失藏书在一千种以上⑥。范钦十一世孙范玉森1915年有题跋记此次阁书被窃事(图3)。
图3 《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范玉森题跋
此后天一阁藏书再未出现大量流散情况。民国七年再次被窃,幸而所失无几⑦。抗日战争期间,阁书辗转在外近十年,也只损失数部书⑧。
注释:
①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31页。黄家鼎《天一阁颠末考》云:“道光辛丑(二十一年,1841),英吉利扰浙,英兵据郡城者数月,劫灰横飞不及于阁,殆有神物呵护。”其时间较准确,而不云掠书数种之事。《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29页。
②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第374、432页。
③范邦甸等《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刘喜海《天一阁见存书目》,民国抄本,天一阁博物馆藏。
④参见《天一阁藏书史志》,第47-48、290、329、331页。
⑤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铅印本。
⑥参见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旧时书坊》,三联书店,2005年,第87-88页;邱嗣斌、汪卫兴《天一阁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48-52页。
⑦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
⑧骆兆平《查检范氏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2-45页。
二
最早专门研究天一阁藏书流散的是陈登原的《天一阁藏书考》,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首先,书中提出以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进呈藏书的范懋柱(1721—1780)为中断之点,“自此以上溯至有明嘉靖,凡二百余年,为书之收藏时期;自此下讫于胜清之末,凡百五十年,为书之散佚时期。”①此说颇有道理,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是民国以前天一阁最后一次入藏大规模重要典籍,天一阁的世俗荣耀由于皇帝褒奖达到顶点。然而同时进呈书六百余种从此一去不返,是目前所知目录明确的首次大规模藏书流散。其次,书中设专章《天一阁之散佚》,以太平天国战争为节点,将天一阁藏书的流散分为洪杨以前、洪杨之时和洪杨以后三个时期,云:“洪杨以前者,实为阁书以管理有所不及,而逐渐散佚。”“洪杨之役,则实阁书大批散佚之时期。”“洪杨以后,盖经丧乱之余,而又重以盗窃之祸。黄台三摘,抱蔓可归,此其时也。”②陈氏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尤其是对流散书历史时期的划分,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不过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进呈书的散佚,实际上大批散佚在洪杨以前已经开始。另外还有一些小问题,如未提及鸦片战争中的藏书散佚、未能确定薛继渭盗书时间等。
赵万里于1934年发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总结了阁书外散的三个原因:“1.由于修《四库全书》时,阁书奉命进呈因而散落的。”“2.由于乾隆后当地散落出去的。”“3.由于民国初年为巨盗薛某窃去的。”③其中前后两个原因比较清楚,第二个则有点复杂,主要指宁波当地藏书家大多收藏有阁书,宁波本地书肆也多有阁书,但这似乎只是阁书外散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三复斯言,似乎赵氏对这些书出阁的原因和途径颇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想法。赵氏版本学造诣精深,且经眼善本无数,因此这篇文章对考察阁书流散途径、鉴别阁书归属都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多次引用冯贞群之语,因陈氏不在宁波,许多资料难以掌握。而冯贞群则长居宁波,一直关注天一阁,并曾任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主任。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出版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之《序》中,冯氏提出了天一阁藏书“五劫”说,是迄今为止有关阁书流散影响最大的观点。所谓五劫,即上文所述明清易代、清修四库、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薛继渭盗书等五次藏书流散。五劫说较陈登原的三时期说前进了一大步,补充了明清易代、清修四库和鸦片战争三次散佚,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阁书流散的历史过程全景。从研究方法上看,五劫说更接近中国传统的书厄论,而三时期说则侧重原因和背景分析,具有一定理论高度,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相类。不过五劫说毕竟更全面、完整,故影响至今④。
也有学者对五劫说提出异议,主要是针对明清易代这一劫,比如骆兆平引用李邺嗣之语“天一阁所藏书最有法,至今百余年,卷帙完善”,并以书目互相比对,认为:“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前的近二百年中,天一阁藏书未曾大量散失。”“在范钦去世以后至范懋柱进呈图书之前的一百八十多年间,天一阁藏书续增或散出的数量都不大。”⑤冯贞群在这一劫下有注云:“经籍、明历朝实录之半于斯时流出。”以实录而言,用宋荦漫堂抄本《天一阁书目》(图4,下简称“宋《目》”)与阮《目》(包括进呈书)相校,前者十六部,后者十一部,减少的虽然没有一半那么多,但接近三分之一。当然,确切的结论还需要全面考察。
图4 清初宋荦漫堂抄本《天一阁书目》
此后对阁书流散的宏观研究,大体不出五劫说的框架。有的对史料搜集更详尽一些,如蔡佩玲《范氏天一阁研究》⑥。有的在次数上稍作调整,如柯亚莉《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研究》在五劫之后又加上抗战时期损失的数种,作为第六次散佚⑦。
注释:
①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前引《陈登原全集》第四册,第9页。
②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第37-43页。“黄台”二句,用唐李贤《黄台瓜辞》典,此处意为一再散失,所剩无几。
③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赵万里文集》第二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77-478页。
④如邱嗣斌、汪卫兴《天一阁史话》,第47-52页;虞浩旭《琅嬛福地天一阁》,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94-96页,均持此观点。
⑤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第43、80-81页。后其《书城琐记·新见〈天一阁书目〉摘抄本校读记》云:“这部分书籍(指见于摘抄本万历《天一阁书目》而不见于后来书目的书)几乎占了摘抄书目总数的一半。可知自万历十五年至明末清初时期的近百年中,天一阁藏书有某些变动。当然也不排除康熙以来的天一阁旧目有失载的可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对此问题看法似有所变化。
⑥蔡佩玲《范氏天一阁研究》,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第54-68页。
⑦柯亚莉《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研究》,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4页。
三
前面讨论的主要是对流散书的宏观研究,而微观方面的研究,即考察每一部书的流散过程和最终下落,并尽量使其以合适的形式回归阁中,则是流散书研究的最重要的目标。
目前所知天一阁最早访归流散书是太平天国时期,阁书在战乱中散出,范邦绥及族人设法追回了一部分,但追回的具体书目却未见记载①。民国三年(1914)薛继渭盗书,当时一部书也未能追回。次年张美翊得到其中范钦中举的《嘉靖七年浙江乡试录》、中进士的《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以及范光文手抄诗稿等三部书,将其交还天一阁②。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期间(1933—1941),访归流散藏书也是该会的一项任务,冯贞群及委员会访归阁书《(嘉靖)广东通志》《明儒论宗》《类隽》等十二部③。1949年以后,天一阁访归的书比较多,截至1987年,共访归阁书一百八十五部、三千余卷④。自此以后,原书访归几不可闻⑤。
在原书访归之外,更多的流散书难以直接访归,需要调查、研究。对于这些流散书,早在19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为其编目的设想。如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云:“这一个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我预备叫它作《内篇》。此外,还有一个《外篇》,附在《内篇》之后。《外篇》是将历次散落在阁外的书,作一次总结账。”⑥冯贞群也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凡例》中专列一条:“海内外图书馆、藏书家收有天一阁书籍者,乞将书目、撰人、卷第、版本写寄,当入《外编》。”所谓《外篇》或《外编》,都是指天一阁流散书目录。可惜赵氏的《外篇》草稿已不可寻觅,而冯氏的《外编》至1962年其去世,也未能成书⑦。不过赵万里经眼的天一阁流散书有一部分留下了记录,即其《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云烟过眼新录》两文著录的一百十二种涵芬楼所藏天一阁佚书⑧。
注释:
①范彭寿《天一阁见存书目跋》,《天一阁见存书目》卷末,清光绪十五年无锡薛氏甬上崇实书院刻本。
②《嘉靖十一年壬辰科进士序齿录》范玉森跋,明嘉靖刻本,天一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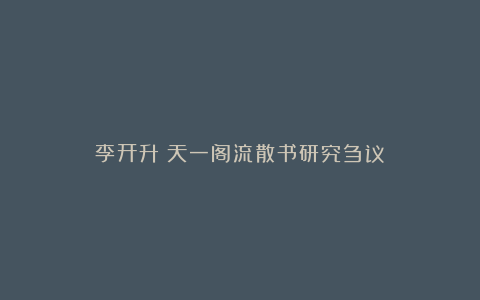
③《天一阁藏书史志》,第8页。
④骆兆平《天一阁散书访归录》,《文献》1990年第1期;又见《天一阁访归书目》,载《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第151-178页。
⑤补注:近年天一阁流散书访归工程启动之后,陆续访归明嘉靖刻本《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及明抄本《宸濠招》两书。
⑥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赵万里文集》第二卷,第476-477页。
⑦骆兆平《天一阁轶事》八《书目外篇和外编》,载《天一阁杂识》,第17-20页。补注:近年天一阁征得赵万里编目笔记本三册。
⑧赵万里《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赵万里文集》第二卷,第479-483页)著录二十六部,《云烟过眼新录》(《赵万里文集》第三卷,第404-414页)著录一百部,二者重复十四部,故合计一百十二部。
1964年,骆兆平以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名义致函国内著名图书馆,调查各馆所藏天一阁流散书情况,共得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十六部、上海图书馆十部、浙江图书馆四部、湖南图书馆一部、甘肃省图书馆二部和中山大学图书馆二部等六家合计三十五部阁书目录。另外大多数馆或者没有回复,或者回复未发现、未收藏①。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提供的均为地方志类文献,可能是整理、研究过这类文献,所以有其数据,不代表该馆其他类文献中没有阁书(实际上还有很多)。
1982年,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出版,著录了一百零五部流散方志的下落,即国家图书馆二十部(其中十部与前次调查书相同)、上海图书馆二十四部(其中十部与前次调查书相同)、台湾四十六部(前北平图书馆三十五部、前中央图书馆八部、前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三部)以及毁于战火的前上海东方图书馆十五部②。
1991年,蔡佩玲《范氏天一阁研究》出版,其中考察了天一阁部分流散书的流传情况:
今取诸家书目题跋中,录载有天一阁旧藏者,列述于下,并记所有数量,至于书名则暂阙不录:海日楼旧藏三十二种、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种、涵芬余录史八种、《适园藏书志》十种、《藏园群书题记》《续记》十种、《菦圃善本书目》二种、《著砚楼书跋》四种、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九种、《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一种、《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七种、《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二十五种、《双鉴楼善本书目》八种③。
主要是清末民国的藏书家,共计一百十九部。其所列只是举例性质,比较随意,如藏园与双鉴楼都指傅增湘,不应隔开;适园张钧衡、菦圃张乃熊为父子,其藏书有继承关系,也应放在一起。实际上各家之书也不能简单相加,有的可能是同一部书在不同藏家之间递藏,如适园与菦圃。虽然如此,蔡氏通过书目题跋考察流散书的方法还是可靠的,值得借鉴。蔡氏还通过比对《传书堂藏书志》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找出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春秋五论》等七部天一阁藏书④。
1996年,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出版,其中《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著录《皇王大纪》(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南城召对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三国杂事》(上海图书馆藏)三部流散书下落⑤。其中《三国杂事》今藏河南省图书馆,可能因河南省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代码相近而误⑥。又其中《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著录三十九部流散书下落,其中地方志五种与《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相同,浙江图书馆三部、中山大学图书馆一部,与1964年调查所得相同。此书著录明抄本《国初礼贤录》二卷藏于甘肃省图书馆⑦,实则天一阁藏此书有两部,一部是进呈书,一卷;一部未进呈,二卷。甘肃省图书馆所藏为进呈的一卷本⑧,已著录于《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著录的二卷本为未进呈书,非甘肃省图书馆藏本。2003年,沙嘉孙发表《传书堂所藏天一阁明抄本考——兼补〈新编天一阁书目〉之阙》一文,辑录蒋汝藻传书堂所藏天一阁旧藏明抄本110部,并与《新编天一阁书目》相校⑨。
注释:
①骆兆平《天一阁散存书的首次调查》,《天一阁杂识》,第46-49页。
②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前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iii页。
③蔡佩玲《范氏天一阁研究》,第72页。
④蔡佩玲《范氏天一阁研究》,第71页。
⑤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第191、196、218页。
⑥河南省图书馆代码“二二〇一”,上海图书馆代码“〇二〇一”,容易混淆。
⑦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第279页。
⑧杜泽逊《跋天一阁进呈四库馆明钞本〈国初礼贤录〉》,《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年第2期。
⑨沙嘉孙《传书堂所藏天一阁明抄本考——兼补〈新编天一阁书目〉之阙》,载《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322-337页。
2009年,柯亚莉博士论文《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研究》通过答辩,其附录二《天一阁散出之明代文献知见录》著录海内外二十二家藏书机构收藏的天一阁流散书四百八十五部,为目前所知数量最多的流散书目录。柯文成绩最大也是最费力处是考察清楚这些书藏于何馆。以进呈书为例,骆兆平《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有藏地者五部(其中二部已访归),柯文可增补十八部。不过因柯文限定在“明代文献”,许多非明代文献未能进入目录。另外,柯文对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成果的利用也有不充分之处,如骆书著录之方志未标明“散出”而该方志一部分在天一阁、一部分散归其他藏书机构者,柯文多未吸收,如《处州府志》《宁国府志》《灵宝县志》等。柯文还对阁书流散线索和途径进行了深入考察,分为进呈本的散出、在宁波当地和散出和在上海的散出,对法式善、卢址、吴引孙、蒋汝藻、刘承干等二十多位藏家收藏阁书的情况一一作了具体分析,理出了阁书流散的几条主要线索①。这方面研究的价值不局限于明代文献,对非明代文献一样适用。
2010年,李开升发表《黄裳所藏天一阁藏书考》一文,搜集黄氏收藏过的八十一部天一阁流散书,分别考察每一部书的递藏源流和最终下落。最终结论是,三十二部在上海图书馆(其中个别待核),二部在国家图书馆,一部在南京图书馆,一部为天一阁访归,十八部仍在黄裳家。另有二十七部情况不明②。这是专门研究某一藏书家所藏阁书的开始。2013年,刘云发表《傅增湘经见天一阁佚书考》一文,搜集傅氏经见经藏天一阁佚书九十六部,其中可考见者四十二部,十五部在国家图书馆,四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十五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四部在台湾汉学研究中心③,一部在台北傅斯年图书馆,三部为天一阁访归④。2016年,刘云发表《嘉业堂经藏天一阁佚书考——兼论天一阁藏书流散港台之经过》一文,考出嘉业堂藏阁书八十二部,其中考出现藏地者:台图二十八部、台北傅斯年图书馆三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七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一部、浙江大学图书馆二部⑤。
2016年,骆兆平发表《天一阁流散书寻踪》一文,考察十三家的十五种书目中的天一阁流散书。其中最多的是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的一百十二部,即上文中赵万里两文所收录者。其次是嘉业堂的二十一部、涵芬楼的十部、江南第一图书馆的七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六部、张寿镛和郑振铎的各五部、吴引孙、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和萱荫楼的各二部、周越然、天津图书馆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各一部,共得一百七十五部⑥。不过其中不同藏家个别藏书有递藏关系,如吴引孙所藏《春秋五论》即涵芬楼之《春秋五论》,所以实际总数不足一百七十五部。
注释:
①柯亚莉《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研究》,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4-65页。
②李开升《黄裳所藏天一阁藏书考》,《天一阁文丛》第8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26页。
③按所谓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所藏三部《太平御览》《云溪友议》《伯生诗续编》,经查,均为台图藏书,索书号分为07821、08262、10914,盖汉学研究中心即台图主办。
④刘云《傅增湘经见天一阁佚书考》,倪莉、王蕾、沈津《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69-589页。
⑤刘云《嘉业堂经藏天一阁佚书考——兼论天一阁藏书流散港台之经过》,载《饶学与华学——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十周年庆典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606-615页。
⑥骆兆平《天一阁流散书寻踪》,载其《天一阁杂识》,第229-249页。
四
天一阁流散书微观研究的成果需要进一步整合并继续加深研究力度和扩大研究范围,以期勾勒出天一阁藏书的全貌和其流散的全过程。宏观研究中疑难的解决,比如五劫说的第一劫究竟如何、能否成立,也需要微观研究数据的支持。
从基本逻辑看,如果把藏书流传过程看成一条线的话,它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头、尾和中间。“头”是源头,是天一阁。“尾”是当今的各个藏书机构(包括个别私人)。“中间”就是藏书从天一阁散出之后,到达今天各个藏书机构之前,所经历的诸多藏书家。因此,总结天一阁流散书研究的历史,结合藏书流传研究的一般方法,下一步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一)从天一阁这个源头出发,将历代的天一阁书目进行全面整理,奠定考察、研究天一阁流散书的基础。天一阁民国以前的各种书目不下二十种,这是有关天一阁流散书的最完整、最可靠的记录。当年冯贞群、骆兆平两先生编纂《天一阁书目外编》就是从互校、整理书目开始的①。将这些书目互校,拼合成一个最完整的目录,去掉其中天一阁现存的藏书,剩下的就是流散书,然后再补上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原目遗漏之书即可。这个基本思路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以宋《目》为例,其编纂年代、编纂体例等都有待研究。如书中的“册”、“套”等量词的具体含义与今天有很大区别,如果不加分析,对统计其著录书籍的数量会有很大影响,导致数据不准确。再如国家图书馆藏所谓介夫抄本《天一阁书目》,原来对其抄写者介夫及题跋者芝栭翁的身份都不甚清楚。现在我们通过初步考证,知道介夫即旗人舒木鲁明(图5,此目下简称舒《目》),芝栭翁为江都人程式庄。台湾藏有舒《目》的另一个本子,虽然初步判断是国图本的传抄本,价值有限,但其两序完整无缺,可补国图本序的十余个缺字。这些对深入研究舒《目》并判断其价值有重要作用。此外,天一阁原来使用的宋《目》和舒《目》都是天一阁藏传抄本,传抄就会有讹误,如舒《目》制书类“《皇明泳化类编》”,阁藏传抄本误衍“类”字。又阁藏传抄本诸经类第五叶与第六叶之间误脱一叶,而此叶著录了三十六部书,显然会对统计收书数量产生不利影响,甚至还会进一步影响对宋《目》和舒《目》关系的判断。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书目上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目前专门研究具体某一部天一阁书目的论文几乎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强。
注释:
①骆兆平《天一阁轶事》八《书目外篇和外编》,载《天一阁杂识》,第17-20页。
图5 清舒木鲁明抄本《天一阁书目》
对各书目之间关系或者整个天一阁书目体系的研究也需要加强。民国以前的天一阁书目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整体性的目录,以全部阁书为著录对象,如前述宋《目》、舒《目》、阮《目》等均是。另一类是专题书目,主要有进呈书目和失窃数目。整体性目录从体例上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旧的账簿式目录,主要包括宋《目》、舒《目》和罗振玉刻《玉简斋丛书》本《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下简称罗《目》)。这类书目的主要特点是只著录书名和册数,具有账目的性质。其分类或者是明代流行的分类法,以制书为首,以下采用大体按四部顺序但部类远远多于四部的多部分类法,如宋《目》、舒《目》;或者干脆不分类,直接按书橱排架顺序来,如罗《目》。另一类是以阮《目》为代表的新的四部分类法目录。所谓新,不是指四部分类法新,而是指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四库总目》的出版,四部分类法在目录编纂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此后的书目很少不用四部分类的。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不同书目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识,从而可以更好地对不同书目互校、整理。比如账簿式目录由于性质相近,可以按其性质进行互校,更容易发现问题。如宋《目》制书类《东汉诏令》缺册数,可以用罗《目》补足。
(二)全面整理历代藏书家书目中著录的天一阁藏书。此前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如吴引孙测海楼、张钧衡适园、张乃熊菦圃、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等家书目,均曾涉及。不过这方面工作还不够深入,有的只是举例性质,连书名也未列出,后来者不得不重新再做一遍。有的也只是就手边易得的目录查一下,没有更全面地调查该藏书家的所有藏书目录。对一家所藏阁书进行穷尽式研究的目前还只有黄裳、傅增湘和刘承干三家,在天一阁藏书流散史上影响很大的藏书家如蒋汝藻密韵楼、李盛铎木犀轩、许厚基怀辛斋等诸家都还缺少深入全面的研究。
这种研究看起来似乎只是翻检书目的体力活,实际上也有诸多困难。首先要求对藏书史非常熟悉,不仅是天一阁的藏书史,所有收藏天一阁藏书的藏书家的历史源流也要了解。不仅要了解宏观的藏书史,而且要对具体的藏书有所了解和鉴别。诸家藏书纵横交错,藏书家们像藏书长河中大大小小的节点一样,其藏书之间互相纠缠,不易区分。有些书似异实同,有些似同实异。有些可以通过比对书目判断,有些则必须通过实物才能解决。有时候判断一个问题是应该用目录来解决,还是应该用实物来解决,也需要相当的学术鉴别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版本目录学的许多课题,研究对象经常是数十乃至成百上千的书籍,与侧重文本内容的研究一般只重点针对一、二部书不同。这种研究分到每一部书上的精力常常比较有限,这对学术鉴别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才能尽量避免错误。
(三)广泛调查当今各大藏书机构中的天一阁藏书。上文提到以前曾使用函调方式向各图书馆调查阁书,取得了一定成果。不过总体来看,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受局限的。首先,这种调查不同于一般的调查事务,本质上属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问题很少能通过函调方式解决的。其次,收藏有天一阁藏书的一般都是古籍收藏比较丰富的较大的图书馆,这样的图书馆不论是古籍工作还是其他业务工作都比较多,对于从千万古籍中调查出天一阁藏书这样业务性、学术性比较强的工作,不太容易从日常工作中专门安排出时间来做。最后,作为一项学术工作,不仅需要专业人才,而且只有对此有所研究的专业人才才能胜任愉快。对于其他图书馆来说,不见得有这种人才储备。
这项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做好前面两项工作,天一阁书目整理出来,才能大致框定调查的书目范围。重要古籍图书馆藏书规模庞大,不可能每一部都看。整理藏书家收藏的阁书,根据其藏书的流散情况,追踪其去向,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去相应图书馆调查。其次,对各大图书馆公布的网络数据要密切关注并及时了解。近年来,海内外古籍数字化工作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古籍收藏机构将所藏古籍扫描成电子数据,有些已在网上公布。如台湾、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公布了许多古籍数字资源。中国国家图书馆近年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陆续公布了两万余部古籍数字资源。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必能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以上三大方面,还可以展开一些专题研究。如流散地方志的研究,《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值得借鉴学习。另外如流散科举录研究、进呈书研究和失窃书研究等,都是值得专门探讨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