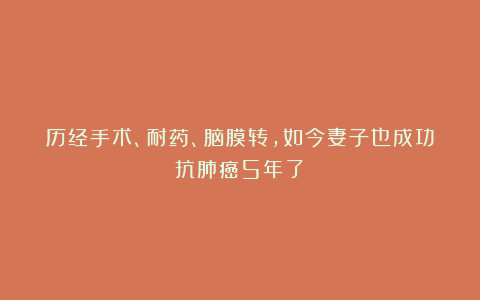作者:老般
一次体检,妻子确诊肺癌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20年12月。我们一家刚结束了云南大理、昆明、丽江的旅行归来。
爱人虽然刚退休,但依然闲不住。她在早教行业深耕多年,并未因退休而停下脚步,很快找到了一份相关工作。
入职前例行体检中,X光片上一处异常引起医生高度警觉,他们请求提供家属的紧急联系信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照做了而已。直到接到电话,我才知道爱人在右肺有一块阴影,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尽快复查确诊。
那一刻,我内心五味杂陈,难以置信。因为以下几点让我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
我的妻子一直是个极其自律的人,她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保健与养生的小习惯。
-
在过去的岁月里,除了生育那次不得不入院外,她几乎未曾有过任何身体不适的经历。
-
即便是小到一场轻微的感冒,她也总是选择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恢复健康。
-
她身材小巧玲珑,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始终保持着健康的体魄,疾病似乎从未靠近过她。
于是,我们首先去了青岛的齐鲁医院。当时因为刚刚开始疫情管控很严格,对于住院病人有诸多要求,其中就包括限制陪伴人员的数量。但是不得不说,那时的青岛齐鲁医院和济南齐鲁医院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或许是因为当时对癌症不够了解,当青岛齐鲁医院建议进行PET-CT检查时,我们立即同意了。那次检查的费用至少需要8000多元。是家外联公司,然而,检查结果显示:肺部肿瘤已经发生了全身广泛转移。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因为患者本人并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感,日常生活也与常人无异,这样的诊断结果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随即在青岛齐鲁医院挂了个胸科专家门诊,然后得到的结论是癌细胞已经广泛转移了,需要保守治疗,也就是化疗。其关键点是右肺上叶有超过鹌鹑蛋大的磨玻璃结节,左侧颈部有一个结节,不排除广泛转移。结果是在青岛齐鲁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然后进行确诊。然而,可笑的是,做了两次支气管活检,结果却未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导致无法确诊。病人遭受很大的痛苦。
当时孩子正在上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在青岛,也没什么其他亲戚。于是和几个朋友讨论,咨询相关问题。潍坊的堂弟是当地医院的麻醉科主任,比较了青岛和济南的医院的医德医风,建议我去济南检查一下确诊。
手术带来治疗希望
邻居朋友的父亲肺癌晚期,存活超过十年,能够正常地接送小孩。于是我向他请教,他给我们这样说的:能手术就手术,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这在我整个治疗期内起了关键作用。不管是以后的治疗中,还是脑转过程中,这位朋友的建议都起了很关键的指导作用。
因为当时爱人的状态和正常人一样,我心里想着,这可能是个误诊。抱着这种心态,我们在济南齐鲁医院多学科会诊、齐鲁医院胸外科、省立医院胸外科、省胸科医院、还有山东省肿瘤医院,分别挂了5个专家号。然后我和家属开着车,带着片子去济南。
齐鲁医院胸外科专家田辉教授,当时齐鲁医院副院长他直接就说,PET-CT显示结果广泛转移是错误的,病人是有手术机会的,肯定是要做手术的;齐鲁医院多学科会诊带头人刘延国教授不确定这左侧颈部的结节是否和右侧的病灶有关联;省胸科医院的医生说,从生理上讲病灶区和左侧的淋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不可能是扩散;最关键的一点是省立医院的胸科主任,他直接就说,右侧肺叶的阴影不管是恶性的,良性的,还是结核都应该切除 ,都那么大了,对病人是没有坏处的。从而坚定了我们一定要做手术的决心。
在齐鲁医院办理好住院手续时,已是2020年底,2021年1月9日就做手术,在济南齐鲁医院胸外科住院手术前,同样做了经支气管镜活检。检查成功,确诊为肺腺癌。当时还担心活检刺激和种植癌细胞,现在想想很可笑。没有活检,就没有办法确诊,就没办法后继治疗,但是不同医院之间的医疗水平和技术存在显著差异。
术前与主治医师及田辉教授的得意门生岳韦明医生进行了深入交流。选择的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手术,并提出了两点具体要求:一是彻底清扫胸腔内的所有淋巴结;二是尽可能保留健康组织的前提下,切除病变部位的肺叶。当时在山东省内,仅有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和齐鲁医院的田辉教授掌握了这项技术。
整个手术过程顺利地清除了胸腔中的29组淋巴结并切除了右侧上叶肺部。同时对这些淋巴结进行了病理学检测以确认是否有转移情况发生。最终结果显示仅在纵隔上的三组淋巴结中发现了少量癌细胞的存在。
术后两个月找田辉教授复查,得到的结果是手术很成功,病人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很满意。手术虽然很成功,我个人认为仅仅是切除了病变组织,病人并没有进行任何治疗,人体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切除了病灶病情就万事大吉。病人现在应该去肿瘤内科确诊一下,是否还需要继续接受治疗。
于是我联系了当时在齐鲁医院负责多学科会诊的刘延国教授。他是齐鲁医院肿瘤内科的主任,我想听听他对病情的看法。
当他看了检查报告之后说:“纵隔上测到了癌细胞,这说明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了。癌症分期已经达到了3A,对于癌症这种疾病,患者必须得接受系统的化疗,并且要进行更深入地治疗。”同时也给我们做了基因检测,发现我们有靶点,符合吃靶向药的条件。
2021年4月起,我们进行了四个疗程的化疗。随后,我们的癌胚抗原指数从手术后的100多降至正常范围内的5。刘教授表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治疗,并为我们开了第三代靶向药物——奥希替尼。让我家病人每天服用1粒,自此之后,我们就一直服用这种靶向药。奥希替尼带来最大的副作用就是甲沟炎和皮疹,很多时候,疼的走不了路,但是也得受着。我们一直吃了28个月的奥希替尼,期间每3个月到齐鲁医院复查一次,每个月在当地医院检查一次血象,检查一次癌胚抗原的指标,做一个记录。
说几个题外的话,首先我家病人在生病期间,有亲戚朋友介绍吃中药,还有就是提供各种偏方,我个人认为好的中医药,好的中医医生都是有的,但是和我们目前没有缘分,所以我们没有进行过中医治疗,都是按照齐鲁医院肿瘤内科刘延国教授的规范治疗进行治疗的。病人保证了生活质量,济南齐鲁医院不愧是行业楷模。
耐药出现,凶险的脑膜转移袭来
时间到了2023年12月,是我们每三个月复查的时候。事后考虑服用第三代靶向药的病人,生存期延长,由于血脑屏障,造成靶向药物突破不了,会形成脑转,这个概率在第三代靶向药治疗过程中随生存期延长,脑转也相继增多。
这时候,我家属每个月的癌胚抗原指标检查中已经发现,原本3、40的指标已经上升到100多,但每隔三个月的复查增强CT和增强核磁都没有发现问题,这时,她偶尔会有呕吐现象,并且说头痛,但并不严重。
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靶向药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在服用了28个月的奥希替尼之后,出现耐药性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在12月底前往齐鲁医院找主治医生进行诊断。在去济南齐鲁医院过程中,病人多次呕吐并且感到极度不适,耳鸣眼花,病情十分危急。
到达济南齐鲁医院后,主治医生怀疑是靶向药产生了耐药性,于是再次进行了基因检测。虽然靶点仍然存在,但对于奥希替尼这种靶向药不再敏感,主治医生建议尽快更换另外一种第三代靶向药。首先尝试的是阿美替尼,然而使用后患者出现了血压压差非常大的症状,高压到180,低压40,她差点崩溃并且感觉非常不舒服,由于副作用过于强烈,只好停止用药并改为伏美替尼,不过使用伏美替尼正常剂量也没有明显的效果。
此时已经是2024年的元旦假期。尽管各项检查均未发现问题,患者的症状却愈发严重:频繁呕吐、眩晕乃至短暂失神的情况时有发生,并且无法下地行走。对此主治医生高度怀疑发生了脑部转移(即“脑转”),但由于尚不清楚具体原因故而安排做腰椎穿刺抽取脑脊液以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肿瘤细胞扩散的问题。
恰逢新年之际全院上下都在休假之中,唯独负责治疗我家患者的刘姓主任医师克服困难坚持返岗为患者实施诊疗工作,其敬业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最终经由脑脊液化验确认其中含有恶性肿瘤细胞从而明确诊断出系大脑广泛性软脑膜转移所致,随后刘教授正式下达了病危通知单。
这时候的病人已经无法下床,睁不开眼,说眼睛闪光;听不见声音,说耳朵轰轰的,体重眼见下降,走路在正常情况下是东倒西歪的。接到主任的病危通知让我签字时,感觉很可怕:颅压过高,一天三袋甘露醇注射,吃什么吐什么,并且随时可能会形成脑疝,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作为家属的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没有碰到过这种事。包括病人和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当时孩子在国外,知道他妈妈很痛苦。但是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及时回来,我只能一个人面对。回想当时的情景,我选择信任给我家病人治疗近三年的刘延国教授,这一点是后期治疗的关键。
在我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刘教授告诉我建议给患者安装一个叫做“Ommaya囊”的东西,否则一旦发生脑疝,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刘教授近三年对我家病人的治疗,所以我对他产生了信任。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很明白这个“安囊”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仍然决定要信任这位医生,并且我相信我的主治医师刘教授。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系到了神经外科的主任,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为我们家的病人完成了这项手术。这次经历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非常安心。
然而,在安装完那个装置之后,患者的病情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她依然无法正常进食,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虚弱。但幸运的是,她内心深处的那种强烈的生存欲望让她即使知道食物可能会被呕吐出来,也会坚持尝试去摄入一些营养物质。看到这里我也很心疼,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法。
但由于齐鲁医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并不具备针对这种特殊病症的专业科室来进行全面有效的诊治工作,因此我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的帮助。
这时我在网络上偶然发现了一篇关于山东省肿瘤医院化疗科胡旭东主任的文章,并决定向他求助。当我来到这家专科医疗机构并向胡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与人文关怀精神。经过详细询问及评估后认为该病例适合由他们院内专攻神经系统肿瘤的神经外科接手处理,并立即开通了绿色通道以便我能尽快带病患前往接受进一步检查与治疗建议。”
在胡主任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省肿瘤的神经外科病房。当时我家病人头上在齐鲁医院的手术线还没有拆,就从囊中抽取脑积液,进行颅压测试,发现颅压没有那么高,只有180,就没有进一步治疗,只做了一次十毫升的培美注射治疗。
在这里又碰到好医生,神经外科朱主任。朱主任是一位说话慢条斯理的和蔼可亲的医生,我家病人是被担架抬到病房里的,当时护士还检查她身上有没有褥疮,病人已经瘦的就剩下一副骨架,也不愿说话,也不愿意动。朱主任哄着逗着想着办法让病人说话,配合治疗,这时候已经是2024年1月17号,我已经20多天在医院睡铁凳床了,也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所以朱主任建议我们先回家,然后再回来检查是否做脑室分流手术。
在肿瘤医院住院两周后,我们出院回家过年,我便把车后座打平,放上床垫,让病人平躺着回家。一直等过了2024年2月19号又到了山东省肿瘤医院,进行了脑室分流的手术。
回到青岛期间,不得不说,因为安囊要做鞘注,开始是7天做一次鞘注,结果在青岛跑了好几个三甲医院,包括青岛市肿瘤医院,竟然没有任何三甲医院能够做鞘注治疗,后来在城阳找到一家医院可以做,可见鞘注治疗估计是麻烦,利润小,很多医院看不上,一开始几次鞘注不得不青岛、济南来回跑,就做十几分钟的治疗。
脑室分流手术,非常神奇。病人第二天就说眼睛不闪了,耳朵也不轰轰响了,也想吃东西了,整个人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后来很多病友问我,安囊会不会感染?做脑室分流手术会不会把癌细胞种植到腹腔里?这时我只能苦笑,我想说的是,做任何手术都有感染的风险,因此消毒必须严格规范,如此才能减少感染概率。至于种植腹腔的问题,病人的生命已经时倒计时了,做脑室分流手术本身就是提高病人生存状态,不让病人太痛苦,难道病人痛苦是靠意志抵消?此时你还考虑种植这种风险吗?
做完脑室分流手术临出院时,朱主任很平静地说:脑转移的病人,特别是有脑膜转移的,生存期基本上只有四至六个月,要做好心理准备。安囊只是基本的救治手段,脑室分流也只是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手术,并不对疾病的治疗起作用。
我心里也很清楚脑转患者的存活时间是以月来计算的。能多活一个月是一个月,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自二月十九日出院以来,病人逐渐好转。到了四月份,她让我驾车从青岛前往郑州的老家给父母扫墓;又去了她曾工作过的单位以及学校门口吃她童年时期最爱吃的烩面。虽然我很担忧但还是选择尊重他的意愿陪她一起去。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整个旅途中她一次都没有呕吐过!后来我知道这是我家病人给自己立下的遗愿清单上的事情。
时间就这么慢慢地走着,我家病人从脑转移到现在10月份已经有22个月了。鞘内注射的周期从最初的一周一次逐渐延长到了两周一次,再后来又延长至三周一次,直到现在变成一个月一次。病人的癌胚抗原(脑脊液)指标也从最开始的三百多降至现在的8.86。
前路漫漫,仍要前行
自去年五月起,病人开始尝试外出旅行。至今为止,她每个月都会抽出十几天的时间出游。一方面是为了品尝各地的特色美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欣赏各地的美丽风光。不管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病人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像个正常人一样。
我认为病人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充足且有营养的饮食是与疾病做斗争的关键,作为病人家属,虽然我们无法保证病人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让她感受到生活的质量。
我和朱主任沟通过,他觉得像我家病人的生存状况是比较少见的。许多病情发展到现阶段的患者要么选择化疗,要么拒绝化疗,或者因身体虚弱而行动不便,大多数时间只能待在家里。像她这样还能四处游玩的确比较罕见。
借此机会,我想对我所遇到的所有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包括齐鲁医院的医生、山东省肿瘤医院的胡主任,以及其他参与我家人治疗的朱主任。我们将继续努力提升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延长其生命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