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4 13:29
1940年2月的晋察冀军区,哨兵刚换岗没多久,就发现驻地里少了一串熟悉的脚印,一分区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带着侦察科长袁彪和37名战士,背着武器消失在夜色里。
这事像块石头砸进沸腾的油锅,军区作战室的灯光亮了一整夜,参谋们在地图上圈出可能的路线,谁也没料到,7天后的黎明,浑身是泥的杨上堃会独自跪在司令部的石阶上,冻得发紫的嘴唇里反复蹦出一句话:“让我回部队,干啥都行,哪怕扛枪站岗。”
1935年1月的乌江,红4团连续两次强渡失败,岸边临时搭起的棚子里,伤员的呻吟声压过了风声。杨上堃蹲是红4团2连的一名排长,刚从前线抬下来,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渗血。
“再试一次!”连长熊尚林说,杨上堃“腾”地站起来,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我跟你去!”这一次,17名勇士挤上仅有的3只竹筏,杨上堃攥着步枪蹲在筏尾,怀里揣着指导员王海云塞给他的半块干粮。
竹筏刚划到江中心,对岸的机枪就像疯了一样扫射,身边的战士小张猛地晃了一下,半个身子栽进水里,杨上堃伸手去拉,只抓到一把冰冷的江水。他红着眼吼了一声,抓起筏上的手榴弹咬开引线,朝着火光最亮的地方扔过去。竹筏被急流冲得打转,他干脆跳进水里,推着筏子往对岸石崖游,冻得僵硬的手指死死抠住岩石缝,指甲缝里全是血。
登上北岸时,17人里已有4人倒下,杨上堃抹了把脸上的血水,跟着战友们扑向敌军的碉堡,等后续部队冲上来时,他正靠在碉堡墙上喘气,身边堆着缴获的弹药,远处传来司号员吹的冲锋号,像在给牺牲的战友送行。
这场仗打完,红4团给2连记了集体大功,杨上堃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军团的战报里,评语是“敢打敢拼,轻伤不下火线”。
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漫山的枫叶红得像火,杨上堃趴在一棵老松树下,看着日军指挥官的身影在山坳里晃动。他当时是支队的一名营长,手里攥着3颗手榴弹,等着总攻的信号。
这场仗打得漂亮,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军区炮兵营的炮弹击中,消息传来时,阵地上的战士们举着枪欢呼,杨上堃把帽子扔到天上,又捡起来紧紧攥在手里,这是他参军8年来,见过最解气的一次。
因为在黄土岭战役中带头冲锋,杨上堃没多久就被提拔为支队参谋长,可这个新岗位,让他浑身不自在。
作战会议上,参谋们说的“兵棋推演”“侧翼警戒”,他听着像天书。一次讨论伏击方案,他把“佯攻牵制”理解成了“全力冲锋”,差点让两个排钻进日军的包围圈,幸亏副参谋长及时发现,才没造成损失。
“上堃,咱是拿枪杆子的,不是耍笔杆子的。”袁彪的话像根草棍,总在他心里搅。
那段时间,杨上堃总失眠,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眼前一会儿是乌江的浪,一会儿是作战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
1940年2月17日晚上,袁彪又来找他,手里拿着两张偷偷画的路线图:“往南走,到保定那边找个地方落脚,总比在这儿受气强。”
杨上堃盯着油灯看了半晌,脑子里突然冒出个荒唐的念头,他借着查岗的名义,集合了37名战士,说要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队伍走出驻地三里地,他才发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寒风里,战士们背着的枪上还挂着军区的徽章,那是他亲手给大家别上的。
离开驻地的第三天,队伍在一道山梁上歇脚,袁彪正对着地图比划,说再走两天就能到封锁线,杨上堃却盯着远处的山影发愣。那山形像极了乌江岸边的崖壁,他突然想起强渡乌江时牺牲的小张,那孩子才16岁,临死前还喊着“排长,我爹是佃农,等胜利了替我看看他”。
“不能走了!”杨上堃猛地站起来,声音在山谷里打了个转。袁彪瞪起眼睛:“参谋长,你疯了?现在回去就是找死!”
杨上堃没理他,转身对战士们说:“是我糊涂带错了路,要走你们走,我得回去。”
有几个战士犹豫着站到他身边,袁彪骂了句“傻子”,带着剩下的人往南走了。
杨上堃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树林里,突然朝着驻地的方向跪了下去,额头磕在冻硬的地上,“咚咚”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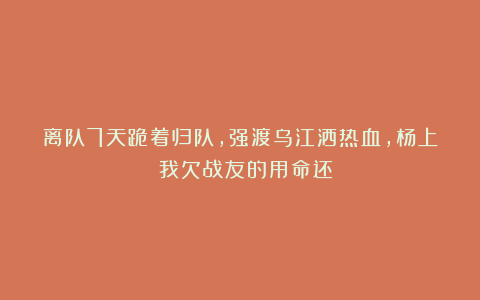
他带着愿意跟他回来的6名战士,沿着来时的脚印往回走,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抓把雪,脚上的草鞋磨穿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
第七天清晨,他们终于看到了军区的岗楼,杨上堃让战士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解开棉袄,露出肩头在乌江留下的伤疤,跪在雪地里,哨兵吓坏了,赶紧去报告。
没多久,政治部主任匆匆跑出来,看着他冻得青紫的脸和渗血的肩头,叹了口气:“先起来,有话进屋说。”杨上堃却不肯起:“主任,我犯了错,该咋处置咋处置,只求能留在部队,哪怕给牺牲的战友守坟。”
杨上堃归队的消息传开,军区大院里炸开了锅。有人说:“战时离队就是投敌,不严惩以后队伍没法带。”也有人念叨:“他打乌江的时候命都不要,这次说不定是一时糊涂。”党委扩大会议开了整整三天,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
作战处长拍着桌子站起来:“37个人带枪离队,这要是让敌人钻了空子,咱们多少同志得遭殃?军法面前没例外!”坐在对面的组织科长慢悠悠地说:“他要是真想叛逃,何苦冒着死回来?再说,他主动把人带回来6个,说明心里还有组织。”
杨上堃被喊进会议室时,腰杆挺得笔直。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是枚磨得发亮的铜质奖章,那是1935年红4团给作战勇猛的战士发的,上面刻着“奋勇”两个字。“这奖章我不配戴了,”他把奖章放在桌上,“但我这条命是红军给的,让我干啥都行,只要能赎罪。”
最后,军区党委拍了板:给杨上堃留党察看一年,撤去参谋长职务,调到涞源县后方医院当担架队队长。
宣布决定那天,杨上堃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谢谢组织给我机会,我杨上堃要是干不好,不用组织处置,自己跳山崖。”
后方医院的院子里,担架队员们第一次见杨上堃时,都有点发愣——这就是传说中打乌江的英雄?咋成了抬担架的?杨上堃没在乎这些眼光,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检查担架,把绑带捆得结结实实,还跟老队员学怎么在山路上稳当抬人。
1941年秋天,日军“扫荡”来得特别凶,医院要往深山里转移,杨上堃带着23名队员,抬着40多名重伤员在山里绕。
有天夜里,他们被日军堵在一道峡谷里,前面是悬崖,后面是狗叫声。杨上堃把伤员安顿在山洞里,对队员们说:“我带两个人引开敌人,你们天亮前把伤员转移到东边的山神庙。”
他带着队员小张、老李,故意在雪地上踩出一串脚印,朝着相反的方向跑。日军的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老李的腿被打中了,杨上堃背起他就跑,跑着跑着脚下一滑,两人滚进了雪沟。
等日军走远了,老李咬着牙说:“队长,你别管我了。”杨上堃掏出绷带给他包扎:“当初在乌江,战友们没丢下我,今天我也不能丢下你。”
他们在雪地里爬了半夜,终于赶上了大部队。当队员们看到杨上堃背着老李,浑身是雪和血时,没人再把他当“犯过错的干部”,都喊他“杨大哥”。那一次,40多名伤员一个没少,杨上堃却累得吐了血,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1943年春天,杨上堃听说军区要组建冀中武工队,立马找领导请战,“我知道自己以前犯过错,”他把请战书递上去,“但打鬼子我熟,让我去最前线,死了也值。”领导看着他眼里的光,点了点头:“去了就好好干,别让人戳脊梁骨。”
武工队的日子比抬担架苦多了,白天藏在老百姓家里,晚上出来摸鬼子的据点。杨上堃记性好,把保定到石家庄的铁路沿线摸得门儿清,哪个炮楼有多少人,哪段铁轨好炸,都记在心里的“活地图”上。
有次他们要炸日军的运粮列车,杨上堃带着队员扮成修路工,趁着夜色把炸药埋在枕木下。列车开过来时,他拉响引线,自己却没跑,有个队员的脚被铁轨卡住了,他冲回去把人拖了出来,两人刚滚到沟里,列车就“轰隆”一声炸成了火球。
当地老乡后来编了段快板:“杨队长,胆子大,铁轨上面安’西瓜’(指炸药);鬼子车,过不去,粮食全归咱庄稼娃。”杨上堃听了总摆手:“不是我能耐大,是大伙心齐。”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带的武工队炸毁日军列车12列,端掉据点5个,被冀中军区记了集体二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杨上堃回到了江西老家,在赣州军分区当司令员。1969年,组织上要派干部去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他又第一个报了名。“我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他跟家人说,“但开荒种地我会,去给国家多打些粮食。”
闽西的荒山上,石头比土多,杨上堃带着战士们用钢钎凿石头,用箩筐运土,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有次挖灌溉渠,遇到块大岩石,炸药都炸不开。他蹲在石头旁看了半天,让人找来几根木头当撬棍,喊着号子带头使劲,硬是把石头挪开了。
副团长劝他:“您都五十多了,这些活让年轻人干。”他抹了把汗:“当年在乌江,五十多岁的老船工还撑筏呢,我这算啥?”
在福建的10年,他带领大家开出5000多亩良田,建起3个水电站。战士们说:“杨副司令的脚印,比地里的垄沟还密。”1979年他离休时,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城里房子,就在农场附近住了间平房,每天还去地里转一圈,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
1982年,组织上按政策给杨上堃定了正军职待遇,他拿着通知看了半天,对来看他的老战友说:“我这条命早该在1940年就没了,能活到现在,还能领国家的工资,知足了。”1984年春天,他病重住院,弥留之际,拉着儿子的手说:“把我那枚’奋勇’奖章捐给纪念馆,告诉后人,别学我犯糊涂,要对得起身上的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