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改革”二字遮蔽的吃人现场
“改革”一词在汉语里自带光环,仿佛只要把它贴在任何旧屋的破门上,就能瞬间化腐朽为神奇。但历史给出的冷酷注脚是:在一条从根上烂起的链条里,每一次“自我改革”都不是在除锈,而是在给锈迹涂上一层更亮的漆,好让链条多勒住脖子一会儿。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乃至晚清的洋务派,他们的悲剧不在于“失败”,而在于被后世误读为“差一点成功”。这种误读本身就是制度吃人的延伸——它让旁观者继续相信:只要再来一次更聪明的改革,老屋就能自动长出钢筋。于是,下一轮吸血开始,新的改革者被奉上祭坛,旧结构则在悼词里获得永生。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二、“自我改革”是一个语义悖论
逻辑上,“自我改革”等于“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封建王朝的合法性叙事建立在“天命—礼教—特权”三位一体之上,三者互为护城河。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拿什么去补偿被剥夺特权者?在产权与暴力都高度垄断的语境里,答案只有一个——“拿未来补偿”。
王安石给士大夫画的大饼叫“国富民强”,但“国富”首先意味着皇权更大程度地汲取社会;“民强”则要求士大夫让渡土地与劳力的控制权。两边同时预支的是一个无法被量化、更无法被担保的“未来”。
当贴现率高于收益率,理性人必然选择杀改革者祭旗,以终止游戏。于是,“自我改革”在语义层面就破产了:它既无法给出现实对价,也无法签署可执行契约,只能靠“青苗钱”、“免役金”这类临时性转移支付拖延危机。拖延不是失败,而是制度按既定剧本的狂欢。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三、胥吏:被忽略的“第二政府”
传统叙事把改革失败归咎于“顽固派”,仿佛只要把司马光、倭仁们搬开,历史就能顺风。真正杀死变法的,是遍布州县的“第二政府”——胥吏集团。
他们不入流品,却垄断信息;没有俸禄,却掌握执法;表面听命于官,实际与豪强共舞。用现代术语,他们是“制度性套利者”:把任何自上而下的政策,都拆分成可变现的寻租指标。青苗法被改造成强制贷款,免役法被加价成“赎身费”,一条鞭法被层层加码成“火耗银”,都不是执行“偏差”,而是制度赋予他们的隐性分红。
换言之,封建王朝的日常治理,就是靠把正式权力“外包”给非正式集团,以换取他们对皇权最低限度的忠诚。改革者想跳过这个“外包层”,等于同时得罪皇帝、官僚、士大夫与地头蛇,四面楚歌是注定的。被忽略的残酷真相是:胥吏不是“败坏”了改革,而是让改革回归了制度的“正常态”——吃人。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四、洋务运动:技术换皮下的权力原教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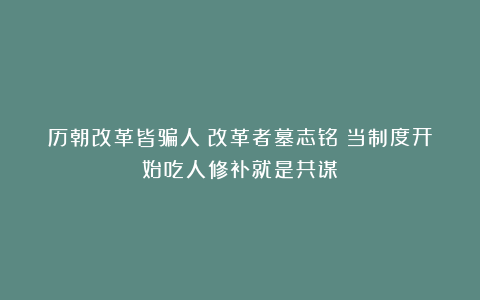
很多人把甲午战败归咎于“器物不如人”,却选择性遗忘:北洋水师成军时,纸面战力高于日本联合舰队。真正导致溃败的,是每发炮弹都要按品级分包的“跪拜式后勤”。
封建权力逻辑对技术现代化的“兼容度”极低:它允许你买军舰,但必须由皇亲国戚的管家去采购;允许你练新军,但士兵必须先学会跪。于是,技术成了权力的晚礼服,裹得住肚腩,遮不住狐臭。更致命的是,洋务派自身也迅速变成新的利益板块:李鸿章的“北洋”不是国家军队,而是李府私兵;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名义上是“官督商办”,实质是“督”者坐地分肥。
改革者一旦获得特权,就立即从“挑战者”变成“守门人”。历史在此露出最狰狞的一面:不是顽固派扼杀了改革,而是改革者自己完成了身份转换,成为旧结构的升级版补丁。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五、现代性陷阱:选票代替血诏,制度外包依旧
有人以为,只要把“封建”换成“民主”,改革就能摆脱死循环。但看看近二十年西方世界的改革困境:马克龙动一下劳工法,黄背心烧遍巴黎;奥巴马想推全民医保,茶党直接把国会山掀了;德国施罗德削减福利,社民党至今没有缓过气。逻辑如出一辙——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再分配,都会遭遇制度性反噬。
不同之处在于:封建王朝用“廷杖”、“流放”物理消灭改革者,现代社会用“选票”、“游说”合法稀释改革。前者是血腥的,后者是体面的,但结果一样:改革被切成公关口号,在一次次选举周期里无限后移。所谓“民主纠错机制”,在阶层固化、金融垄断、产业外包的多重夹击下,越来越像一种自我安慰的修辞。
换句话说,现代西方只是用“程序合法性”替代了“天命合法性”,却没有解决“谁为改革付成本”这个根本问题。当99%的人只能靠1%的人发慈悲,改革就仍然是一场需要“血诏”的奢侈品。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六、打破重来:革命与改革之间并无中间道路
历史给过最诚实的忠告:当制度开始系统性地吃人,任何“内部修缮”都会沦为共谋。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是因为“改革者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旧制度彻底关闭了自我更新的接口。
革命不是改革的升级版,而是对“改革幻觉”的强制清零。真正的悲剧在于,后人总喜欢用“代价太大”来否定革命,却选择性遗忘:被否定的那场革命,恰恰是因为旧结构连最小限度的让利都不肯。
换言之,革命的成本从来不是革命者强加的,而是旧制度在一次次“自我改革”骗局里层层加码的利息。当利息高到社会无法承受,爆炸就是唯一的选项。所谓“暴力循环”,不是革命本身的原罪,而是旧制度拖延改革的复利。
七、结语:请把勇气留给值得的制度
今天,我们纪念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最该做的不是歌颂他们的“理想主义”,而是承认他们的失败是制度性必然,从而彻底放下“修补老屋”的执念。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改革不是鲜花铺路,而是虎口夺食;不是渐进直线,而是爆炸前的倒计时。真正的勇气,不在于明知是虎还要一次次伸手,而在于看清吃人逻辑后,敢于推倒老屋,另起地基。否则,每一代人都将重复同一套悼词:“他失败了,但他激发了后人继续改革。”
——不,后人只会继续被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