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一真的人生,其实藏着一连串的矛盾。这人是日本人,扛着相机踏进北京的时候,身边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可他干的却有点像书生——在最不安稳的年代,拍下了最安静的风景。有人说,他是外来入侵者的随军摄影师;可你真翻开那些老照片,又忍不住想,这人没准心里也柔软过。
其实,小川的那台照相机,是他随身的秘密武器。1901年初夏,城墙外是炮火,紫禁城却还留着暮春的清风。他跟着队伍进了那一片皇家的园林阴影,按动快门时,眼里看到的未必就是“敌国之物”,更多的是岁月走过的脉络。他走在昆明湖边,冬末的冰还没化净,石舫独自横在水上,那是大清权势最后的残影,也是当年乾隆皇帝自信写下的“水能载舟”隐喻。
小川恐怕也没想到,自己按下快门的这一刻,百年后还能让许多人凝视。他拍下的,是69年前烧过的东西——圆明园已经成废墟,石舫烧后复建,抓拍下的新旧,分明在纠缠。乾隆年间石舫的寓意:稳如磐石、奈何连皇家也是“水火无常”,转眼九州动荡。
照片里的每一块青砖、每一道飞檐,其实都藏着一丝被风刮过的人气。谁又能想到,石舫初建之时,京城的手艺人忙得马不停蹄,琉璃瓦贴得色彩纷呈。光绪年时又重修,园丁刷漆的味道还没散去,慈禧太后已经带着寿宴的鼓乐走上了廊道。
照片更像一本无声的日记。走在长廊下,有翻修后新油漆的明黄,也看得出烧毁时灰黑的痕迹;一边拍下白塔残破的模样,小川偶尔也疑惑——谁会在大火和铁蹄过后,还愿意在断壁残垣里修一座佛塔?
那年北京,是一座被兵燹和屈辱剥了皮的老城。但在这些画面外,小川见到的,还有园子里零星的仆役,跟日本军人窃窃私语。他们看见镜头,偏过脸,眼中有点嫌恶,有点不屑。毕竟,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日本人既是“强盗”,又是个在战火里捣鼓新鲜玩意儿的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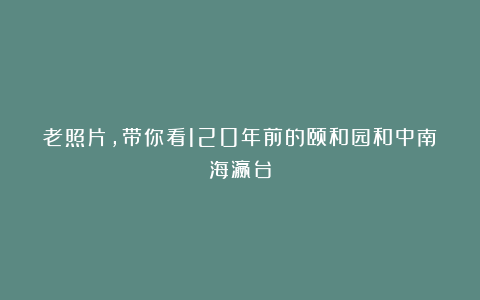
小川也总要有困倦和犹豫。夜里,翻拣自己拍的底片,他大概也纳闷:石日在昆明湖边看似无言,比起朝堂风云它又算什么?可等阳光好了,他还是跑到瀛台的石桥上,咔嚓一声,把流水亭的倒影包进画幅。那时候的北京,不是只有皇帝和将军——亭子里也会有疲惫的园丁和偷偷扎根的野花。瀛台的迎薰亭、小桥流水,老北京人说“那里风细,好写诗”,小川就一头扎进去了。
你说这些照片,究竟算不算一种“掠夺”?有人说,小川是在替侵略者圈地——他把我们的园林藏进“帝国的相册”,成了他民族炫耀的资本。可退开一步看,那些画面其实也在证明:这些石头、琉璃、粉墙,是打不碎、抢不走的东西。只是,这话说出来,百年前的北京人也许只会苦笑。
逛完颐和园,小川又跟着部队去了中南海。他拍紫光阁的时候没想到,自己此刻拍下的门廊和水面,几十年后还会迎来外国元首、议事厅里的风声。春明楼、翔鸾阁,这些名字是给王孙贵族用的;可当时已经是乱世,所谓“高楼宴会”,不过是一曲中断的小令。
其实,他留在胶卷里的除了石头塔,就是时间流过的印迹:万寿山四梵塔的白塔在风里剥落,冬日斑驳墙皮上还沾着野鸽子的足迹。挨着长廊的排云门,有时候能拍到一个青衣守门的老太太,背影比宫墙更让人叹息——这城的故事里,人始终是游离在权力与风景外的过客。
有一张他拍瀛台,巧了,正是袁世凯那些年挤在里面谋大位的时候。老北京人有个段子:袁世凯头大,瀛台楼梯太窄,每下楼都得侧身,这段子一代又一代流传。小川对这种故事也许没有共鸣,但每次架好相机,拍下水流潺潺,也逃不开外来身份的尴尬。有位守门的太监问他:“你们厚道吗?”没等回答,就被部队催开。
小川在北京拍了大半年。说实话,人也会有点倦。紫禁城、万寿山、黄寺的佛像……这座城的娇贵都被他逐一按下快门。可越拍越觉得悲凉:东黄寺的佛像,镀金的笑脸已经掉皮,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更连影子都没有了?寺庙、园林、石牌坊,一损再损,到头来只剩几张泛黄的老照片。那些照片后来漂回日本,装帧成册,取名《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有人收藏有人议论,而北京的老百姓还得忙烤地瓜、添衣服,继续过日子。
这些老照片像时间留下的剪影。120年后的今天,你我在网上翻着看,感叹当年北京的琉璃和石雕,已无法亲见。也许我们永远猜不透小川那时的心思——他是为谁拍下的北京,是记录,是炫耀,还是不自觉的叹息?
照片不会说话。可城墙和亭台间的光影,却像一代人没说完的话,幽幽远远。谁也道不清,到底是小川抢走了老北京,还是在替那一段旧光阴留了点纪念。
故事就留在这里吧。再往后,北京城有风起雨落,石舫在水面上熬过每一个晨昏,有人惋惜、有人唏嘘,小川的底片静静地躺在别国柜子里,被时光裹住了声音。你听到什么了吗?我偶尔想,如果那些老照片也能开口,也许他们不会分什么谁来谁走,只想说一句:“这里曾经有人生活,真的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