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西头的老杨叔,那双手,可是全村有名的。小时候我们这群孩子总爱围着他,掰着他的手指头看——十个指头,清一色的“簸箕”,那纹路一圈圈散开,真像家里扬米去糠的簸箕,一个圆溜溜能“装钱”的“斗”都没有。
于是,村里老辈人提起他,总会咂咂嘴,叹口气:“老杨这人啊,存不住财。”
这话,搁在老杨叔身上,好像真有点道理。他是个热心肠,也是个大手脚。他家地里的瓜果蔬菜,永远是左邻右舍尝鲜的第一茬。谁家建房搭屋,他准第一个扛着家伙去帮忙,工钱饭食提都不提。村口小卖部的老板最清楚,老杨叔兜里只要有几个零钱,转脸就能给我们这帮娃娃换成糖豆、麻花,他自己就蹲在旁边,眯着眼看我们吃,比他自己吃了还香。
他媳妇杨婶为这事没少跟他拌嘴:“咱这日子不过了?闺女以后上学不要钱?你当咱家是金山银山?”老杨叔总是嘿嘿一笑,用那布满“簸箕”的大手挠挠头:“钱嘛,挣了就是花的,东西吃了用了才是自己的。乡里乡亲的,计较个啥?”
那年夏天,连着下了几天暴雨,村里五保户刘奶奶那间老土房,山墙塌了半截。村干部组织人帮忙,可材料钱一时还没着落。刘奶奶坐在废墟边上,抹着眼泪。老杨叔一声没吭,扭头回了家,没过多久,把他和杨婶省吃俭用攒下,准备给闺女交学费的三千块钱,全塞到了村支书手里。
“先用着,救命要紧!”他话说得斩钉截铁。
为这事,杨婶气得带着闺女回了娘家,半个月没回来。村里人背后议论得更响了:“看看吧,我说啥来着?十个簸箕就是往外簸的命,连闺女学费都簸出去了,真是没处装!”
老杨叔那段时间,一个人蹲在自家门槛上,闷头抽烟,看着自己那十个手指头,不言不语。
日子流水般过着。那年秋天,老杨叔上山捡山货,不小心摔断了腿。这下,家里顶梁柱倒了,眼看就要秋收,地里活儿都耽搁了。杨婶急得嘴上起了燎泡。
可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家的院门就被推响了。东头的张大哥扛着镰刀来了,西边的李婶提着早饭来了,前院的赵家兄弟开着拖拉机也来了……不一会儿,院子里就聚了十几口子人。
“老杨,你好生歇着,地里的玉米,我们包了!”
“就是,去年要不是你帮俺家抢收,俺那粮食早烂地里了!”
“杨嫂子,这二百块钱你先拿着,给老杨买点营养品,不多,是俺一点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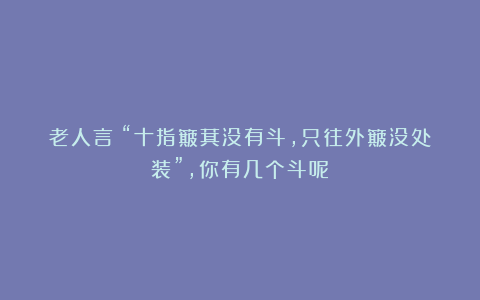
人群里,甚至还有当初说他“簸箕命”最响的那几位。大家七手八脚,不到两天工夫,老杨叔家几亩地的玉米,颗粒归仓,收拾得利利索索。
老杨叔靠在炕头上,看着院子里堆成小山的粮食,看着乡亲们送来的鸡蛋、挂面,还有杨婶手里那叠零零整整的票子,这个硬邦邦的汉子,眼圈红了。
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簸箕”纹路的大手,轻轻握住了杨婶的手,声音有些沙哑:“孩儿她娘,你看……我这十指簸箕,是没处装。可咱这人情、咱这心里,它装得满满的啊!”
打那以后,村里人还是会说老杨叔是“簸箕命”,但那话里的味道,却全变了。大家再说起时,总会跟着补上一句:“老杨那’簸箕’簸出去的,是真心,簸回来的,是金山银山都买不着的暖和气儿。”
是啊,有些东西,是“斗”装不下的。老杨叔那十只“簸箕”,簸出去的是小利,装回来的,是整个村子的情义。这道理,朴实得像地里的黄土,却比什么都金贵。
“十指簸萁没有斗,只往外簸没处装”: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十个手指的指纹全都是“簸箕”,一个“斗”都没有。那么这个人就像一直拿着簸箕在往外撒东西,却没有一个“斗”来储存和积累。
斗(箩):呈圆圈状,一圈一圈闭合的螺旋形或同心圆形,像个小漩涡。古人认为它像“斗”(一种盛粮食的容器),能聚财、聚物。
簸箕:呈半开放或波浪形,像流水的波纹,不闭合。古人认为它像“簸箕”(一种扬米去糠的农具),是用来把东西撒出去的。
当然 ,这句老话从我们现在科学角度来看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指纹的形成是由基因和胚胎发育早期的随机因素决定的,它与一个人的性格、财运、命运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一个人的理财能力、消费习惯是由其后天的教育、家庭环境、个人规划和自律性决定的。
这只是古代民间一种“象形”和“谐音”的联想式说法,属于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并非客观规律。类似的俗语还有“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等,都带有很强的娱乐和戏说成分。
总之,这句老话它蕴含了古人关于财富积累的朴素智慧,即“量入为出,积少成多”的道理。它作为一个生动的比喻和警示,提醒我们要注意理财,避免成为那个“只往外簸没处装”的人。
作者 | 鸿雁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