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新君
人老了真的太难了,我不缺房不缺钱,儿女也出息,可如今年过70岁了,却感觉一无所有。
我叫老张,今年71岁,年轻时候我总觉得,人活着就得争口气。
我爹娘是煤矿工人,一辈子在井下刨生活,指甲缝里的黑泥就没洗净过。
我上初中那年,父亲在井下被落石砸断了腿,然后卧床不到三年,就走了。
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儿子,咱不当挖煤的,咱得站在太阳底下挣钱。”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也激励着我努力学习,最终参加高考,并考上了县城的电力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供电局,拿到了人人都想要的铁饭碗,也让母亲跟着过起了好生活。
工作第四年,经人介绍娶了老伴,结婚第二年,她就为我生下一双儿女。
年轻时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我满心期望:将来得让他们读最好的学校,考名牌大学,不能像我这样,一辈子就守着这一亩三分地。
后来,我的一双儿女也出息,儿子考上了上海的大学,学计算机,毕业进了家互联网大厂。
女儿去了广州读师范,毕业后留在那边教书,现在在一重点小学当教导主任。
看着他们在大城市工作又安家,我跟老伴有难一阵子,是开心的晚上睡不着觉。
60岁那年我退休,第一个月拿到7200块退休金,在我们这小城里,算得上是高收入了。
我跟老伴合计着,先去海南过冬,再去新疆看草原,年轻时没功夫去的地方,老了都得补上。
头两年确实舒坦,我们跟着旅游团跑了大半个中国,老伴脖子上挂着我给她买的玉坠,逢人就说这是我老头给买的。
邻居们见了就羡慕:“老张真有福气,儿女有出息,自己手里又宽裕。”那时候我也觉得,这辈子值了。
谁能想到,好日子就跟搭戏台似的,说拆就拆了。
四年前的一天早上,老伴去楼下倒垃圾,结果滑了一跤,后脑勺磕在台阶上倒在地上。
虽然及时送医了,但情况很严重,医生抢救三个多小时才出来。
我当时在外面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烟抽了整整一包。
给儿子打电话,他说在国外出差,签证出了点问题,最快也得三天才能回来,说完就给我转了十五万。
打给女儿,响了半天没人接,再打就关机了。我握着手机,指节都攥白了。
后来才知道,她那天正带着学生参加比赛,手机放在更衣室去了。
虽然医生极力抢救了,但老伴还是没手术成功,老伴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还没闭眼,但脸色白得像纸。“孩子们……回来了吗?”老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一样。
“在路上了,马上就到。”我凑到她耳边说,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她可能等不到了。当晚推出手术室不到6小时,老伴就走了,而女儿是第二天早上到的,等儿子回来的时候,老伴已经入殓了。
处理完后事,儿子和女儿都劝我跟他们走。
儿子说上海的房子大,有间朝南的卧室空着。女儿说南方暖和,适合我养老。
我都没答应,感觉自己离不开和老伴同住半生的房子,并且也觉得孩子们上班那么忙,我去了净给他们添乱,两代人过日子,哪能没摩擦?
我当时还琢磨着,自己身体硬朗,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下午跟老伙计们下下棋,晚上看看电视,一个人也能过得挺好。
可没过半年,就出了岔子。那天我在菜市场买了块五花肉,想自己炖点肉吃,刚走到单元楼门口,突然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旁边守着的是老邻居王大爷。他说我倒下的时候,脸都磕破了,流了好多血。
医生说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得按时吃药,不能累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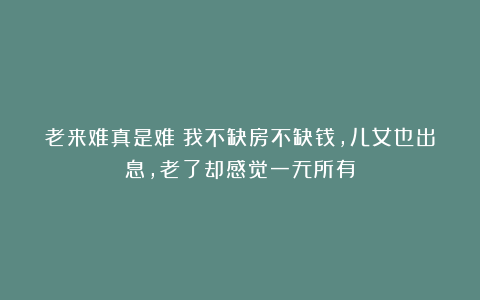
出院回家,打开门,屋里冷冰冰的,灶台上还放着那块没炖的五花肉,已经变味儿了。我看着那块肉,突然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人挖走了一块。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给儿子打了个长长的电话,跟他说我住院了。
他在那头急得不行,说明天就回来。
我说不用,就是跟你说一声,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直到天亮。
后来女儿抽空回来一趟,给我买了台智能音箱,说有事喊一声就行。她还想给我找个保姆,我说不用,我自己能行。
可她走了没几天,我就发现自己是真不行了。
有天晚上起夜,脚下一滑,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最后还是拽着毛巾架才撑起来的。
没办法,只能找个保姆。中介给介绍了个姓刘的大姐,四十多岁,看着挺实在。一开始还行,她做的菜合我口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净。
可过了俩月,我发现不对劲。
我放在抽屉里的零钱,总莫名其妙少几张。有一次我故意放了张五十的,第二天就没了。
我问刘大姐,她支支吾吾说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碰掉了。我没戳破,心里却跟明镜似的。没过几天,我发现她偷偷拿我冰箱里的排骨,给她儿子打电话,说晚上炖排骨吃。
我当天就跟她说,不用再来了,工资一分没少给她。
女儿知道了,非要接我去广州。
我说啥也不去,最后她没辙,说那去养老院吧,她考察了一家条件不错的,有医生有护士,住着放心。我琢磨着也行,养老院里都是同龄人,说不定能交上几个朋友。
那家养老院我真去住了几天,确实气派,门口有喷泉,院子里种着不少花。房间是两人间,带卫生间,比我家还干净。
头几天是挺新鲜,早上跟着大家做早操,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看看电影。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食堂的菜看着花样多,可吃着没味儿,炖个鸡,连点盐味都没有。跟我同住的老李,脾气古怪得很,晚上睡觉打呼跟打雷似的,我根本睡不着。
有天半夜,我起夜,听见走廊里有哭声。出去一看,是护工在训一个老太太,说她又尿裤子了。
那老太太缩着脖子,跟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看着她,突然就想到了自己,要是哪天我也动不了了,是不是也得受这窝囊气?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收拾东西回了家,还有十来天的费用都没去退。。
回到家,看着屋里熟悉的摆设,心里稍微踏实了点。可空荡还是空荡,尤其是晚上,让我很是孤单与寂寞。
去年秋天,我把城里的房子租了出去,收拾了几件行李,回了老家。
我爹娘早不在了,可老家还有个弟弟,比我小6岁,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守着几亩地过日子。
他儿子在镇上开了个杂货铺,离得近,三天两头就来看看他。
我回来那天,弟弟和他媳妇在村口接我,手里还提着个保温桶,里面是刚炖好的鸡汤。他们把老家老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西厢房还给我腾了出来,铺着新褥子。
晚上吃饭,弟媳妇给我夹了块鸡腿,说:“大哥,你别嫌弃,家里条件不好,可咱有口热饭吃。”我啃着鸡腿,喝着白酒,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酒虽然没有我平时喝的贵,可喝着暖心。这鸡腿炖得也不如老伴炖的烂,可吃着却很香。
如今在老家待了快一年,我才算明白,人老了,图的不是住多大的房子,手里有多少钱,图的是个热乎气儿。
弟弟没啥大本事,可他儿子每天早上都来给他送新鲜豆浆,孙子放学就往他怀里钻,喊着“爷爷抱”。
晚上吃完饭,一大家子坐在院子里,扇着扇子聊天,那种热闹劲儿,是我在城里住再好的房子也换不来的。
看着弟弟一家子如此幸福,我突然就想:如果当初儿子和女儿没走那么远,就在县城找份工作,是不是现在也能经常回家看看我?是不是老伴走的时候,能多见孩子们几面?
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就像地里的庄稼,种下去了,长出来啥样,就得认啥样。
只是有时候,看着弟弟抱着孙子在院子里转圈,听着他媳妇在厨房喊吃饭,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这辈子挣了那么多钱,培养出那么有出息的儿女,到底图个啥呢?图到最后,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所以人老了真是难啊,就算不缺房子不缺钱,儿女出息,老了也还是一样难逃老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