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是最识人间炎凉的。先前还带着些秋老虎的余威,卷着槐叶在巷口打旋,如今却像淬了冰的刀子,刮过光秃秃的树梢时,总发出呜呜的响,倒像是谁在荒庙里敲破了木鱼。天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云絮都冻成了硬块,懒懒散散地挂着,连挪动一下都嫌费力气。
这时候的山,是真正空了。春里闹着的杜鹃,秋时聒噪的寒蝉,此刻都销声匿迹。先前常有人说,山是活的,藏着百兽的呼吸,可眼下踏进去,脚底下的枯叶发出“咔嚓”的脆响,竟能惊起半里地的回声。那些曾在岩缝里探头的松鼠,草窠里蹦跳的野兔,像是约好了似的,连个影子都寻不见。偶见几株老松,铁铸似的立在崖边,松针上凝着白霜,倒像是披了件旧棉絮,风过时抖落几点,在地上砸出细碎的白。
田埂上的霜,是下得不含糊的。清晨推开柴门,眼瞧着近处的麦地全蒙了层薄纱,远处的池塘结着冰,冰面反射着惨淡的光,倒比天上的日头更刺眼些。有早起的农人,裹着打了补丁的棉袄,蹲在田埂上抽烟,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满是皱纹的脸,像幅褪了色的年画。他不说话,只是望着自家的地,地里的麦苗缩着脖子,叶片上的霜被风一吹,簌簌地落,倒像是在掉眼泪。
路是冷清的。先前赶集的日子,这条土路上总挤满了人,挑着菜的,牵着羊的,背着筐的,闹哄哄能从日头刚冒尖到晌午。如今却不然,走半晌也遇不见个活物,只有路边的歪脖子树,枝桠上挂着几片干硬的叶子,风一吹就晃悠,像个垂头丧气的老头。偶有赶车的路过,马蹄踏在结了薄冰的土路上,发出“嗒嗒”的响,车轱辘碾过枯叶,卷起一阵碎末,很快又被风卷走,留不下一点痕迹。
村头的老井,井口结着层薄冰,井绳上挂着冰碴子,提水时得先敲碎冰面,“哐当”一声,在这寂静的村子里,显得格外响亮。井台上的石板,被几代人的脚磨得光滑,此刻也冻得冰凉,蹲在上面洗衣服的妇人,手浸在水里,一会儿就得往袖口里缩,嘴里嘶嘶地吸着气,脸上却带着笑,跟旁边的人搭话:“这天,是要把人骨头都冻透呢。”
屋檐下的冰凌子,挂得老长,像一串串透明的刀子,太阳出来时,能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可没等晒化,就又被寒风冻得更硬。墙根下的猫,蜷成一团,缩在干草堆里,眯着眼睛打盹,偶尔竖起耳朵听几声狗吠,又很快耷拉下去,懒得动弹。柴房里的柴火,堆得老高,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烟囱里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到了半空,被风一吹,就散了,连个烟影都留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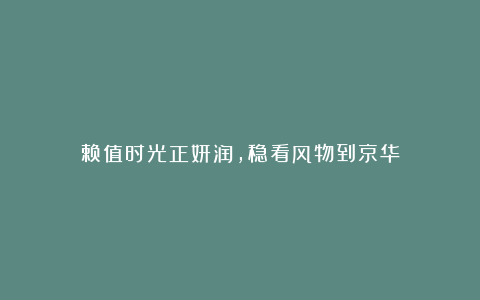
这时候的日子,像是被冻住了似的,过得慢悠悠的。男人们蹲在墙根下晒太阳,抽着烟袋,说着往年的收成,声音不高,像怕惊扰了这寒冬的寂静。女人们坐在炕头上,纳着鞋底,线穿过布面,发出“嗤啦”的轻响,孩子们在屋里追跑,被大人喝住,便乖乖地缩在炕角,摆弄着手里的冰疙瘩。
傍晚时分,炊烟渐起,村子里才多了些生气。各家屋顶的烟囱里,冒出或浓或淡的烟,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像一条条细线。归巢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几声,很快又安静下来,像是怕冷似的,把头埋进翅膀里。
夜色来得早,天刚擦黑,村子就陷入了寂静。只有偶尔几声狗吠,或是谁家孩子的哭闹,划破这沉沉的夜色,很快又被无边的黑暗吞没。窗外的风,还在呜呜地刮着,像是在诉说着这寒冬的漫长。
这寒冬,虽带着几分凛冽,却也藏着几分实在。山空了,是为了来年的葱郁;霜重了,是为了地里的庄稼积蓄力气;人静了,是为了在忙碌一年后,好好歇一歇。这乡土的冬,没有春花秋月的矫情,只有实打实的冷,和冷里藏着的,对生活的热望。
晓随灯火背千家,落尽疏星见远霞。
一饷春声回宿鸟,半天寒色在啼鸦。
临陂弱柳犹藏叶,当路残梅已尽花。
赖值时光正妍润,稳看风物到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