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神秘学与炼金术系列的第六篇文章。
前文可见:
Maiori forsan cum timore sententiam in me fertis quam ego accipiam.
也许你们在宣读判决时,比我接受判决时更感到恐惧。
——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
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在其代表作《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6 世纪意大利东北部弗留利地区,一个磨坊主多梅尼科·斯坎德拉(Domenico Scandella),认为宇宙之初的一切都是混沌,土、气、水、火混在一起,这团混合物自然凝结,就像牛奶搅拌后凝成奶酪,从中又生出了“蛆”,这些“蛆”就是上帝和天使,上帝被立为主,与路西法、米迦勒、加百列和拉斐尔一起治理万物。
1599年,斯坎德拉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并处以火刑。
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
在金茨堡看来,这是前天主教的民间信仰顽强保留在乡村口述传统中的结果。
但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就在斯坎德拉受刑一年后,一个更危险而激进的异端也被送上火刑架,他受到了正规的多明我会神学教育,但他的宇宙观,却与那位磨坊主的奶酪理论无比接近。
2.
1437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八世·帕莱奥洛古斯( Ἰωάννης Παλαιολόγος)率领七百余人的庞大随行队伍横跨海峡来到意大利,他们先抵达威尼斯,辗转费拉拉,之后又为了躲避鼠疫,在冬日的狂风暴雪中落脚佛罗伦萨。
在圣玛利亚诺韦拉教堂,东罗马帝国的代表们与天主教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双方签署合一文件,东罗马承认教宗对东正教的最高权威,以此换取西方援助抵御土耳其的承诺。继1054年教会大分裂以来,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然而,甚至连庆祝的余音都还没消,协议就在抗议和猜忌中化作泡影,东正教的信徒们不甘屈居人下,意大利人的承诺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数年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纪年定格在1453。
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
不过,对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而言,会议的结果却是再乐观不过。
东罗马帝国主教贝萨里翁(Βασίλειος Βησσαρίων)留在意大利,成为红衣主教与学术赞助人。柏拉图研究权威格弥斯托士·卜列东(Γεμιστός Πλήθων)在佛罗伦萨停留讲学,被亚里士多德遮蔽已久的柏拉图哲学,重新进入西欧人文主义者的视野。
慷慨的赞助人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随即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中心,委托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将柏拉图全集翻译成拉丁文。
但在柏拉图的阴影之下,还潜伏着另一套久已失传的思想体系
——赫耳墨斯主义(Hermeticism)。
3.
1460年,病榻上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命令菲奇诺暂时搁置柏拉图的翻译工作,优先处理一部刚从马其顿修道院辗转带回的希腊语手稿——《赫耳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菲奇诺连夜攻读,在科西莫去世前一年将拉丁译本呈上。
这部文集由17篇希腊语论文组成,作者是传说中的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托斯(Hermes Trismegistus)。
或者,用更通俗的说法,“三重伟大的赫耳墨斯”——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神(Hermes)与埃及托特神(Thoth)的混合体,西方神秘主义的滥觞。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赫耳墨斯文集》早于柏拉图,与摩西同属一个时代。
与同为赫耳墨斯文献,但更倾向炼金术等实用技艺的《翡翠石板》(Tabula Smaragdina)不同,《赫尔墨斯文集》探讨了宇宙论及灵魂救赎等宗教哲学,同时吸纳了埃及本土宗教、古希伯来宗教、斯多葛主义与诺斯替主义。
作为“原初神学”(Prisca Theologia),《文集》勾勒出一条从俄耳甫斯(Ὀρφεύς)、阿格劳斐摩斯 (Ἀγλαόφαμος),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哲学暗线,这条线索曾一度在中世纪西欧中断,又似乎是神启一般,于文艺复兴降临。
赫耳墨斯文集
科西莫的命令在后世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不是柏拉图影响了赫耳墨斯,而是赫耳墨斯启发了柏拉图。
自此,中世纪西欧与希腊哲学,乃至更早期基督教神学间的桥梁,终于再次连接起来。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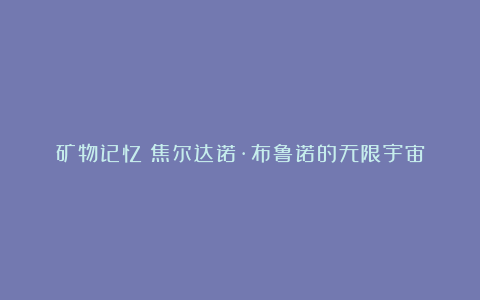
当然,想也知道事情并非那么凑巧,菲奇诺的翻译远谈不上客观中立,他深思熟虑地处理那些暧昧的术语,将它们有意引向新柏拉图主义的语境,小心翼翼地把神秘主义安放进天主教的正统框架。
他援引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主动改写赫耳墨斯的身份,将其从异教神祇变成了耶稣之前的外邦先知(Gentile prophet),是那位预告“上帝之子”降生的古老启示者。
菲奇诺将赫耳墨斯解释为先知而非异教之神
然而,文本的力量并不会服从译者的意志。
只需稍加通读,我们便能发现《赫耳墨斯文集》的危险之处,它将世界分为三层:其上为神,其下为理智世界,再下为可感世界。
太阳被视作可感世界的中心,具有“第二神”的地位,诸天以它为纲运行。人类则是被造世界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microcosm),两者相互映照,事物的整体模式便得以揭示。
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类比(也称“如上亦如下”)
恒星与行星同样发挥作用,它们交织出人类的命运(heimarmene),而人类则可以借由灵魂修炼超越命运,上升至与神合一的境界。
菲奇诺对这些段落深感不安,在《论天体生命的比较》(De vita coelitus comparanda)中,他竭力淡化赫尔墨斯主义的神学含义,尝试在“自然魔法”与“恶魔魔法”之间搭建一道微妙的防火墙,避免越界进入恶魔崇拜。
他辩称,人们可以吸引星辰中有益的灵气来增进健康,这与召唤魔鬼截然不同,仅仅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实践。
《论天体生命的比较》是菲奇诺的《生命三书》(De vita libri tres)的第三卷
但这套绥靖式的诠释,随着文本的迅速传播变得摇摇欲坠。后继的思想家们不再像菲奇诺那样谨慎,他们推倒了这堵墙,释放出潜藏于赫耳墨斯主义中的激进火种。
5.
火药桶的爆炸总归需要一根引线,这根引线并不难等到:1517年,宗教改革爆发。
路德和加尔文宗猛烈抨击天主教会是“迷信”和“魔法”的温床,作为回击,天主教会启动了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
1559年,《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的出台标志着反击的制度化 。尽管《赫耳墨斯文集》因其自身的深远渊源未被立即封禁,但注释者的著作却遭到毁灭性打击。阿格里帕、帕拉塞尔苏斯和所有涉及地占、水占与死灵术的书籍,被系统性地列入黑名单。
禁书目录
更为致命的是神学定义的硬化。菲奇诺曾费尽心机区分“自然魔法”和“恶魔魔法”,但在反宗教改革的神学家眼中,这道防线崩溃了,凡是产生超出自然可见因果的效果,无论表面多么虔敬,其背后必然潜藏着与恶魔的契约。
就是在这个充满敌意的氛围中,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带着他那激进的赫耳墨斯教义,闯入罗马的视野。
6.
如果说菲奇诺试图将赫耳墨斯变成一个基督徒,那么布鲁诺则试图将基督还原为一个赫耳墨斯主义者。他甚至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基督教不是赫耳墨斯智慧的成全,而是它的腐化 。
弗朗西丝·耶茨(Frances Yates)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布鲁诺视自己为复兴埃及宗教的先知,在他看来,太阳不仅仅是天文学的中心天体,也是神性在宇宙中可见的标志,是回归埃及太阳崇拜的契机。
哥白尼与布鲁诺之前的托勒密地心说体系
对于布鲁诺而言,一个由无限世界组成的无限宇宙(Cosmic Pluralism)是神学上的必然。如果上帝是无限的,他的创造物必然也是无限的,这一多元宇宙多元论源自赫耳墨斯主义关于神性“充盈”(plenitude)的推理,它消解了“道成肉身”的独一性。
如果有无限的世界,是否有无限的基督?
或者,基督的降生,只是无数宇宙事件中渺小的一例?
而我们也终于能得出结论,知识高层的布鲁诺与知识底层的磨坊主在宇宙观上的惊人一致,正是宗教改革敲开教会硬壳后,在裂缝与松动之间,远古异教与民间信仰趁虚而入、短暂合流的结果。
7.
1592年,威尼斯贵族乔瓦尼·莫切尼戈(Giovanni Mocenigo)向宗教裁判所秘密告发布鲁诺 。
虽然威尼斯相对宽容,但罗马宗教裁判所闻讯后,强硬要求引渡,一年后,布鲁诺被移送罗马。
经历长达七年的审判,著名的耶稣会神学家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枢机接手此案,他研读其著作和审讯记录,提炼出了八条命题(Eight Propositions),直击布鲁诺的异端核心。
布鲁诺受审
为了防止他在临刑前对人群发表异端言论,行刑者用铁制夹具(mordacchia)穿透并锁住了他的舌头。这位赫耳墨斯的最后使徒,被迫以沉默消失在火焰中。
8.
布鲁诺死后仅14年,瑞士语言学家依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通过分析证明,《赫耳墨斯全集》并非写于摩西时代,而是公元2至3世纪希腊化时期 。
“古代神学”的大厦轰然摇动,赫耳墨斯不是预言基督的古老先知,仅是一位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主义者,菲奇诺和布鲁诺的宏伟谱系失去了神圣源头。
与此同时,科学革命也开始将“魔法”与“科学”剥离,新一代自然哲学家们致力于寻找不依赖世界灵魂或天使干预的自然法则,布鲁诺那“万物有灵”的宇宙观,被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机械宇宙取代。
神秘主义被驱逐出“原初神学”,魔法被赶出自然哲学,宇宙只剩下寂静的法则与运动的天体,《赫耳墨斯文集》被冷静地宣判了死刑,鲜花广场上的灰烬,被台伯河畔的风吹散。
罗马鲜花广场上的布鲁诺纪念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