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神秘学与炼金术系列的第三篇文章。
前文可见:
Era qualcos’altro che vedevamo in quei tarocchi, qualcosa che non ci lasciava più staccare gli occhi dalle tessere dorate di quel mosaico.
我们在这些塔罗牌中看到了别的东西,某种让我们的目光再也无法离开那金色马赛克镶嵌画的东西。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命运交叉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
1441 比安卡
10月25日,小城克雷莫纳迎来一个热闹的深秋,全城各处悬挂着蛇纹与雄鹰的纹章旗帜,以迎接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的一方是15岁的比安卡·马里亚·维斯孔蒂(Bianca Maria Visconti),她是米兰公爵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唯一的孩子,而婚礼的另一方,则是大她25岁的雇佣兵首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I Sforza)。
这是一场权力交接仪式,比安卡无法继承父亲的公爵头衔,迫于无奈,公爵只能让她嫁给自己的雇佣兵手下,米兰公国自此落入斯福尔扎手中,结束了短暂的维斯孔蒂时期。
而被继承下来的,除了一个庞大的公国,还有一套神秘的牌组。
象征维斯孔蒂的蛇纹与象征斯福尔扎的雄鹰
一直以来,维斯孔蒂公爵都在进行自己的牌组试验,他身材肥胖、体弱多病,可能还患有忧郁症,长年隐居在米兰城堡里,为数不多的爱好就是纸牌、占卜与棋类。
就在女儿诞生的那年,公爵久违地准备了一场“凯旋庆典(Trionfo)”以表达自己的骄傲和喜悦。他甚至为此委托马尔齐亚诺·达·托尔托纳(Marziano da Tortona),设计了一套包含56张鸟类花色(鹰、凤凰、鸽、乌鸦)和16张古希腊–罗马神祇主题胜牌的牌组。
公爵将这副牌命名为凯旋牌(Trionfi)。
这组牌显然没能给他带来好运,但欣慰的是,女儿比安卡将他的爱好延续下来,她借鉴马穆鲁克牌,将花色从鸟类改为了圣杯(Coppe)、宝剑(Spade)、权杖(Bastoni)、硬币(Denari) 四种,并且将胜牌扩展到了21张,包含节制、力量、正义、皇帝和皇后,太阳、月亮与星星……
还有一张豁免牌:愚人(Il Matto)。
现存的最早的维斯孔蒂-斯福尔扎牌组之一——耶鲁塔罗
之后的半个世纪,意大利战争使雇佣兵和商人们往来于意大利北部与法国南部,将凯旋牌带往了它下一个应许之地——马赛。
1781 热贝林
“这并非一副普通的牌,而是隐秘的埃及典籍,《托特之书》。”
在安托万·考特·德·热贝林 (Antoine Court de Gébelin)这句断言前,凯旋牌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近乎失传。
作为一种通俗纸牌游戏,凯旋牌曾经在16世纪的法国十分流行,在大众文化的改造下,“Tarot”这个名称取代了古典的“Trionfi”,“凯旋牌”也因此成了“塔罗牌”。
但在17至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塔罗牌游戏的流行地区,已经退缩到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国东南部延伸至瑞士的一个狭长地带。
在欧洲更多地方,人们习惯去掉22张胜牌,将四花色简化成更易识别的红桃(圣杯)、方块(硬币)、黑桃(宝剑)、梅花(权杖),马赛塔罗此时已经与现代扑克牌分道扬镳,成为局限在造牌师们与收藏家圈子里的工艺品,
不出意外的话,塔罗牌也将像它的所有前身那样,成为纸牌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形式。
马赛塔罗牌组
热贝林出现得恰如其分,在《原始世界》(Le Monde primitif, analysé et comparé avec le monde moderne)第八卷,他称塔罗牌是古埃及神祇托特(Thot,即三重伟大的赫耳墨斯)所著的《托特之书》,只是一直以来都被当作纸牌游戏。
更重要的是,热贝林重新拾起了本已沦落至边缘的22张胜牌,将其赋予隐秘的象征意义,22张胜牌正好对应托特之书的22幅象形画,塔罗牌自此与蕴含宇宙智慧的秘传文献联系在一起。
热贝林的塔罗牌组
1783 埃特伊拉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是神秘主义群魔的乱舞场,从土耳其行棋傀儡到古埃及象征主义,整个社会陷入对古代东方知识的狂热中,启蒙思想也为动摇基督教权威加了最后一捆柴火,占星、炼金和水晶球占卜术席卷街头巷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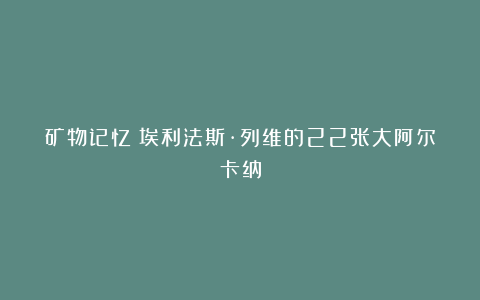
就在热贝林发表塔罗牌神秘主义宣言的两年后,一个版画和纸牌商人也加入了这场大潮,他的原名是让-巴蒂斯特·阿利埃特(Jean-Baptiste Alliette),但或许我们更熟悉他将姓氏倒拼而来的笔名——“埃特伊拉”(Etteilla)。
1783年,埃特伊拉出版了《用塔罗牌重塑自我》( Manière de se récréer avec le jeu de cartes nommées tarots),即使这个书名听起来就像家养小精灵指南一样滑稽,但没人能否定它是世界上第一本塔罗牌占卜手册。
自此,马赛塔罗从纸牌游戏中升华,埃特伊拉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塔罗牌占卜师。
埃特伊拉重新排序了22张大阿卡纳牌,将1-8号牌解读为从混沌初开到第七日安息的八天,将9–12号牌解读为审慎、正义、节制、刚毅四大美德,余下的13-21号牌则成为人类生命历程和终极命运的象征。
而愚人牌,则被编号为第78号,称作“疯狂”(Folie),作为整副牌的最后一张,它象征人生旅途最终难逃愚妄虚无。
埃特伊拉声称这些改动源于埃及神庙与壁画中的符号,并借鉴了赫尔墨斯主义经典《Poimandres》(神智)中的宇宙观来构思塔罗的象征体系。
占卜时,他会按照当前占卜时太阳所在的星座开始,依次洗牌分发于模拟星盘的十二宫位置上,直到78张牌全部分完,这样,每个宫位上的数张牌对应占星命盘中的一个领域,从中便能推出询问者在该领域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如今我们所熟悉的塔罗牌占卜方式,大多都建立在埃特伊拉的雏形之上,他用一半埃及的想象和一半占星的技法,让塔罗牌第一次拥有了完整的“宇宙叙事”。
但即使如此,埃特伊拉却仍没能脱离世俗算命的“奇技淫巧”,真正让塔罗牌脱颖而出成为神秘学知识体系核心的人,还要再等半个多世纪才会出现。
埃特伊拉的塔罗牌阵
1853 列维
1832年,22岁的阿尔方斯·路易斯·康斯坦特(Alphonse Louis Constant)进入巴黎圣苏尔皮斯神学院,不久,他被晋铎为副执事(Sub-deacon),三年后又晋铎执事(Deacon),不出意外的话,下一步他就将正式成为一名神父。
然而,就在成为神父的一周前,他放弃了晋铎,退出修道生涯。
后世学者将路易斯放弃神职的原因归于“思想上的疑惑与异见”,这在他之后的履历中是有迹可循的,1840-1850年间,路易斯在孩子夭折与婚姻破裂的低谷中投身神秘主义,在波兰神秘学家胡安·沃伦斯基(Józef Hoene-Wroński)的影响下,他开始相信“唯有奥秘学才能解读圣经和历史中隐藏的真理”。
埃及元素此时仍是神秘主义的灵感之源
1853,路易斯将自己的名字转译为希伯来文“Éliphas Lévi Zahed”作为他的笔名,一个原本常见的天主教名字“Alphonse Louis”,自此成为神秘学历史中最为知名的姓名之一:
埃利法斯·列维(Éliphas Lévi)
在列维浩如烟海的著述里,我们只能勉强总结他的成就,他将犹太卡巴拉哲学、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的宇宙观、占星学与动物磁学等各门学科,融合进一套包罗万象的“高等魔法”理论中,再将其作为22张大阿尔卡纳牌的诠释。
1856年出版的《高级魔法的教义与仪式》(Dogme et rituel de la haute magie)成了列维确立自身地位的代表作。
列维将全书22个章节与22张大阿尔卡纳、22个希伯来文字母与22条生命之树的路径一一对应,打造了一场问寻者游历世界再返回自身的循环之旅。
完整的列维塔罗-卡巴拉体系
魔术师(Le bateleur)成为一号牌,对应字母Aleph(א,希伯来字母首位),象征问寻者迈入塔罗世界的第一步,对应卡巴拉的源头“Ein Sof(无限)”及第一个神圣显现“Keter(冠冕)”。
第二张牌女教皇(la grande prêtresse)则被列维解释为隐秘的智慧女神,她的膝上放着三重伟大的赫耳墨斯的《托特之书》,对应卡巴拉的智慧和直觉领悟。
以此类推到第十五张,恶魔(le diable)成为最能代表列维自身的形象,被他解读为著名的巴风特(Baphomet)五芒星山羊,人身羊首、雌雄同体、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在列维的理论中,恶魔牌隐含着二元对立统一的奥秘,将善与恶、阳与阴、电与磁融于一体。
列维经典的巴风特形象
愚人(le fou),则成为列维与前人(和后人)最大的不同,作为一张无编号或0号牌,它与希伯来文倒数第二个字母Shin(ש:形如三舌之火焰,字义为“牙”)相关联,拉丁箴言为“Dentes furca amens”(“蛇之舌,疯狂之齿”),暗指愚者说话荒谬、思虑不周。
然而,一旦无知被点化,愚者便可转化为“圣愚”,从零号重新归太一。于是,愚人被置于审判(le jugement)与世界(le monde)之间,象征愚昧经考验走向完成的过程。
需注意的是,后世的塔罗体系常将愚人放在第一位对应א,与列维不同
直至世界,造物完满、循环闭合,寻求者实现了与神性的合一,微观与宏观融为一体。在生命树上,世界既是“Malkuth(王国)”,亦与至高的“Keter(冠冕)”相呼应
终点即是起点,完成即是新的开端。
仍需注意的是,列维时代的小阿尔卡纳牌仍然没有图像,仅仅具有花色,因而此图仅作参考
某种意义上,列维在神秘学历史中扮演了康德在哲学史中的地位,过去的一切在他身上汇聚,未来的一切又从他发端。
他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信徒,却也不是纯粹的异教术士,而是一位站在十字架与五芒星交汇点上的神秘哲人。
列维对基督教教义的继承、重构与批判,正是其神秘学体系中最具争议但也最引人着迷的部分。
而在他的无数继承者中,即将诞生一个将卡巴拉塔罗体系开枝散叶的团体——黄金黎明会。
这个团体中的阿瑟·爱德华·韦特(A. E. Waite)与帕梅拉·柯尔曼·史密斯(Pamela Colman Smith)二人,又即将补全列维还没能阐释完全的部分——56张小阿尔卡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