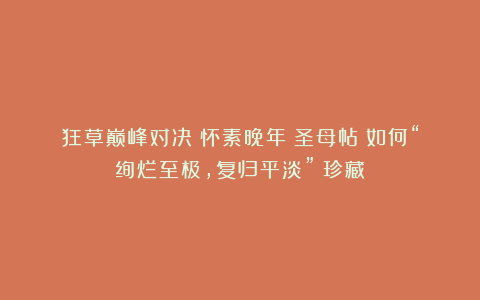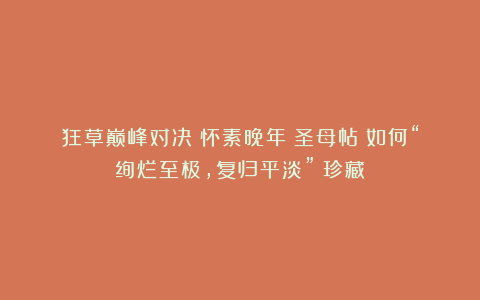|
怀素的《圣母帖》,是唐代狂草艺术的一座高峰。它不仅是书法技法的集大成之作,更将宗教叙事与文人精神熔铸一炉,展现了怀素晚年“绚烂至极,复归平淡”的艺术境界。若想真正读懂这卷墨宝,不妨从它的创作脉络、笔墨密码与历史回响说起。
唐贞元九年(793年),57岁的怀素已过知天命之年。这位曾以“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狂态震动长安的僧人,此时却悄然走出湖南,行至扬州江都宜陵镇(古称东陵)。或许是江南的烟柳画桥触发了某种心境,他提笔写下一段关于晋代杜姜、康氏二仙女的传说——这便是《圣母帖》的由来。帖中文字不仅记述了二仙“蹑灵升天”“庇佑江淮”的神话,更暗含隋代炀帝推崇道教、修建仙宫的历史背景,将民间信仰与文人雅趣交织成一片墨海云烟。
若说怀素早期的《自叙帖》是“骤雨旋风”般的激情宣泄,《圣母帖》则是他晚年沉淀后的“复归平淡”。前者以“狂”为骨,笔势如万马奔腾,牵丝连绵处尽显少年意气;后者却以“韵”为魂,用笔更趋圆浑古茂。你看那线条,虽仍保留狂草的自由,却多了几分中锋行笔的沉稳——瘦劲如篆籀,弹性似弓弦,转折处的篆书笔意若隐若现,仿佛“霓裳仙驾降空”一句,笔锋轻提又按下,便带出了仙人乘云的飘逸感。更妙的是章法,字态大小随势而变,行距宽绰却不显松散,看似狂放的笔墨里藏着严谨的秩序,恰如禅意里的“自在”与“规矩”。
这样的笔墨,自然引来了历代书家的激赏。清代梁巘直言:“《圣母帖》圆浑古茂,多带章草,较《自叙帖》更佳。”在他看来,这卷作品是怀素“通会之际”的至高成就——既非初期的肆意挥洒,亦非刻意的法度束缚,而是技法与心性的完美融合。明代王世贞则用“匀稳清熟,妙不可言”概括其魅力,道尽了怀素对晋唐笔法的精熟驾驭。更有趣的是,八大山人曾收藏宋拓本并题跋,称其“醒书得索幼安与张有道之整”,足见其对后世书风的深远影响。
从书法史的长河看,《圣母帖》的意义远不止于技法创新。它标志着怀素从早期“纵情恣意”的狂草阶段,转向晚年“法度内化”的成熟境界,恰如孙过庭《书谱》所言“平正—险绝—平正”的书学轨迹。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张旭与怀素并称“狂草双峰”的固有认知——相较于张旭“呼叫狂走”的癫狂,怀素的狂草更多了一份文人的理性沉淀,而这卷《圣母帖》,正是这种转变的最佳注脚。
如今,我们仍能在西安碑林第二室见到《圣母帖》的原刻石,故宫博物院藏的宋拓陕刻本更是稀世珍品。八大山人旧藏本上,他的题跋至今未干,仿佛在诉说着这卷墨宝跨越时空的魅力。它不仅是研究唐代草书演变的经典范本,更是一扇窗口——透过那些圆转流畅的线条,我们能看见一位僧人对生命、对信仰、对艺术的深刻思考:所谓“狂草”,从来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心性的自然流淌。当怀素在《圣母帖》中写下“仙阶崇者灵感远,丰功迈者神应速”时,或许他早已明白:真正的“灵感”与“神应”,原是技法与心境的双重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