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将军读哲学之“读点中国哲学”之十三
四、《大学》和《中庸》在这一时期渐成儒家之经典
孔子的儒家学说极富精神魄力,既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孔子本人是一等一的气象阔大的人物。但在孟轲、荀卿之前的及门弟子中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发挥光大他的哲学。这一时段的儒生,极其成就,只是在一个“孝”字和一个“礼”字上,做了一些补绽的工夫。这样一来,儒家学说便在中国哲学史上沉寂了一二百年时间。
孔子死后一二百年间,在孟子、荀子出现之前,儒家总该有几部书延续儒家的思想,使其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吧,不然,极端重视伦常主义的儒家,何以忽然出现一个尊崇个人的孟子?极重君权的儒家,何以有孟子的民权主义思想?儒家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何以会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心理的人生哲学的出现?这样,《大学》和《中庸》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使儒家思想的发展有脉络可寻了。
《大学》一书,不知何人所作。后人因书中有“曾子曰”,遂以为是曾子和他的门人所作。这有待考证。《中庸》古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大学》、《中庸》是孟子、荀子之前的儒书,在孔子和孟荀之间延续着儒家的学说。
按胡适先生的观点,《大学》和《中庸》两部书的要点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法。《大学》、《中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方法。后代的宋儒极力推崇这两部书,其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程子论《大学》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朱子序《中庸》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终始、先后,便是方法问题。《大学》所给出的方法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在中华大地上,非常强势地飘荡了两千多年。
而《中庸》的方法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之”之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行”之范围乃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大学》、《中庸》所讲的方法明白明了,条理清楚。在宋儒时代,对“格物”究竟作何解?对“尊德性”与“道学问”究竟谁先谁后提出了质疑,但在这一时期是不存在问题的。
第二:个人的注重。孔子之后的儒家有许多分派,其中有一派把“孝”字看得太重了,以至于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我”不是一个“我”,只是“我父母的儿子”。这样的伦理观念最终会倒致两个结果,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是极端的为人主义。这两种极端学说的盛行,使儒家不由得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大学》的主要方法是把“修身”作为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这个“身”的“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了。如《孝经》上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而《大学》上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大学》与《孝经》的不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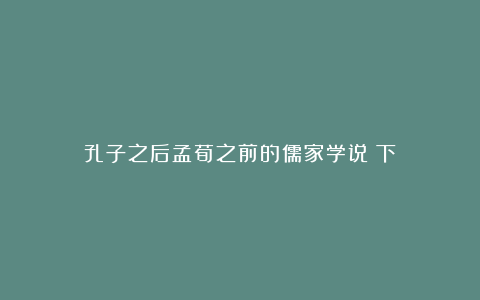
《中庸》上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曾子说过:“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的意思,和《中庸》中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的主张恰好相反,一个是“孝”的人生哲学,一个是“修身”的人生哲学。
《中庸》最重一个“诚”字,诚即是充分发展人的本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一路做去,若能充分发挥天性的诚,这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中庸》把个人看作本来是含有诚的天性的,极看重个人的地位,“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
第三:心理的研究。儒家在《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开始注重个人心理的研究。早期的儒学只注重实际的伦理和政治,只注重礼乐仪节,不讲究心理的内观。到了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时,便开始有了内省的工夫了,但触及所“省”内容则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还只是外在的伦理。儒学到了《大学》时代便不同了,《大学》的心理学说,重要的一点在于分别“心”与“意”。“揔(zǒng同“总”,总括、汇集;持、揽)包万虑谓之心,为情所忆念谓之意。”这是心与意的界说,心有所在便是意,如常说的“居心”与“用意”。《大学》的“意”便是“居心”。
《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便是《大学》的“内观的儒学”,如人常说的“居心总要对得住自己”。
大凡论是非善恶,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从“居心”这方面立论,一种是从“效果”这方面立论。义不义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大学》注重诚意,自然是偏向居心这方面。所以《大学》的政治哲学主张:“是故君子先慎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这是极端的非功利派政治论,其根本点是在于诚意。
《大学》论“正心”时说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怨恨发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大学》中说的“正”,就是《中庸》上说的“中”。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忿懥、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中庸》说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是“和”了。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过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和”了。所以《中庸》说:“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的人生哲学只是要人喜怒哀乐皆无过无不及,如饮食学那“知味”之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饿肚子。
后记:
孔子之后,孟荀之前这一二百年间,儒门并没有出现旗手级标志性人物,但儒学的发展并未停滞。这期间的儒门之人在其门派内部进行着自己的“百家争鸣”,八大派之间进行着理论之争和学术争鸣,活跃着儒家思想。在相互争论中,孔子嫡传一派,对“孝”、“礼”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完善,形成较为完备的一套理论。另外,这期间的儒家弟子,对《大学》和《中庸》进行了儒家式的解释和发展完善,逐渐确立了这两部经典为儒家的理论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大量的儒门子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理论工作,为迎接儒家“亚圣”孟子及儒门“别出心裁”者荀子的出世,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