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阿米蒂奇/ Quanta杂志
1983年,八十多岁的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站在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讲台上。她以不愿抛头露面而闻名——几乎像个隐士——但按照诺贝尔奖的惯例,人们在获奖后都会发表演讲,于是她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DNA序列如何在基因组中移动的实验。演讲接近尾声时,她透过金属框眼镜眨着眼睛,换了个话题,问道:“细胞对自己了解多少?”
麦克林托克以古怪著称。不过,她的问题似乎更像是出自一位哲学家,而非植物遗传学家。她接着描述了在实验室实验中观察到的植物细胞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做出的反应。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它们似乎以“超出我们目前理解能力”的方式进行调整。细胞对自己了解多少?她说,这将是未来生物学家的工作。
四十年后,麦克林托克的问题依然具有影响力。一些未来的生物学家如今正努力探究“认知”对单细胞的意义,他们在单细胞生物和非神经人类细胞中寻找基本认知现象的迹象——比如记忆和学习的能力。长期以来,科学界一直认为多细胞神经系统是此类能力的先决条件,但新的研究表明,单细胞也会记录它们的经历,这似乎是为了适应环境。
去年年底,神经科学家尼古拉·库库什金 (Nikolay Kukushkin) 和他的导师、纽约大学的托马斯·J·卡鲁 (Thomas J. Carew) 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项引人深思的研究,他们发现,培养皿中生长的人类肾脏细胞能够“记住”化学信号的模式(打开新标签页)当这些记忆以规律的间隔呈现时——这是一种所有动物都常见的记忆现象,但迄今为止在神经系统之外从未见过。库库什金是少数几位充满热情的研究人员之一,他们致力于研究“无神经”或“无脑”的记忆形式。细胞对自己了解多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研究表明,麦克林托克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无脑学习
长期以来,神经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记忆和学习是大脑“突触可塑性”的结果。在一次体验中同时活跃的神经元簇之间的连接会增强形成网络,即使在体验结束后仍保持活跃,从而将其作为记忆延续下去。这种现象可以用“同时放电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来表达,它塑造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记忆的理解。但是,如果单个非神经细胞也能记忆和学习,那么神经元网络就无法解释一切了。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神经系统之外的细胞会因为自身经历而发生改变,从而促进生存,这合情合理。“记忆对所有生命系统都至关重要,包括那些比大脑出现早数亿年的系统,”萨姆·格什曼说道。(打开新标签页),哈佛大学认知科学家。
无细胞黏菌在觅食时会留下化学痕迹,提醒它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细菌在沿着化学梯度向更有利的环境迁移时,会比较当前和以前的环境。Gershman 预感这些“更古老的记忆形式”可能对突触可塑性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以至于他最近在他的实验室里增加了一个湿实验室,以系统地研究单细胞纤毛虫Stentor coeruleus。
对于认知科学家来说,纤毛虫可能听起来像是一个非传统的研究对象,但对这些单细胞生物记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动物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詹宁斯在其著作《低等生物的行为》中详细阐述了实验(打开新标签页)早在1906年,人们就发现了一种类似的纤毛虫——S. roeselii 。这些喇叭状的细胞在世界各地的淡水池塘中都能找到,它们利用粘稠的“固着器”将自己固定在环境中,并通过拍打毛发状的纤毛来吸收漂浮的食物颗粒。
1906 年,赫伯特·斯宾塞·詹宁斯 (Herbert Spencer Jennings)(右)的实验表明,单细胞纤毛虫Stentor roeselii(左)具有学习能力——它“因经历的经历而改变”,他写道。
赫伯特·斯宾塞·詹宁斯(Herbert Spencer Jennings)通过档案馆;美国哲学学会/科学来源
在一系列实验中,詹宁斯反复向来自附近池塘的一些纤毛原生生物喷射一种刺激性的红色染料,并观察它们的反应。他发现,首先,个体会弯腰避开他用来分配染料的玻璃吸管。如果这不能阻止刺激,原生生物就会用纤毛向吸管吐水。如果这仍然无法清除染料,它们就会迅速收缩回固着器中。弯腰、吐水、躲藏。确定了这一系列反应后,詹宁斯决定在短暂的延迟后重复实验,以测试罗氏细丝藻的记忆力。
纤毛虫躲藏了大约半分钟后,从固定器中钻出,再次遇到了染料。詹宁斯想知道, S. roeselii会再次经历整个躲避过程吗?还是说,它会“被过去的经历改变”?换句话说,细胞会学习吗?他发现,答案“特别有趣”。再次面对无情的染料,它立即收缩,跳过了前导步骤。在最后一系列的钻出和收缩之后,纤毛虫最终感到厌烦,拔起桩子游走了,大概是在寻找一个不那么有害的地方安顿下来。
在詹宁斯时代,对单细胞行为的主流观点是,像S. roeselii这样的生物体是由“向性”驱动的,即对光、化学梯度和重力等外界因素的自动反应。但詹宁斯的研究表明,单细胞生物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强其反应,这表明它将先前的经验融入到其行为中——实际上,它们能够记忆。
神经科学家萨姆·格什曼表示, Stentor roeselii的特征“非常类似于”神经元。“纤毛虫拥有像神经元一样可兴奋的膜,而且与神经元更相似的是,它们具有动作电位。”
讽刺的是,斯滕托的记忆几乎被遗忘了。詹宁斯的实验被广泛认为无法重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细胞学习的研究经常被忽视,甚至被认为是边缘科学。后来,在2010年,格什曼的同事杰里米·古纳瓦德纳(打开新标签页)对此很感兴趣。Gunawardena 是一位数学家,后来成为系统生物学家,直到最近还在哈佛医学院任教。他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翻找资料,发现唯一一次真正尝试重复 Jennings 实验的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Stentor coeruleus 上进行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受到这个明显错误的鼓舞,他成功说服了一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加入他,进行了一项长达数年、不分昼夜的“臭鼬工厂”项目,试图用正确的生物重复 Jennings 的工作。当他们的结果(打开新标签页)于 2019 年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詹宁斯的观点:S. roeselii实际上可以“改变主意”。
Gunawardena 和 Gershman 为细胞学习领域的同行们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并不多,”Gershman 说。他们也是历史爱好者;他们的论文经常以温柔的笔触描绘那些曾经饱受诟病的科学家,而这项研究如今正在为他们带来救赎。在为 Jennings 平反之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了名气不那么响亮的 Beatrice Gelber。(打开新标签页)是一位反传统的科学家,在她声称“训练”了另一种单细胞纤毛虫——草履虫,使其能够与一根无涂层的金属丝结合后,于 20 世纪 60 年代离开了芝加哥大学。(打开新标签页)食物——想想巴甫洛夫的培养皿。盖尔伯严谨的研究成果是少数几项关于单细胞联想学习的研究之一。古纳瓦德纳认为,与詹宁斯一样,她在那个时代被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她训练的草履虫驳斥了细胞无法学习的主流正统观念。
他说,现在我们了解得更多了。
细胞的视角
如果无脑单细胞生物体内存在一种细胞内记忆机制,那么考虑到它所呈现的优势,我们很可能继承了某种形式的记忆。所有真核细胞,包括我们自己的细胞,其进化起源都追溯到一个自由生活的祖先。这份遗产在我们每一个细胞中回荡,将我们的命运与广阔的单细胞世界紧密相连,在这个世界中,原生动物等生物应对威胁、寻求救助,并感知从生到死的道路。
库库什金认为,在细胞层面上,记忆就是对变化的具体反应。
我们大多数人很难跳出主观的、内省的经验去想象这样一个细胞的记忆会是什么样子。但对于尼古拉·库库什金来说(打开新标签页)对于一位接受过分子生物学培训的人来说,这很容易理解。“真的,当我闭上眼睛时,我就在细胞里,”他在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实验室里通过视频电话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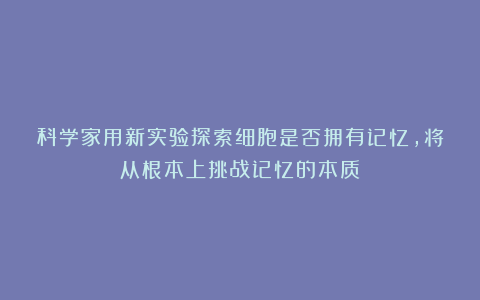
库库什金解释说,细胞的整个存在都发生在多细胞躯体温暖黑暗的环境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谓的“体验”是化学物质在时间间隔内的模式:营养物质、盐分、激素以及来自邻近细胞的信号分子。这些化学物质以不同的方式(例如,引发分子或表观遗传变化)和不同的速率影响细胞。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细胞对新信号的响应方式。库库什金认为,在细胞层面上,这就是记忆:对变化的具体反应。记忆、记忆者和记忆行为之间没有区别。“对细胞来说,”他说,“它们都是一样的。”
为了阐明这一想法,库库什金最近决定尝试在细胞中找出所有动物共有的记忆特征,该特征由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于1885年首次描述。艾宾浩斯亲自做了实验:他花了数年时间反复记忆一串无意义的音节,以测试自己的记忆力。他发现,如果能控制记忆节奏,记住音节序列比一次性学习所有内容更容易——这就是“间隔效应”,任何曾经为了考试而临时抱佛脚,并意识到自己应该早点开始学习的人都应该对此很熟悉。
库库什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从艾宾浩斯发现间隔效应以来,它“已被证明是许多不同动物记忆中最不可动摇的特性之一”。(打开新标签页)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在人类、蜜蜂、海蛞蝓和果蝇等不同生命形式中都有发现——以至于库库什金怀疑它是否可能一直延伸到细胞。为了找到答案,他需要测量非神经细胞对间隔化学模式的反应程度。
库库什金和他的同事首先分离培养了人类肾细胞和未成熟的神经细胞。然后,他们试图模拟他们所了解的神经元的化学“体验”。他们的关键创新在于,利用一种名为cAMP反应元件(CRE)的DNA序列来测量这些细胞对化学信号的内部反应。该DNA序列是许多细胞信号通路(包括神经元信号通路)的一部分。在实验中,这个基因代表着记忆。通过对两种细胞系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在CRE被激活时产生一种发光的蛋白质,他们能够测量细胞何时形成记忆,以及记忆持续的时间。
对多种生物的研究表明,非神经细胞会记录它们的经历,例如,无细胞黏菌(左),它会留下化学提醒物,涡虫(右),它会在被斩首后对训练做出反应。
Dennis Kunkel 显微镜/ Science Source;Bazzano 摄影
然后,在一个被库库什金描述为繁琐的、如同时钟般精准移液的过程里,他们将细胞暴露于精确定时的化学物质爆发中,这些化学物质模拟了大脑中神经递质的爆发。库库什金的团队发现,神经细胞和肾脏细胞都能精细地区分这些模式。稳定的三分钟爆发激活了CRE,使细胞发光数小时。但同样剂量的化学物质,以四次间隔10分钟的较短脉冲形式释放,却能使培养皿发光超过一天,表明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一段记忆。
库库什金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神经细胞能够计数并检测模式。尽管它们无法像神经元那样快速完成这些任务,但它们确实能够记忆,而且当刺激以一定的间隔传递时,它们似乎能够记住更长时间——这是所有动物记忆形成的一个标志。
格什曼说,直觉上,这很有道理。从细胞或任何其他表现出间隔效应的生物系统的角度来看,间隔信息表明环境相当稳定且缓慢变化:一个稳定的世界。另一方面,大量信息——一次化学物质的爆发或一次通宵的临时抱佛脚——可能代表着更混乱环境中的偶然事件。“如果世界变化非常快,你应该更容易忘记事情,因为你学到的东西的保质期会更短,”格什曼说。“它们以后不会那么有用,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动态变化与细胞的存在息息相关,就像与我们的存在一样。
疫苗接种是一种记忆。伤疤、孩子、书籍也是一种记忆。
库库什金最近自称“分子哲学家”,他相当肯定,无论使用哪种细胞,他的发现都会一样。“我敢打赌,任何人最喜欢的细胞系都会表现出间隔效应,”他说。“我认为应该默认记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有这些单细胞都会记忆,植物也会记忆,神经元和所有类型的细胞都以相同的方式记忆。举证责任不应该在于证明它们是相同的。举证责任应该在于证明它们是不同的。”
格什曼对此表示赞同。“在大脑中,记忆的动态与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有关:这是一种多细胞现象,”他说。“但在单细胞中,我们谈论的可能是细胞内分子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动态。不同的物理机制可以产生共同的认知过程,就像我可以用钢笔、铅笔、打字机或电脑写信一样。”
归根结底,重要的是那封信——也就是记忆。
结构性偏见
古纳瓦德纳表示,科学界一直不愿接受细胞规模记忆,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因素。詹宁斯和盖尔伯等早期研究人员的发现之所以被“记忆洞”化,是因为它们与当时盛行的理论不符:詹宁斯在斯坦托尔发现的记忆违背了“向性”的教条,而这一教条启发了盖尔伯时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这两种观点都假设了一个由生物自动机组成的生命世界,它们通过预先编程的反应进行循环。能够学习和适应的细胞并不属于这类模型。
“我们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目前在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任教的古纳瓦德纳说道。“这只是人类与世界互动的自然组成部分……在科学领域,我们确实低估了这些偏见在组织科学界以及确定什么是合适的科学和什么是不合适的科学方面所起的作用。”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尼古拉·库库什金 (Nikolay Kukushkin) 表示:“我认为应该默认记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有类型的细胞都以相同的方式记忆。”
这也是一个语义问题。像所有重要的术语一样,“记忆”的含义丰富、不精确,不同学科对其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它对计算机科学家和生物学家来说含义不同——更不用说我们其他人了。“当你问一个普通人记忆是什么时,他们会内省地思考,”库库什金说。“他们会想,’嗯,我闭上眼睛,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记忆。’但这不是我们在科学中研究的东西。”
库库什金写道,在神经科学中,记忆最常见的定义是,它是经历之后留下的、能够改变未来行为的东西。这是一种行为学定义;衡量记忆的唯一方法是观察未来的行为。想象一下,罗氏链球菌(S. roeselii)会迅速回到它的固定器中,或者实验室老鼠看到之前被它缠住的带电迷宫时会僵住。在这些情况下,生物体的反应是先前经历留下痕迹的线索。
但记忆是否只有与外部行为关联时才算记忆?“这似乎是一个武断的决定,”库库什金说。“我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是这样决定的,因为在与动物合作时,行为是很容易测量的。我认为,行为最初是可以测量的,后来却成为了记忆的定义。”
行为告诉我们记忆已经形成,但却无法解释记忆形成的原因、方式和地点。此外,记忆还受到规模的限制。以加州海兔(Aplysia californica)为例,这是一种肌肉发达的海蛞蝓,拥有巨大的神经元(最大的神经元大约相当于一美分硬币上的一个字母大小)。神经科学家喜欢用加州海兔进行记忆实验,因为它的生理反应很容易测量——戳它一下,它就会缩一下——而且这些反应可以清晰地映射到参与实验的少数几个感觉和运动神经元上。
库库什金表示,海蛞蝓的例子可能会使神经科学的行为偏差更加复杂。假设你电击它的尾巴,引发了它的防御反射。如果第二天你再次电击它,发现它的防御反射比之前更强烈,那么这便是行为证据,表明海蛞蝓记得最初的电击。任何神经科学家都会将其与记忆联系起来。
加州海兔(Aplysia californica)拥有巨大的神经元,因此很容易作为记忆的模型进行研究。
但是如果你把那条海蛞蝓拆开(打开新标签页)只留下静止的神经元?与完整的生物不同,这些神经元无法收缩,所以不会有任何可见的反应。记忆消失了吗?当然不会,但如果没有外部验证,记忆的行为定义就会失效。“我们不再称之为记忆,”库库什金说。“我们称之为记忆机制,我们称之为突触变化是记忆的基础,我们称之为记忆的类似物。但我们不称之为记忆,我认为这是武断的。”
或许,记忆的定义应该超越行为本身,涵盖更多过去的记录。疫苗接种就是一种记忆。伤疤、孩子、书籍也是一种记忆。“如果你留下一个脚印,它就是一段记忆,”格什曼说道。将记忆解读为一种物理事件——在世界或自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将涵盖细胞内发生的生化变化。“生物系统已经进化到能够利用这些保存信息的物理过程,并将其用于自身目的,”格什曼说道。
那么,细胞对自己了解多少呢?或许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问题更贴切的版本是:细胞能记住什么?在生存方面,细胞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它对世界的了解重要:它如何整合自身经验信息,决定何时屈服、何时战斗、何时突围。
细胞保存着维持其存在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是如此。如今,随着细胞记忆研究人员重新审视过去被遗弃的实验线索,他们也在探索记忆与其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的社会环境如何决定哪些想法得以保留,哪些想法被遗忘。这仿佛是一个领域从长达50年的失忆中苏醒过来。幸运的是,记忆正在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