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话,就一言难尽了!’张姥姥起身为伍、李二人各倒了一杯茶,又吩咐人’药煎好了就快送过来’,这才坐下叹道,’这个故事儿外头人知道的很少,我们两家也都不张扬﹣﹣说起来有七百多年的光阴了!’
听见这话,云娘不禁一怔。伍次友心中推算,七百年前,正是后唐五代之时﹣﹣他也没有料到,张孔两家竟有这么深的渊源。
张姥姥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那时正是后梁年间,因天下大乱,孔府的家道也就中落了。
‘当时的第四十二代老公爷孔光嗣,已是三代单传,老公爷望五十的人才得了个麟儿,起名叫孔仁玉。三千亩地一棵谷,就这么一根独苗苗,怕在府里养不活,便叫奶妈子抱回家去养﹣﹣就是我们张家头一辈姥姥,离现在已经传了二十一世。’
伍次友听至此,不禁点头:原来这’姥姥’也是张家世袭的。
‘当时有个洒扫户叫刘末,因进府当差,改名儿叫孔末。老公爷瞧着他勤谨靠实,就把府库、名器、财帛和阙里六十宗户本支孔家的谱牒都交给了他掌管,开初人们也没当回事。’
‘他是个洒扫户么?’云娘问道,’不是听说孔家’男不能为奴,女不能为婢’么?’
‘那是明朝以后才定的男不为奴,女不为婢,前头进孔府当差都得改为孔姓。’张姥姥解释道,’-﹣谁想这孔末见世道乱了,就在府中作耗,
盗了府库的银子,又私改了祖宗谱牒,日子久了,竟没人不说他原本就姓孔,是圣人的血脉。’乾化三年八月十五,老公爷在花园里设了酒筵,请阖府伙计吃酒。孔末在旁掌筵,喝到二更天,扶着醉醺醺的老公爷回房,趁没人,竟下毒手勒死了老人家。’说到这里,云娘忍不住问:’这奴才如此大胆,官府难道就瞧着不管?”好姑娘哩,那时正逢天下大乱!’张姥姥拍手叹道,’五十来年换了五个朝廷,哪个官府有心管这些子事?’
‘那孩子呢?’云娘又问,’过八月十五,难道不接回府去?’张姥姥点头道:’孩子命大,那日正好发烧,公爷倒是派人来接过一回,因风大,姥姥不让回去﹣﹣那孔末杀了老公爷,出来召集孔府的人说:老公爷已经归天,临死有话,叫他孔末接印。还说孔仁玉是老公爷的侍妾与外人的私生子儿,接不得孔氏香烟,命人抓来杀掉。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又是打灯笼燃火把,又是举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
‘姥姥一家人欢欢喜喜拜完月老儿,已是后半夜了,正要睡觉,听见门外像发大水似地号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一开门,原是孔末带着几十个人蜂拥进来﹣-﹣下子把姥姥吓愣了。孔末在灯影里,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刀,立逼姥姥交出孔仁玉来,若不答应,便满门杀绝!
‘姥姥抖抖索索进了里间,见自己最小的娇子狗儿正和仁玉在炕上争月饼,叽叽嘎嘎地满炕爬……上去一把抱起仁玉,亲了亲,眼泪像断线珠子一样落了下来。欲待往外抱,实在割舍不得;又抱起狗儿,狗儿两只温乎乎的小手拿着月饼直往姥姥口里塞,口里叫着’娘,吃,吃,吃嘛!’……娘生孩儿养,哪个都是心头肉啊!’
说到这里,张姥姥凄声长叹,伍次友早已明白,望着幽幽灯光不言语,云娘的泪水已是顺颊而下。张姥姥擦了擦眼又道:
‘姥姥正迟疑间,门’哗’地被推开了!孔末一步跨进屋里,杀气腾腾地问:’哪个是孔仁玉?’两个孩子见这个阵仗,吓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子三个抱成一团,哭得天昏地暗……姥姥暗想,我好歹有三个儿,可孔家只这一条血根!咬了咬牙抱起狗儿递给了孔末……那狗儿又惊又怕,抱着姥姥脖子死不丢手,哭着叫:’娘,我怕……’
”娇儿,别怕……’姥姥拍拍狗儿,把炕上的糖果月饼都塞到孩子怀里,说’不怕,不怕,一会儿就……好了!’
‘孔末认定了这孩子就是孔仁玉,一把抓过去,狞着脸笑着,当时就……’说到这里,张姥姥擦一把眼泪。屋子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七百多年前东厢屋里发生的一场惨案仿佛就在眼前。不要说伍次友,连杀人如麻的李云娘也是凄侧心酸,半晌方抬头问道:’那后来呢?’
‘后来,张家就避祸迁走了,在石门一带深山里住了十几年,姥姥整日里纺线、织布,给人家帮工绣花,洗衣裳缝穷,攒的钱一点点都拿出来供这孔仁玉读书。后唐明宗年间孔仁玉进京赶考,朝廷授了太学生。这时,姥姥才敢把仁玉的身世向他明说了,可是姥姥已双眼失明了。
‘仁玉原本是回来接母亲进京的,听了姥姥的叙说,连夜赶回京城,把自己凄惨身世细细写成折子呈奏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曲阜拿了孔末,碎剐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仁玉接了,这就是孔家四十三代’中兴祖’了。
‘为报张家这段恩情,孔仁玉上奏朝廷,奉旨尊张家为孔家世代恩亲。’姥姥’是官称,代代都是张家长房媳妇承袭,算到我这里,已是二十一代了。’
娘听完,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大哥一天都在纳闷,孔令培又是孔家的人,又是官府的人,这么霸道,到了姥姥这里却为什么被治得服服帖帖的呢!’
‘他算什么!七百来年,我们张家和孔家联亲的多得很,我的大丫头就是衍圣公夫人,每任公爷一袭位便照原样赠过一根龙头竹节拐杖,连衍圣公都能打的﹣﹣我们庄稼人不指着这些个吃饭,倒也不在乎这恩亲不恩亲。不过这是孔家立下的家法祖训,代代相传,孔家的人最重这个。孔令培有几个胆子,就敢来搜这院子?’
半个月后,李云娘的伤势已经痊愈,伍次友也恢复了嗓音,二人便计议着上路的事。照云娘的想法,伍次友应该即刻进京,留在这里迟早还是要出事,而且皇上现在正筹谋着撤藩大事,正好可以为他划策。但伍次友却另有打算:自己已被赐金还山,在外头逛了一圈子又回到京师,脸往什么地方放呢?所以他已拿定主意不再做官;可是既然不做官,又忙着进京干什么?
‘先生既不回北京,’云娘说道,’那我可要走了!’和伍次友相处这么长时间,她以女子特有的细心,体察伍次友仍是放不下与苏麻喇姑的那段情意,她也直觉地感到,伍苏二人重新结合是不可能的,既如此,何必再继续搅下去呢?
伍次友看着云娘,半晌才道:’要走,你就去吧,这是没法儿的事。
不过有一件还要想想,张姥姥这样待我们,总得要报答一下的。’
‘真是的!’云娘猛醒过来:这样的大恩不报,那还算个人?想想说道:’连我们的衣裳都是人家的,身上又一个钱没有,那只有今夜再做案了。’
‘云娘!’伍次友发了脾气,’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依旧这样?你做案,别人奈何不了你,也只道是遇了恃强霸道的强人。可那丢了东西、死了人的家不也像张家以前出事一样?-﹣那是五代乱世,当今正要安民治国,你还是这么着怎么成?再说,姥姥若知道了你这钱的来路,岂肯收你的?’
‘那你说怎么办?’云娘也犯了踌躇,犹豫片刻又道,’不然就把鸡血玉砚变了钱?’她的脸色又有些发白了。
伍次友无可奈何地笑笑。他并不是丢不开苏麻喇姑,也不是一点儿也不爱云娘。他在感情上道义上有卸不下的重负,觉得自己已经不幸,又何必再扯上别人和自己一道儿不幸!见云娘这样,又不忍过于决绝,便温语劝慰道:’云娘,你听我说,世上有虽非夫妻而情过夫妻者,也有虽非兄妹而谊过于兄妹者。我和苏麻喇姑、和你,此时都是这种心境。你总拿鸡血砚来发作我,既戳你的心,又伤我的情,这又何必呢?张姥姥这个恩,不是拿钱能报得了的……’
‘对了!’张姥姥已在外头听了多时,伍次友这个话她听得又感动,又难过,见二人争执得拿不定主意,便掀了帘子进来说道,’我穿衣有棉田、织机,吃饭有麦米、磨坊,要你的钱做什么用?不干净的钱我更不要!妞啊,我两个儿出去做生意,家里头连个说话的也没有,你不能陪姥姥多住些日子,给姥姥说说话儿,去去心焦也是好的呀!’
张姥姥慈爱爽朗,说的十分动情,自幼失怙的云娘只觉万感交集,’呜’地一声哭着扑到姥姥怀里,抽咽着说道:’姥姥!您若不嫌弃,我就认了您老作干娘吧!’
‘我心里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嫌弃?’张姥姥抚摸着云娘油黑的头发,又转脸对伍次友道,’我上回说过,孔家尚任在石门山读书,想着要写一本什么书。这么有学问,在这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指点指点他,若能成了材料,不是既给皇上办了事,又报了我的’恩’?唉!我的那两个儿自小就不爱读书,要不然﹣’
正说话间,院里传来大说大笑之声:’姥姥带的好信儿!那位伍先生住在何处?’张姥姥一手扯起云娘笑道:’正说他,他就到!咱们娘俩前头说话去﹣-喂,聘之,到这屋里来罢!’说着和云娘起身去了。伍次友心知孔尚任来了,刚立起身来,孔尚任已呵呵笑着大踏步进来,看了伍次友一眼,一个长揖,
朗声道: ‘落拓不羁书生拜见奇遇不偶书生!’
‘好!’只此一语便大合伍次友胃口,一边让座儿,一边笑道,’窥破万缘书生,迎候豪气干云书生﹣﹣请坐!’
孔尚任将后摆一撩,大咧咧地在伍次友的对面坐下。伍次友这才仔细打量,孔尚任不过二十岁上下,只穿一件绛红长袍,腰间束一条浅蓝色带子,刚剃过头,也未戴帽子,发辫黑光油亮,丹凤目灼灼有神,心中不禁暗赞:’好一表人才!又是圣人后裔,可谓资质俱佳!’口里却笑道:’久闻你的大名!听姥姥说,你在写一本什么’黄子’书,是否准许不才拜读一番?’
‘是一部传奇,’孔尚任笑吟吟说道,’不知先生于此道有何高见?’显然,他也很喜欢伍次友的脾性。
伍次友大感兴趣,口里却道:’传奇,小道耳!你既为秀才,为什么不去研读经史、八股,却躲在石门山上做什么传奇?’
‘传奇虽属小道,却源于大道。’孔尚任笑道,’对诗词、曲赋、稗官野史,抑或经史子集,若有一路不精,难写传奇。您不是喜欢八股文么,我有一篇,请指教!’说着,摇晃着脑袋念念有词道: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
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籍。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
‘哈哈哈哈……’孔尚任尚未念完,伍次友已是纵声大笑,他很久没有这样畅快了,’真骂尽天下腐烂恶劣的墨卷,我且给你续一句:
思入时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孔尚任听了也不禁大笑。
‘该请丑媳妇出来,见见公婆了。’伍次友笑着说道。
孔尚任听了,身子向前一倾,正色说道:’我这部传奇,只为识者读,不为昏者误,写的便是一代兴亡的色与气。敢问,何为色?’
‘色者,离合之象也!’伍次友循传奇的义理答道,’男有其俦,女有其伍,悲欢离合寓其中,锱铢不爽!’说至此,猛的想到自身,伍次友敛了笑容。
‘嗯。’孔尚任很满意这个答复,又问,’那么,气呢?’
伍次友因听他方才讲到’一代兴亡’的话,沉吟了一下,缓缓答道:’气者,兴亡之数也,君子为朋,小人为党,错综纷乱寓其中,无纤毫之差!’想想又补了一句,’我这不过是据理而言、据情而断,写得好了自然就是如此;写得不好,强捏造一个传奇出来,我还没工夫看呢!’说着,跷起二郎腿来,看着孔尚任笑。
孔尚任听着这些话,句句在行,点了点头,起身在屋里徘徊几步,说道:’我做了首《金菊香》,先吟给先生一听:
偏有那文章湖海旧相知,剥啄敲门来问你,带几篇新诗出袖底,硬教评批,君莫逼,这千秋让人矣!
‘好好好!’伍次友大笑道,’张姥姥还说要我指点,只听你这一曲,我就无可指点,这’千秋’你不要让我,我也不逼你﹣﹣尽情拿来我先赏就是了。’
孔尚任这才将一卷文稿从怀中取出来。伍次友双手接过,诧异地问道:’就是这些么?’孔尚任一改方才狂放之态,笑着点头道:’这是一部《桃花扇》,共分四卷,还未完稿,您先看一卷吧,我准备用十年的工夫改好它,才肯拿出去呢﹣﹣只可惜无缘见到侯公子,有些地方写的不很顺手!”那你今日不虚此行,侯方域前辈正是在下受业之师!’伍次友看了一眼又惊又喜的孔尚任,便开始翻稿。孔尚任自静静坐在一旁吃茶。
半晌没有动静,孔尚任起身站到窗前,观赏墙头横卧着的一枝老梅,正拟构思一篇诗词,犹豫不定时,猛听’砰’的一声,回头一看却是伍次友看得忘了情,在击节称赞!
‘妙哉!’伍次友笑道,’这《访翠》一出,亏你怎么想来!’说着他一边翻念着,一边手舞足蹈。已有些着魔:
……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
‘确是妙语如珠!’伍次友连连赞叹,’二十年所读文章,不及君这一篇!你看﹣’
结罗帕,烟花雁行;逢令节,齐斗新妆。有海错、江瑶、玉液浆。拨琴玩,笙箫嘹亮。
伍次友笑道:’字字余香可嚼,句句精辟动心!天耶天乎!你这样的人竟生在山东,真真不可思议!’显然,伍次友认为只有江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采。
‘先生不必赞了。’孔尚任也很高兴,’有何补阙之处也该说说么。’
‘这样的书我可补不了什么阙。’伍次友笑道,’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应该出山了,要不要我写封荐书给你?’
孔尚任一怔,说道,’君子守时待命,先生的荐书不敢领。’
‘嗯,确乎如此!’伍次友更加赞赏,’你这样的大才,必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不过我如不荐,于心何忍?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可惜此非经国之策,’孔尚任笑道,’皇上未必就看得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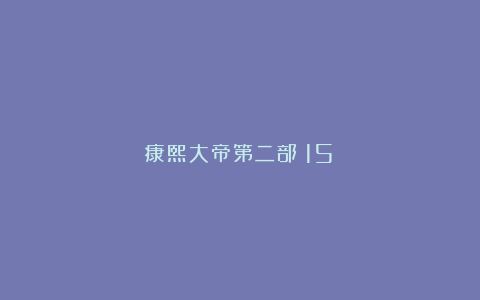
伍次友情绪平静了下来,微微一笑,说道:’当今乃是一代令主圣君,岂有叫你落空的?’说到这里,又沉吟良久道:’可惜的是,三藩未靖,虎视中央,皇上虽有此心,未必抽得出余暇来处置这些文事啊!’说到这件事,孔尚任情绪低落了,点头叹道:’我是久闻先生道德文章的了,既然皇上方在用人之际,先生何必自弃?应当回皇上身边参赞大计才是啊!’
这话说得伍次友心里一动。是啊!乱世之人,不如治世鸡犬,像孔府这样的巨族,衰微下来,会出现孔仁玉那样的惨剧;像孔尚任这样的才人,遇到这种时候,也只好坐等天下太平。守时待命,什么时候是个了局?
正默默出神,张姥姥带着云娘进来,呵呵笑着说道:’尚任,一看就知道你们谈得投缘,在那屋里都听见这里又说又笑,多少天来这院里没有恁热闹了﹣-再告诉伍先生个喜讯儿,郑春友已经叫钦差给杀了,这兖州府地面要清净几日了。我和云娘已经说好,就照我前头的话办吧。’
‘敬遵姥姥的命。我和聘之兄还可多切磋些学问。’伍次友说道。他心里不免诧异:没有听说有钦差到,怎么会突然就杀了郑春友?
府衙逃走了’李雨良’和伍次友,张姥姥碰回了孔令培,兖州知府郑太尊却仍决定大出红差,处决所有谳定秋审的在狱罪因。原因很简单,伍次友既已出走,又拿不回来,他这个知府是做不成了,须得逃往云贵。狱中在押的三十二名死囚,除四名盗贼、奸淫的刑事犯外,都是在云南哗变返回中原的官佐,还有是钟三郎会众的反叛。自己的真面目既已暴露,肯定臬司要重新审核,说不定还要惊动刑部,让这些’汉贼’从他郑春友手上活着出去,将是终生憾事。再说,自己逃到了云南,总不能空着手去见平西王呀!所以,当孔令培回来报知在曲阜无法捉拿伍次友的消息后,郑春友先是一阵惊恐,沉默良久,突然失心疯似地爆发出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想不到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依旧是镜花水月,水月镜花……哈哈……’
听他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被他吓呆了,半晌方期期艾艾地问道:’太尊……您,您这……这是?’
‘太尊?’郑春友睁着一双血红的眼,’太尊已经没有了,现在我是大明义民郑春友!’他忽然又显得伤心颓唐,一下子跌坐在交椅里,埋头思索好一阵,抬起泪光闪闪的脸说道:’令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在此一年半,你知道我刮了多少?’
孔令培不敢回答。
‘十五万!’郑春友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十五万分了三份,一份给了平西王;一份给了朱三太子;余下的五万我用来打点身边的人!所以,于满清我算得第一赃官,于大明我却是第一清官!若是我身遭不测,请你将这话传遍天下。’拿!’
孔令培不解地问道:’那怎么会?伍次友并没有出兖州,还是要想法子捉’我手中若有兵,还用你说?’郑春友冷森森地一笑,’可叹可惜,朝廷竟没在兖州驻兵,你们孔府有兵,却又由不得你来支配……’
‘那我怎么办?’
郑春友不言声,至桌前提笔写了一张条子,又小心地用了自己的印,交给孔令培,说道:’你拿这个条子到库里提一万银票,到云南,到北京去寻世子都成,远走高飞!’
‘那您呢?’
‘我?’郑春友咬牙笑道,’放心﹣﹣我也不傻!今日四门齐开,斩决全狱要犯,我也要裹银而遁了!’说着便笔走龙蛇、文不加点地亲自起草杀人文告。写好了,自己再看一遍,见孔令培还怔怔地坐着,便道:’你还不去,是怎么了?’
孔令培嗫嚅半天,方道:’我怕……怕伍次友抄了我的家……’
‘国且不国,何以家为!’郑春友冷笑道,’便宜不了他伍次友!我表弟朱甫祥在固安罢官后,已在抱犊崮和大响马刘大疤会合,啸聚了七百多人,我已写信请他留意。他知道此中情由,岂肯放过伍次友?我现在……’他说着,有些气短,回身摘下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抽出来弹了弹。那是上好的剑,立时发出铮铮嗡嗡的金属颤鸣,’我现在最恨的是皇甫保柱!王爷怎么选这样一个人来办大事?他若不怠慢心软,我郑春友焉有今日之祸?’
他一边沉思着说,一边走近孔令培,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向孔令培当胸猛刺一剑,那剑一直穿透他的后心。
‘你!’孔令培’刷’地立起身来,踉跄着不肯倒下,狞笑着问郑春友,’你为什么?说出来叫我死得明白!’
郑春友端一杯凉茶喝了,笑眯眯地说道:’爱国即不能爱家,爱家必然惜身,惜身必然卖友!我这不是成全了你么?伍次友知道我杀了你,还会抄你的家么?’
孔令培瞪着眼听完,’嗯通’仰倒在地,无声无息死了。郑春友拔出剑来,扯过桌上台布,细细揩拭干净了,佩在身上,出来将大门反锁了,气宇轩昂,面色从容直趋签押房,按剑大呼:’升堂!’
西菜市刑场阴风惨惨,杀气腾腾。三十二名刀斧手一色儿新的绛红大袍,玄色腰带,一律右臂赤胸在外,磨得雪亮的鬼头刀刀钩朝外,宽厚的刀背压在多毛的前胸上。他们不耐烦地站着轻轻跺脚,横肉块块饱绽的脸上泛着黑红的光﹣-那是八两老烧刀子的功效了。刑场四周布满了衙役,足有四百多人﹣﹣连首县衙门的人都调空了。正中面南的一座高台上摆着﹣张公案桌,一根根亡命签牌齐整摆好了。郑春友一身簇新的官袍,立在案后提着朱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地一一勾牌,交给司书发下。只见各班番役人等已经到任,郑春友便吩咐:’预备好,本府亲自监斩!’
‘喳﹣﹣噢﹣-‘下面雷轰般长应了一声,便推出已插了亡命牌的人犯出来。立时,外头瞧热闹的老百姓一阵骚动,都伸着脖子看,圈子里的衙役便用鞭棍一阵乱打,逼着人圈子向后退。孔四贞还是头一次见地方官杀人,和地狱里森罗殿布置毫无二致,不觉心悸。回头看时,青猴儿拿一把瓜子儿站在孙延龄身边,一边嗑着,一边用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在犯人中搜寻伍次友和李云娘,却因犯人一色披着囚衣,头都被刀斧手按得低低的,竟看不清楚。孙延龄却显得若无其事,背着手用冷冰冰的目光漠然注视着满脸杀气的郑春友。
‘自古对谋反造逆之人,决不待时而斩!’郑春友双手据案,大声说道。这是他知府任上杀人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所以特别郑重。他回头看一眼特地赶制出来的一面竖旗:宝蓝缎面儿四周镶着血红的流苏,中间一行大字也是他的手书:
钦命进士及第五品中宪大夫知府郑
旗上的十五个黄字迎着寒光刺人眼目。郑春友转过脸来,眼中带着肃杀之气又道:’本府为绥靖地方,安抚百姓,已缉获劫牢大盗李雨良、聚众谋反首领于六,经六百里加急请示上宪,今日处置待决死囚,操刀手预备好了没有?’
‘喳!’三十二名刽子手齐声应诺,’请大人下令!’
‘慢!’见孔四贞使眼色,她的包衣奴才戴良臣大喝一声,手一扬跨进了刑场,盯着郑春友问道,’你说已奉宪谕,拿出桌司滚单来叫大家瞧瞧呀!’
谁也没有料到竟会有人敢在这当口走出来说话,场内场外黑鸦鸦上千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都伸直了脖子瞪着眼瞧。
‘大胆!’郑春友因接了吴应熊的信,心中早有防备,见这汉子跳出来,料是钦差手下的人,’啪’地将公案一击,喝道,’将法场滋事的人给我拿了!’护在郑春友身边的几个彪形大汉’喳’地答应一声,恶狠狠扑了过来。
孔四贞一回身,厉声向孙延龄道:’延龄,上!’郑春友在台上早一眼望见,点着护法场头儿的名字叫道:’刘天一,是谁在那边喧哗?’
刘天一以为有人劫法场,早吓得愣在一边,尚未及答话,青猴儿突然一跃蹿了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
‘是小爷!明白么!-﹣爷们奉了皇命钦差来的,谁敢来拿?’
青猴儿说着,’嗖’地抽出腰刀,一把揪住扑上来的刘天一,顺势儿反拧了他的膀臂,将刀猛地斜劈下去:’谁敢无礼?’
这毛头小子经云娘和胡宫山传授,身上功夫已经不浅,这一下出手又快又利落。刘天一的头颅滚出四五尺远,血溅得到处都是,连上来拿孔四贞的衙役们都吓得愣在当地!
‘给我拿,拿,拿!’郑春友咆哮道,’这正是昨夜劫衙的大盗!’
‘你拿不成!’孔四贞至此才迈着大步进来,将康熙赐她的金牌令箭从怀中取出,高擎在手,晃一晃,耀目辉煌,’我乃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贞!这是圣上令箭,命我微服查访民风!’
郑春友倒抽一口冷气,心下一阵暗惊:这便是久闻其名,未谋其面的’四格格’!性命交关之际,他反镇定了下来,嘿嘿冷笑道:’你就是钦差?怎么既没有廷寄,也没有勘合,上宪也无滚单告知?哼!自古至今,哪有女流之辈为钦差大臣的﹣﹣显系刁妇冒充钦差,这还了得?’他抬高了嗓音,大喝道,’一个也不要放走了,一体擒拿正法!’
孔四贞听了不禁仰天长笑。她奉康熙之命,以和硕公主身份携了丈夫孙延龄同赴广西,节制父亲孔友德的旧部。这次赴广西,孙延龄原想走陆路,但四贞却因奉旨顺道密访伍次友,执意循水路南下,不想昨夜在兖州府刚刚住下,便遇到了从府衙中逃出的青猴儿,便在船上议定,今日劫法场营救伍次友。
郑春友瞧见了铸有’如朕亲临’的金牌,心里一阵发寒,眼见围观百姓已是骚动不安,衙役们面面相觑,知道稍一胆怯便一切全完,因见她只寥寥四人,略觉放心,恶狠狠一笑,说道:’这件东西是真是假,难以凭信!’
孔四贞不屑与郑春友答话,只冷笑着将手一招,孙延龄便忙不迭过来,拱手道:’公主,有何指令?’
‘公主!’这下子人们都听清了,千余双目光都射向了孔四贞,一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气都透不过来。
‘延龄,’孔四贞平静地将手一摆,’拿下他来!’
‘喳!’孙延龄答应一声,挺身直趋监斩台,一个书吏双手张着来拦,
被他当胸一点,接着一记耳光,早仰面朝天倒下。孙延龄这才哈哈笑道:’我也是个钦差,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附节制广西兵马都统孙延龄!懂了么?’说着转脸向人群喊道:’谁出来应命,大爷有赏!’
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刷’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也来助打太平拳,一齐躬身对孙延龄道:’惟大人之命是听!’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灵醒过来,一齐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地鼓噪,’拿了这狗官!拿了这狗官!’
郑春友一阵气馁,向座椅上一瘫,又弹簧似地跳起来,拍案冷笑道:’如今的钦差真比兔子都多,一下子便蹦出两个来!可笑之至﹣﹣还有谁是钦差?站出来说话!’说着,不动声色地扫视全场。
‘没有了?好!’郑春友步下监斩台,指着一个死囚问孔四贞道,’我姑且称你钦差大人﹣﹣此人,还有那三十一个,都犯的什么罪,讲啊?’他嘿嘿笑道,又转问孙延龄,’你’大人’又因何搅扰’下官’的公务呢?’
这句话问的在理,又十分得体。孙延龄没了词儿,原说是要救伍次友,但他和孔四贞却都不认识,因转脸瞧青猴。此时青猴儿已逐个儿验看过了囚犯,只懊丧地摇了摇头。孔四贞情知变中有变,微一沉吟,朗声说道:’我私访至此,知你劣迹斑斑,是个贪官!元春之月不请圣上御旨,擅自勾决这么多人犯,更属居心叵测!且人犯临刑呼冤,应即停刑再勘,国有明典﹣﹣条条款款你全都犯了,还敢在我面前放肆,自称无罪?’
‘哪个认你们是钦差?谁晓得什么孔四贞?’郑春友倏地脸色一变,拔剑在手格格冷笑,’衙役们!’
‘在!’番役们早被这阵势弄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此时一听府尊大人吆喝,参差不齐地答应道。
‘出了事一切由本府挡着,你们尽自拿人,拿住一个赏银三百两!’郑春友狂怒地红着眼,’咔’地挥剑斩掉桌子一角,’有畏缩不前者,斩!’
话音未落,孙延龄早已大怒,一个箭步上前,将郑春友胳膊反拧过来,下了他手中的剑,顺势一剑砍下,将他膀子削下一块肉来,问道,’还敢无礼么?’
‘拿!只管拿!’郑春友横了心,拧着脖子狂叫道。
但衙役们早已被这勇武得像天神一样的孙延龄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再动了。孔四贞见时机已到,双手捧着令箭,由戴良臣和青猴儿护持着款步直登监斩台,将案上知府印信随手甩给一个瞠目结舌的书吏,供好了御札、令箭,行了三跪九叩大礼。
这才肃然落座,叫道:’孙延龄,将郑春友拖下去,斩!’
孙延龄答声’是’,拖着痛得半昏迷,浑身是血的郑春友便往下走,往地下一丢便要下刀,青猴儿在旁拦住了道:’额驸,你不知这家伙有多阴毒﹣﹣不是那个杀法,我来!’说着,左一剑、右一剑、横一剑、竖一剑,在郑春友身上连戳十七八下,最后才照心窝里猛扎进去。他出手如此狠毒,连孔四贞将门虎女,也暗自心惊。
‘把人犯先押回狱中监理,’孔四贞回过神来,大声吩咐道,’发文山东泉司,委干员重新审理谳定,报刑部详文,请皇上勾定之后再行处决!’
这一处置十分明快,无论于法理,于程序都对,原来疑心’劫法场’的衙役们顿时放下心来,在下头高声答应:’喳﹣-‘
当日孔四贞一行人便住了府台衙门,只到用晚饭时,大家心神方才安定。孙延龄一边吃一边笑道:’今日真的唱了一台戏,兖州府全被轰动了!难为公主压得住阵脚﹣﹣这事据我看,得赶紧申报朝廷才是。’
‘那当然,吃过饭你就代我草个折子,我过了目就拜发。’孔四贞见青猴儿吃得香甜,将自己跟前一盘子肥鹅推过去,一边笑道:’青猴儿,你倒对我的脾性,跟我到边庭立功去,好么?’
‘我不!’青猴儿鼓着腮帮子道,’我还要寻我的姑姑呢!’说着双手将鹅一撕两半,左一口右一口,汤汁淋淋漓漓撒了一桌子。
孔四贞叹道:’这孩子只一心念着他的姑姑。唉……也不知伍先生现在哪里﹣﹣这次我们是没工夫再细查了。’孙延龄一边随便吃着,一边说着:’咱们在直隶山东已经停留了不少日子,不敢误了正经差使。这回虽没见着伍先生,好在衙役们都说他们已经脱险了。’
孔四贞最亲近的密友便是苏麻喇姑,听孙延龄说的有理,又想着有点对不住苏麻喇姑,沉思良久,自慰地叹道:’也只好如此。瞎,世上只有女人们心痴,男人们哪里晓得这些?这么着想,我的心也灰了……’
第二日启程,青猴儿仍是不愿跟孔四贞南下,口口声声要寻李云娘。孔四贞眼见这娃儿伶俐可人,越发舍不得丢手,便劝道:’好孩子,你渐渐大了,也是要立功名做事业的,跟了我南去,弄个红顶子见你姑姑多好!-﹣你不是说过,你娘被卖到了广东?那儿离我们那里却不远,我着人细细打听着,说不定你们母子还能团圆呢!’
说到娘,青猴儿又迟疑了,泪光闪闪的一双大眼睛瞧瞧这个,又望望那个,嘴咧了几咧,竟自放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