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简称ADCs)是一种有前景的癌症治疗手段,可将药物靶向递送至肿瘤细胞。然而,针对ADCs的耐药性仍是一个挑战,因此需要探索联合治疗(combination therapies)的可能性。一种强有力的生物学理论表明,ADCs通过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树突状细胞激活(dendritic cell activation)以及记忆T细胞激活(memory T-cell activation)等机制,能够与癌细胞和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从而诱发长期的抗肿瘤免疫,最终与免疫治疗产生潜在的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s)。
基于广泛且可靠的临床前数据,目前已有若干项临床试验正在将ADCs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联合用于包括乳腺癌(breast cancer)、胃癌(gastric cancer)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等多种癌症的治疗,以评估这种联合治疗的安全性(safety)和抗肿瘤活性(anti-tumor activity)。来自早期临床试验的初步证据已报告更为有效的疗效数据(efficacy data)。
本文综述了ADCs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重点强调了两者协同作用的关键机制(key mechanisms),并总结了不同ADCs靶点(ADCs targets)相关的临床证据。同时,本文还探讨了用于联合治疗的再挑战策略(re-challenges)以及ADCs药物的优化设计选项(optimized design options)。
关键词
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免疫治疗(Immunotherapy)·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实体瘤(Solid tumor)
引言
以PD-1/PD-L1抑制剂(PD-1/PD-L1 inhibitors)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一类通过阻断免疫检查点与其配体的结合,从而解除免疫抑制(immune suppression)并激活免疫细胞以发挥抗肿瘤作用的药物。然而,遗憾的是,仅有一部分患者能够获得临床获益,因此仍需探索与其他药物或不同治疗策略的联合治疗,以克服耐药性并拓展其临床应用价值。
近年来,以抗体为基础的新型大分子复合物(antibody-based macromolecular complexes),以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s)为代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ADCs由三部分组成:一种抗体(antibody)、一个有效负载(payload,即高效细胞毒性药物分子)以及连接这两者的连接子(linker)。其作用机制为:抗体与靶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后,ADCs被内吞(internalized),并释放出其有效负载,从而发挥细胞毒性作用(cytotoxic effects),为多种实体瘤提供了一种高效且精准的治疗策略。
自2013年首个ADC获批用于实体瘤治疗以来,已有9种ADCs被批准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并涵盖不同的适应症,详见图1所示。然而,药物耐药性依然难以避免。相关研究表明,ADCs不仅通过靶向抗原并释放有效负载来诱导肿瘤细胞死亡(tumor cell death),还可诱发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 ICD),进而改变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ICIs则可通过激活T细胞(T-cell activation)来解除免疫抑制,从而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s),因此,两者的联合应用已成为癌症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
该联合治疗方案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对难治性实体瘤具有显著疗效,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特征。本综述将重点关注ADCs与免疫治疗联合的研究进展,聚焦其作用机制、临床试验结果及未来发展方向,为个体化癌症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ADCs联合ICIs的生物学机制
如图2所示,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s)通过识别并结合肿瘤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specific antigens),被内吞(internalized)进入细胞。随后,ADCs中的连接子(linkers)被降解,释放出有效负载(payloads),从而诱导细胞凋亡(apoptosis)。此外,一些payload还能通过旁分泌效应(paracrine effect)杀伤周围未表达靶抗原(non-targeted)的细胞,这一过程并不依赖于细胞表面靶抗原的表达。因此,payload是ADCs的最终效应组分(ultimate effector components),主要包括:微管抑制剂(microtubule inhibitors,如MMAE、MMAF、DM1、DM4)、DNA损伤类药物(DNA damaging agents,如Calicheamicin、PBD、Duocarmycin)以及拓扑异构酶抑制剂(topoisomerase inhibitors,如SN38、DXd)。
此外,ADCs还能通过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 mAb)部分介导的效应功能进一步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包括抗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ytotoxicity, ADCC)、抗体依赖的细胞吞噬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 phagocytosis, ADCP)以及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作用(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 CDC)。
ADCs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其他正常组织器官的损伤。这种策略不仅增强了药物的治疗效果,还提升了肿瘤的免疫原性(immunogenicity)[13]。ADCs增强ICIs疗效的关键机制之一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 ICD)。ICD是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其区别于传统的凋亡(apoptosis)在于,ICD伴随有肿瘤相关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TAA)与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DAMP)的释放。DAMP包括暴露在细胞表面的钙网蛋白(calreticulin, CRT)以及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 HSP70和HSP90),这些分子促进吞噬细胞(phagocytosis)摄取死亡细胞;同时,还包括胞外释放的免疫刺激因子,如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1, HMGB1)和细胞因子(cytokines)。
当肿瘤细胞存在异常的DAMP释放通路(如自噬autophagy和未折叠蛋白反应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时,可能无法对诱导ICD的刺激产生反应。因此,提高特定DAMP的可用性有望将非免疫原性细胞死亡(non-immunogenic cell death)转化为ICD。这些分子随后被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s)识别、摄取并加工处理,然后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II类分子(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II, MHC II)呈递,从而激活CD8+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T cells)和CD4+辅助性T细胞(helper T cells)。
以往研究表明,微管去稳定化药物(microtubule destabilizing compounds,如长春新碱vincristine)可有效诱导树突状细胞的表型和功能成熟(phenotypic and functional maturation),而微管稳定剂(microtubule stabilizers),如紫杉醇(paclitaxel)则无此效果。此外,这些药物的抗肿瘤作用依赖于完整的免疫系统(intact immune system),在免疫缺陷小鼠(immunodeficient mice)中疗效明显减弱。重要的是,LA-4抑制,因此使用ICIs可以有效解除这种抑制并维持T细胞对肿瘤的免疫反应。
ADCs与免疫治疗联合用于抗肿瘤治疗的协同效应已在相关临床前试验中得到了验证。在一项将含有微管去聚合剂(microtubule depolymerizing agents)payload的ADCs与ICIs联合治疗接种了MC38肿瘤的小鼠的临床前研究中,每组使用12只小鼠,与单用ADCs(1只)或单用ICIs(3只)相比,联合治疗组中有更多小鼠(7只)实现了肿瘤完全消退(complete tumor rejection)。这充分表明,ADCs与ICIs的联合治疗显著优于单药治疗(monotherapy)。
类似地,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s),如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也展现出相同的疗效。已有研究表明,三种不同的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顺铂(cisplatin)、拓扑替康(topotecan)和伊立替康(irinotecan)——均可增强T细胞的肿瘤杀伤活性(tumor killing activity)。而T-DXd在相关的临床前小鼠模型实验中的数据也可能进一步证明联合治疗的优越性。
临床前研究表明ADCs可通过促进记忆T细胞(memory T cells)的生成来实现长期抗肿瘤免疫(long-term anti-tumor immunity),这一现象已获得部分体内实验结果的支持。D’Amico等人使用负载蒽环类衍生物(anthracycline derivatives)的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HER-2-targeted ADCs)治疗人源化HER-2表达阳性(HER-2⁺)纯合小鼠(homozygous mice)。在这些小鼠被完全治愈后,研究人员再次接种原始HER-2⁺癌细胞或其他不同谱系的肿瘤细胞。结果显示:重新接种原始HER-2⁺癌细胞的小鼠维持完全缓解,而接种不同谱系肿瘤细胞的小鼠则迅速发生肿瘤。
同样,Iwata等人观察到,对T-DXd(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完全应答的纯合小鼠模型能够完全清除重新接种的癌细胞;相比之下,这些相同的肿瘤细胞在未接受任何预处理的对照小鼠中则迅速生长。在另一项将Disitamab vedotin(RC48)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的临床前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结果。综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DCs可能通过产生适应性免疫来发挥抗肿瘤作用。
不同ADCs与ICIs联合使用的临床研究数据
在强有力的临床前研究基础之上,众多临床研究已经展开,旨在评估ADCs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联合治疗肿瘤的临床可行性、安全性以及疗效。表1总结了目前针对ADCs与ICIs联合用于实体瘤治疗的临床试验现状,而表2则列出了已公布全部或部分疗效数据的临床试验。
HER‑2
HER-2是多种癌症中高表达的关键成员,包括乳腺癌(breast cancer)、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等。活化的HER-2可促进肿瘤的生长和扩散。因此,HER-2是许多HER-2阳性肿瘤治疗中具有前景的治疗靶点。
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是第一个被批准用于实体瘤(solid tumors)治疗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多项既往联合治疗研究显示,在PD-L1阳性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mission rate, ORR)更高,疗效优势也更为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项所有患者均为PD-L1阴性的试验中,T-DM1联合免疫治疗并未显示出显著的临床意义。
T-DXd(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目前是HER-2阳性实体瘤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多个试验正在探索该ADC与免疫治疗(immunotherapy)联合使用的可行性及潜在疗效。在DS8201-A-U105 I期b期试验的乳腺癌(breast cancer, BC)部分,45例HER-2阳性BC患者接受了T-DXd与Nivolumab联合治疗。中期分析显示,HER-2阳性患者的ORR为65.6%,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为11.6个月;而HER-2低表达患者的ORR为50.0%,mPFS为7.0个月。在同一试验的尿路上皮癌(uroepithelial carcinoma, UC)部分,接受联合治疗的HER-2高表达(免疫组化IHC 3+/2+)转移性UC(mUC)患者达到ORR为36.7%,mPFS为6.9个月,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为11.0个月。结果显示,推荐扩展剂量(recommended extended dose, RDE)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在接受过广泛前期治疗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mBC)和HER-2高表达mUC患者中展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这一抗肿瘤活性与先前T-DXd单药研究结果一致。
正在进行的HUDSON试验评估了Durvalumab与T-DXd联合用于HER-2过表达(HER-2 overexpressing, HER-2e)或HER-2突变型(HER-2-mutant, HER-2m)NSCLC患者的抗肿瘤疗效。HER-2突变型患者在ORR(35.0% vs 26.1%)、PFS(5.7 vs 2.8个月)和OS(10.6 vs 9.5个月)方面均优于HER-2过表达患者,提示联合治疗在HER-2m患者中展现出更显著的疗效趋势。
此外,DS8201-A-U106研究评估了Pembrolizumab联合T-DXd在HER-2e与HER-2m NSCLC患者中的抗肿瘤效果。最新中期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均展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ORR:54.5% vs 66.7%;mPFS:15.1 vs 11.3个月)[44]。将HUDSON试验和DS8201-A-U106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在相同治疗人群中,T-DXd与PD-1抑制剂联合使用的疗效更为显著。
多个试验也正在评估T-DXd与免疫治疗联合(DESTINY-Breast07的Module 1),以及T-DXd联合免疫治疗与化疗的三联治疗(DESTINY-Breast07的Module 4),用于HER-2阳性mBC患者[45]。DESTINY-Gastric03试验正在进行,研究T-DXd用于治疗晚期/转移性HER-2阳性的食管癌(esophageal cancer)、胃癌(gastric cancer)或胃食管交界腺癌(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GEJA)患者。
RC48-C013是一项评估RC48联合免疫治疗用于HER-2阳性晚期胃癌或胃食管交界癌(G/GEJ)及其他实体瘤的I期试验。在接受推荐II期剂量(recommended Phase II dose, RP2D)治疗的患者中,ORR达50.0%,显著高于RC48单药治疗组的24.8%。即便是在HER-2低表达的G/GEJ患者中,ORR也达到46.0%。进一步分析显示,初治患者的疗效优于曾接受过抗HER-2治疗的患者,ORR(53% vs 43%)、mPFS(6.1 vs 4.2个月)和mOS(24.7 vs 11.9个月)均显著改善。此外,在接受RP2D治疗且PD-L1 CPS(Combined Positive Score)≥1的患者中,ORR更高,PFS和OS更长。上述结果表明,RC48联合免疫治疗可能改善部分G/GEJ患者的治疗效果,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RC48-C014是一项针对局部晚期/转移性尿路上皮癌(la/mUC)的Ib/II期试验。最新数据显示,在相同治疗方案下,患者的mOS为33.1个月,mPFS为9.3个月,ORR高达73.0%,在长期随访中展现出显著疗效和总生存优势。
Trop-2
近年来发现,人滋养层表面抗原(human trophoblast surface antigen)Trop-2在多种实体瘤中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这种上调不仅促进了肿瘤细胞的增殖、增长和扩散,还与预后不良及转移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Sacituzumab govitecan(SG)是首个靶向Trop-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Trop-2-targeted 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在Saci-IO HR+试验中,对既往接受过治疗的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和激素受体阳性/ HER-2阴性(hormone receptor-positive/HER-2-negative, HR+/HER-2-)转移性乳腺癌(mBC)患者进行了评估。在PD-L1阳性(复合阳性评分Combined Positive Score, CPS ≥ 1)的HR+/HER-2-患者中,SG联合Pembrolizumab(A组)相较于SG单药治疗(B组)显示出更佳的疗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延长了4.4个月(11.1 vs 6.7个月),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延长了6个月(18.5 vs 12.5个月)。试验结果更支持联合治疗的优势,然而,不同PD-L1表达层级(CPS ≥ 1 vs CPS < 1)在PFS和OS上并无显著差异。
此外,在Morpheus-TNBC试验中,SG联合Atezolizumab显示出获益趋势(12.2 vs 5.9个月),尽管PFS数据尚不成熟。将上述两个试验中联合治疗部分的疗效数据进行比较显示,SG联合Atezolizumab的抗肿瘤活性显著优于SG联合Pembrolizumab,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分别为76.7%和21.2%。此外,在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方面,SG联合Atezolizumab亦展现出更优疗效(12.2 vs 8.4个月)。
II期EVOKE-02研究的最新数据显示,无论组织学类型(鳞状或非鳞状,squamous or non-squamous),SG联合Pembrolizumab在未经治疗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NSCLC)患者中均展现出抗肿瘤活性。
Datopotomab deruxtecan(Dato)是一种以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为有效载荷的Trop-2靶向ADC。在BEGONIA试验中,接受Dato联合Durvalumab治疗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mTNBC)患者达到79.0%的ORR(62例患者中6例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 CR,43例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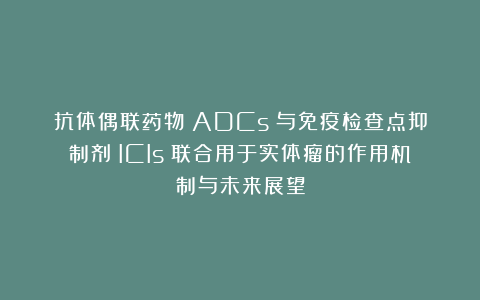
另一项针对Dato联合Pembrolizumab(±铂类药物,platinum analog)治疗NSCLC的Ib期试验数据显示,无论PD-L1表达状态如何,双联或三联治疗方案下均展现出持久的抗肿瘤活性。
另一种Trop-2靶向ADC药物SKB264在原发晚期NSCLC患者中亦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效果(ORR为48.6%)。目前,数项关于SKB264的I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相关数据尚未公布。
Nectin‑4
Enfortumab vedotin(EV)是一种靶向Nectin-4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已被批准作为单药治疗用于铂类化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耐药的晚期尿路上皮癌(advanced urothelial cancer, aUC)。
在III期EV-302试验中,EV联合Pembrolizumab在既往未经治疗的晚期/转移性尿路上皮癌(advanced/metastatic urothelial carcinoma, a/mUC)患者中展现出显著疗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为12.5个月,显著优于化疗组的6.3个月;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为31.5个月,几乎是化疗组的两倍。此外,联合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也明显高于化疗组(67.7% vs 44.4%),疾病进展风险降低了55%,死亡风险降低了53%。这些结果表明,在a/mUC一线治疗中,EV联合治疗相较于传统化疗具有显著且临床意义明确的优势。
此外,在II期EV-202研究中,EV单药治疗头颈癌(head and neck cancer, HNC)患者的确证ORR为23.9%,超过了预设阈值(17.5%),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这为评估EV联合Pembrolizumab治疗HNC患者提供了依据。
EV-202研究的另一队列目前正在研究EV联合Pembrolizumab作为复发/转移性头颈鳞状细胞癌(recurrent/metastatic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arcinoma, R/M HNSCC)并具有PD-L1复合阳性评分(CPS)≥ 1的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
其他新靶点(Other new targets)
先前的研究表明,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MIRV)在一项针对叶酸受体α阳性(folate receptor alpha-positive, FRα-positive)晚期或复发性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 EC)患者的I期剂量扩展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和单药活性。随后的一项II期研究评估了其与Pembrolizumab联合使用的疗效。在接受治疗的16例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37.5%,其中1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5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
近期研究结果显示,MIRV联合Pembrolizumab在治疗FRα阳性、复发性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stabilized, MSS)/错配修复功能正常(proficient mismatch repair, pMMR)浆液型子宫内膜癌(plasmacytoid EC)中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具备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目前也正在开展针对潜在获益亚组的研究。
此外,Tisotumab vedotin(TV)是一种靶向组织因子(tissue factor, TF)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在一项针对复发/转移性宫颈癌(recurrent/metastatic cervical cancer, r/mCC)的Ib/II期研究中,TV联合Bevacizumab、Pembrolizumab或Carboplatin用于一线、二线或三线治疗时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这为TV与单药联合治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目前,TV联合Carboplatin、Pembrolizumab,或选择性联合Bevacizumab用于一线治疗的扩展研究正在进行中。
最后,在一项针对晚期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advanced non-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Ib/II期临床试验中,Tusamitamab ravtansine(靶向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5,carcinoembryonic antigen-related cell adhesion molecule 5, CEACAM5)的ADC联合Pembrolizumab展现出积极的初步结果,客观缓解率(ORR)为47.8%,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为11.6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median duration of response, mDOR)为12.4个月。
此外,目前还有数种靶向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 18.2(主要用于胃肠道肿瘤,gastrointestinal, GI tumors)的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其中一项Ib/II期临床试验在ASCO会议上公布:在6名可评估疗效的患者中,有3名达到部分缓解(PR),因此其在Ib期研究中的最佳总缓解率(best overall response, BOR)为50%。
抗体偶联药物(ADCs)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安全性与再次使用(re-challenge)药物安全性与不良反应(Drug safety and adverse reactions)
表3总结了表2中各项临床试验的安全性数据。
在T-DM1联合免疫治疗的非随机早期临床试验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 AEs)包括疲劳(fatigue)、贫血(anemia)、恶心(nausea)和肺炎(pneumonia);而较为严重的不良事件则包括血小板减少(thrombocytopenia)、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elevate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elevate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及肺炎。在接受T-DM1联合Atezolizumab治疗的患者中,由于不良事件而中止治疗的情况比单用T-DM1更为常见,实验组中还发生了一例噬血细胞综合征(phagocytosis syndrome)导致的死亡事件。
当T-DM1与Pembrolizumab联合使用时,有四位患者在第2、3、4及第12个治疗周期后出现了肺炎,这些病例均被怀疑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相关,并在接受激素治疗(steroid therapy)后得到改善。相比之下,在随机对照KATE2试验中,尽管Atezolizumab组中因肺炎而中止治疗的情况更多,但所有等级和≥3级肺炎的发生率在两组之间相似,提示联合Atezolizumab并不会显著增加肺炎的风险。
多项临床试验表明,与单用T-DXd相比,T-DXd联合免疫治疗患者更容易发生严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 SAEs)。DESTINY-Gastric03试验的初步结果显示,T-DXd三联疗法(triple therapy)中≥3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91%,显著高于双联疗法(81%)和单药治疗(64%)。
在DS8201-A-U105试验的转移性乳腺癌(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BC)和转移性尿路上皮癌(metastatic urothelial cancer, mUC)模块中,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 TEAEs)为恶心(nausea)、疲劳(fatigue)和呕吐(vomiting)。与低HER-2表达患者相比,HER-2阳性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更高,尤其是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肺炎,其中一些患者出现了5级ILD/肺炎(grade 5 ILD/pneumonia),导致治疗中止或死亡。
在与Pembrolizumab联合的Ib期试验及HUDSON试验中也观察到了类似情况。在HUDSON试验中,肺炎是最常见的≥3级不良事件。ILD/肺炎的处理主要包括停药和使用激素治疗(steroid therapy),部分患者在治疗后有所改善。
在两项关于Datopotamab deruxtecan(Dato)的试验中,口腔炎(stomatitis)和恶心是最常见的TEAEs,尤其在双药或三药联合方案中,恶心的发生率更高。在TROPION-Lung02试验中口腔炎的发生率为57.0%,而在Begonia试验中为65.0%,两者均以1–2级不良事件为主。
最后,在Enfortumab vedotin(EV)联合Pembrolizumab的试验中,最常见的TEAE为周围感觉神经病变(peripheral sensory neuropathy, PN),多为轻度至中度。而在EV-103试验中,周围神经病变与皮肤反应则属于需特别关注的≥3级不良事件。
再次使用(Re-challenge)
严重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serious drug-related adverse reactions)是肿瘤治疗过程中常见的停药原因。然而,大多数不良反应通常较轻且可逆,通过对症治疗(symptomatic treatment)可以缓解,且停药后功能通常能够恢复正常。当不良反应得到有效控制后,患者可以继续使用原始治疗方案或根据临床指征进行剂量调整。这种停药后恢复使用原方案的行为称为“再次使用”(rechallenge)。
间质性肺病/肺炎(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pneumonia, ILD/pneumonia)是许多癌症治疗中常见的导致停药的不良事件,抗体偶联药物(ADCs)也不例外。在DESTINY临床项目中,T-DXd显示出总体可控的安全性,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血液学(hematologic)和胃肠道(gastrointestinal)相关事件,但ILD/pneumonia为特别关注的不良事件。2级及以上的ILD/pneumonia通常需要永久停药并进行高剂量激素治疗。2024年欧洲临床肿瘤学会年会(ESMO Congress)报道了一项关于T-DXd再次治疗的回顾性分析,数据涵盖了9项临床试验中接受过至少一次T-DXd治疗的HER-2改变型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在2145名患者中,有193人出现1级ILD,其中97人通过激素治疗得到缓解,45名患者在恢复后接受了T-DXd再次治疗。在这45名患者中,有15名因再次使用的剂量与原始剂量相同(均为1级和2级)而复发ILD。在所有复发ILD的患者中,只有8人完全恢复。此外,有两名患者在尚未完全恢复1级ILD前即再次接受治疗,导致ILD分别进展至2级和3级。
此外,有一例病例报告描述了一名患者在多线治疗失败后接受T-DXd再次使用。该患者在接受两周期治疗后被诊断为3级ILD,接受了激素和抗生素治疗。症状缓解且恢复至1级ILD后,患者以减量方式进行T-DXd再次使用,同时维持低剂量激素治疗。在再次使用期间,患者疗效达到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且未观察到ILD的恶化或复发。另外,在T-DM1联合Pembrolizumab的1b期临床试验中,有4名疑似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ICIs-associated pneumonia)的患者在激素治疗后症状改善。其中3名患者永久停止Pembrolizumab治疗,但继续使用T-DM1,且未观察到肺部异常显著增加。
抗体偶联药物(ADCs)的发展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抗体偶联药物(ADCs, antibody-drug conjugates)的快速发展为肿瘤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经典的ADCs靶点(例如HER-2、CD30和CD79b)在多种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这些传统靶点的耐药性(drug resistance)和肿瘤异质性(heterogeneity)问题逐渐显现。肿瘤耐药通常与治疗靶点表达的下调或非靶向效应(off-target effects)相关。为此,研究人员采用联合靶点策略(combination target strategies)或靶点表位(epitope)优化,以增强肿瘤治疗效果并延缓耐药的出现。
抗体与靶点选择
构建ADCs的理想骨架(ideal backbone)应具备识别仅在癌细胞表面特异性表达且在非癌组织完全缺失的抗原的能力,从而实现肿瘤特异性的载药物递送(tumor-specific payload delivery)。然而,大多数ADCs靶点(例如HER-2和TROP-2)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在非癌组织中表达,这可能导致靶向依赖性(target-dependent)及非依赖性毒性(non-dependent toxicity)的发生。为了增强肿瘤特异性,目前正在探索能够识别带有结构变异(如截短(truncation)、裂解(cleavage)或翻译后修饰(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的肿瘤特异性抗原的抗体[73–75]。其中,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bispecific ADCs)通过结合对两个靶点和传统载药物的抗体,能够显著提高载药递送效率及细胞毒性。此外,为解决传统ADCs分子过大导致的穿透性问题,开发的纳米抗体偶联药物(nano-antibody–drug couplings, NDCs)在实体肿瘤中展现出增强的穿透性和抗癌潜力[76]。一些ADCs还可通过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有效解决表观遗传异质性(epigenetic heterogeneity)问题,通过刺激对表达靶抗原细胞周围癌细胞的抗肿瘤活性来发挥作用。多项研究表明,可裂解连接子(cleavable junctions)和疏水性载药物(hydrophobic payloads)是实现旁观者效应的关键,这将成为新型ADCs开发的重要方向。
连接子优化
连接子(Linkers)是抗体偶联药物(ADCs)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共价方式将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ies)与细胞毒性载药物(cytotoxic payloads)连接起来,起着维持ADCs稳定性、疗效和安全性的关键作用。连接子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可裂解连接子(cleavable linkers)和不可裂解连接子(non-cleavable linkers),其中可裂解连接子包括化学不稳定型(chemically unstable)和酶敏感型(enzyme-sensitive)连接子。化学不稳定连接子可在肿瘤酸性环境中发生断裂,从而有效释放药物,但其在血液循环中的稳定性较差,通常导致药物过早释放。酶敏感连接子的出现通过利用肿瘤中过度表达的特异酶实现特异性断裂,从而提升了稳定性和递送效率,解决了上述问题。不可裂解连接子则通过溶酶体内的酶促完全降解释放药物,具有高稳定性和低非靶向毒性(off-target toxicity)的优势,但其释放效率较低且无法产生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因此需要通过优化载药物结构来提高疗效。
载药物优化
载药物(Payloads)的改进是ADCs优化过程中关键的组成部分。传统载药物,如微管抑制剂(microtubule inhibitors)和靶向DNA的药物(DNA-targeting agents),因其毒性和剂量限制面临挑战。近年来,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s)作为新型载药物的成功应用显著提升了ADCs的疗效,包括曲妥珠单抗-德昂定(T-Dxd)和SG,通过较高的药物-抗体比率(drug-antibody ratio, DAR)实现更高疗效。同时,引入低毒性分子及连接子技术的改进提升了ADCs的稳定性和治疗窗(therapeutic window)。此外,为满足肿瘤特异性和高效力的需求,载药物的选择通常偏向于在低浓度下具有高效活性的分子,通常其半数抑制浓度(IC50)处于纳摩尔至皮摩尔范围。
ADCs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联合治疗方案近年来在实体瘤治疗中展现出显著趋势。该联合治疗在多种实体瘤类型(例如非小细胞肺癌(NSCLC)、乳腺癌(BC)、胃癌等)中展现出良好效果,尤其在难治性肿瘤和高免疫耐受肿瘤中,联合治疗表现出增强的抗肿瘤活性。然而,要实现最佳治疗效果,仍存在一些需解决的限制。虽然前临床及早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联合治疗在减少肿瘤生长和增强免疫反应方面具有显著协同作用,但耐药性问题依然存在。尽管部分早期临床试验表明ADCs与ICIs联合治疗在HER-2阳性乳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癌症中具有潜力,但不同肿瘤类型间效果不一致及潜在严重不良事件的可能性,强调了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的必要性。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优化剂量方案、筛选合适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以及在更广泛患者群体中评估联合治疗的安全性,以确保更可持续和有效的治疗选择。
结论
总之,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s)与免疫治疗(immunotherapy)的联合展现出显著的协同潜力,不仅通过靶向递送细胞毒性药物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还能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 ICD)并增强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反应。前临床和临床研究均证明,这种协同效应有助于克服肿瘤异质性,减少治疗耐药,提高患者预后。早期临床试验显示,该联合策略在多种实体瘤中表现出优异的抗肿瘤活性及总体可控的毒性。然而,仍需警惕可能的重叠毒性问题,并加强对治疗安全性和长期疗效的监测。鉴于目前相关数据有限,仍需通过持续的药物警戒(pharmacovigilance)和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支持优化临床实践和提升患者护理。总之,ADCs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新方向,预计将成为个体化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难治性癌症治疗的整体进展(见图1和图2)。
资金支持
本综述文章未获得任何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的专项资助。
数据可用性
本研究产生或分析的所有数据均包含在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合理请求时可提供数据支持。研究发现所支持的数据可通过与通讯作者联系,在合理请求下获得。